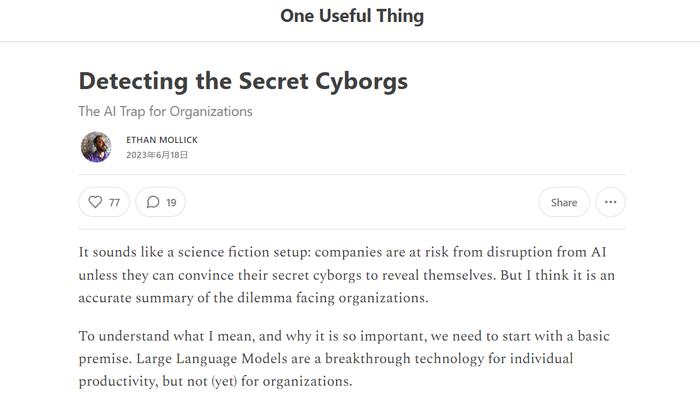小生脞談
原標題:小生脞談
今日推送之《小生脞談》錄自《春申舊聞續》,作者陳定山,工書畫,兼善詩文。他幼時因隨長輩歷練,得以結識了舊上海許多社會名流,耳聞目睹了上海灘名流們的種種過往,對舊上海掌故爛熟於胸,信手拈來,《春申舊聞續》是陳定山的掌故隨筆,爲《春申舊聞》續集,描寫舊上海文人逸事、藝壇雜俎、風俗市情、社會祕辛、菊壇掌故、勾欄風月、黑道傳說等等,一應俱全,引人入勝。
自從江南俞五返回上海,小生行一時興起“四顧無人”之嘆。其實俞五的戲只是崑曲好,論到平劇小生,他的身上,嘴裏都差。平劇小生的幼年練工,文武底子,俱不下於老生和花旦。俞五出身世家,唱崑曲是當年姑蘇爺臺們最出風頭的事,俞五的老太爺俞粟廬先生就是一位崑曲爺臺們的祭酒。俞五幼年受到庭訓便是唱曲子,俞老先生數一把鵝眼錢放在桌上,翻開曲譜,自己吹起笛子,教兒子唱,唱一遍,數一個鵝眼錢,這樣把桌子的錢數完了,今天才算放學。你說振飛的用功還算小嗎?至於他的平劇小生,就只算得羊盤,而全不是相家。說到武的,在崑曲裏他也有一點子,我聽過他的《起布》《問探》和崑曲全本的《宛城刺嬸》。《問探》是龐京周的探子,《宛城》是徐凌雲的曹操、徐子權的典韋。都在康腦脫路徐園唱。徐園是徐凌雲的別墅,當年水木清華,亭臺位置媲美愚園。崑曲傳習所就是凌雲和穆藕初發起辦的。最近有人在談《販馬記》,說俞五不算好,當年仙霓社裏有個顧傳玠,也就是現在臺灣的顧志成,顧傳玠唱紅的時候,俞五尚無藉藉之名。這可說得不對了。俞五崑曲名輩之早,不在袁寒雲後。
俞振飛之《琴挑》
崑曲傳習所乃是仙霓社的前身,《春申舊聞》裏有一篇《闌珊燈事話仙霓》,把仙霓社的歷史說得非常清楚。顧傳玠就是顧志成不錯,可是俞五在徐園客串時,顧傳玠尚是傳習所裏的子弟。雖和俞五提示不到顧傳玠,但傳玠至少也得叫他一聲師叔,因爲他們對於俞粟廬先生都是尊稱爲“太先生”的。
談到《販馬記》,這戲根本就不是崑曲而名爲弋腔,一名吹腔。崑曲家認爲下里之音,通人不道。貴俊卿、朱素雲、趙君玉常演《寫狀三拉》于丹桂第一臺,亦僅列倒第三,排不上壓軸的。問這出《販馬記》誰人在上海唱紅,那是李麗華的父親李桂芳和碧雲霞在共舞臺唱紅的,老生用陳嘉麟。李桂芳和程繼先是師弟兄,昆亂不擋,他還有一個怪癖,便是愛喫五毒。壁虎、蜈蚣、蠍子,他都喫,江南沒有蠍,看見壁虎,他就會瞪着眼,只想把它抓下來喫。後臺同事知道他有這個癖,都會替他尋找。但是他唱小生卻是溫文儒雅,一出《珍珠衫》尤其演得精細人微,和麒麟童同臺丹桂時,麒有許多表情偷他的,所以他的《販馬記》《寫狀三拉》實在夠得上“絕”,可是他在徐碧雲南下時過班共舞臺,唱這出戏沒紅。碧雲霞來,紅了。
說起來真氣人,原來碧雲霞是坤伶,不過,她的美而豔,劉喜奎我沒有看,提到後來的童芷苓、言慧珠,真替她拾鞋她還不要呢。其實好的是李桂芳這份綠葉,把她的牡丹襯紅了。李桂芳去世很早,可惜他的絕藝不傳。
坤伶碧雲霞
俞振飛唱《販馬記》還是在下海以前。說實些,這出《販馬記》在朱素雲和趙君玉唱時,《寫狀》一場沒有現在這樣的花妙。這戲確有經過俞五和顧傳玠兩個人商量改動的地方很多。顧現在臺中,可以就近問他。去年,我和他喫過一次酒,他的笛子還是撅得那麼遏響飛聲。可惜那次徐炎之不在座,沒有讓他好好的唱,只拍了一段“收拾起”那一句“冷雨悽風帶怨長”,還是聲如裂帛,直上雲霄。我們也談到《販馬記》,他把許多身段比劃着,但是,他自從商之後,就不曾登過臺,這一份昆生,實在是魯殿靈光、寶島之寶,比起江南俞五來,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的。
俞五在北平的桃色新聞是指不勝屈的,當年他那個少爺公子,和蘇州狀元坊的陸公子麟仲(陸鳳石子)在北平是一對璧人。俞五的昆,以巾生爲傑作,《秋江》《亭會》《拆書》《跪池》都是他的拿手。麟仲則擯長雉尾,《拜月亭》的呂布,尤其是他的絕。
小宴一場,他的翎子,左右翻飛,袍袖舒捲飄忽,據說是徐小香親自教他的。徐小香是和程大老闆(長庚)同臺的人,他是蘇州人,光緒十年間還隱吳門,就留了鬍子,不再唱戲,活到八十多歲逝世。民國初年還看得見他,所以陸麟仲受到徐小香的親炙是可信的。
俞五在北平鬧桃色,是張宗昌正作威福的時代。張宗昌第五妾亞仙老七,卻和俞五熱戀上了。伶人高三奎劉漢臣偷了褚玉璞的姨太太,被褚活埋(一說是槍斃的)。俞五正在六國飯店和亞仙一處,聽見消息,直嚇得連夜南奔。滬上縉紳前輩,漸不直俞五紈絝所爲,而俞五亦漸即窮愁潦倒矣。旋復北上,識其友人陳某之妻日黃曼耘,愛好崑曲,俞五悉心授之,遂成燕好,黃離其夫而隨俞攜一女,見者猶稱之爲陳太太,旋攜陳以俱南,益不得志,乃謀下海,北上求師於程繼仙之門。程爲程大老闆嫡孫,自徐小香、王楞仙而後,繼仙小生已爲獨步。乃悉心以教俞五,俞五聰明人,不耐習苦,稍有所得,爲生活計即欲出臺。繼仙初難之。俞五固請不已,乃自立馬門後,爲之把場。俞五自言,平生雖客串,舞臺經驗,亦夠豐富,南北登場無慮數十百次。可是今天不對了,兩條腿完全鬧彆扭,彈棉花似的,舉步千鈞,隨便怎樣也出不去。程繼仙在馬門後面擰起腿來,向他後面踢。俞五後來常常對人說:“第一次出臺,真比女人難產還難。”
俞振飛、黃蔓耘之《奇雙會》
俞五在北平下海並不得志,上海一班自命清高的親友,甚至票友,則無不驚顧失色說:“怎麼好好的一個俞振飛,也下海唱戲去?”其實唱戲是一種藝術,我倒不反對的。俞五的人緣在昆票時,可說紅遍大江南北,一下海唱京戲,就有許多人批評,搖頭,說他不地道了。平心而論,俞五的唱,在平劇的條件裏實實是不夠的,但是,扮一個安公子,便是扮周瑜,他都行。加以他的崑曲頭銜,世家弟子,也自有一部分觀衆。俞五衣錦還鄉,是幫的新豔秋,在更新舞臺唱全本《連環計·鳳儀亭擲戟》。上海是他的故鄉,人緣就比北邊好得多了,捧俞之盛,並不下於捧秋。於是有人主張俞振飛應該和程硯秋合作,幫新豔秋是太委屈了。
程硯秋小生老搭檔是王又荃,自被新豔秋挖班,才改用顧珏蓀,玩藝兒不錯,材料太臃腫,有點像現在的馬世昌。又荃幫新不久,就告病故。程硯秋果然垂青到江南俞五。他們合作了。可是程硯秋和梅蘭芳一樣的表面大度,裏面小器,凡是跟他唱戲的人,準例不許要一句彩。俞五跟硯秋,硯秋的私房戲,本本排得小生像一個木頭人一般,尤其是唱全本《金瑣記》,叫他扮一個丈夫,剛出臺,過一場就死了。俞五的下海倒黴。說起來,眼淚直可以一把一把地數。上海人還是捧俞五的,便有許多報紙,一例着文主張俞五回南。俞五當初也躊躇到上海不能生活,上海人還是念舊,例如趙培鑫、孫養農、陸菊生,對於他的生活都是極關心的人。俞五果然回南了,這時候珍珠港事件未起,上海已經淪陷,租界還是安樂土,紙醉金迷,酣歌恆舞,並不減色多少。俞五下江南,雖不出臺,名氣的響擋卻是飛黃騰達起釆。趙培鑫特爲他組織一個票房,還請了劉叔詔來教餘派老生,培鑫的棄馬改餘,也就是這個時期開始的。
程硯秋、俞振飛之《春閨夢》
這時繼仙的前胸生着酒杯大的一個疔瘡,我事先沒有前知。演後,繼仙來看我說:“昨兒沒有把它演好,因爲胸口有個瘡,《打侄》一場只好馬虎一點兒了。”其實那一場的演法、神情、跌腿、奪棍、求情已經神妙到秋毫顛,他自己不說,我們哪裏看得出來他有哪一點兒地方馬虎,可是繼仙這次回到北平,就言歸道山,聖藝超羣,從此絕響。我們談了許多關於小生的珍貴軼事。
我問他:“程大老闆晚年和徐小香同班甚久,小香屢次要想辭班回南,大老闆不答應。小香一天私自逃走了。程大老闆還是把他請回去,也不叫他唱戲,請他坐在包廂裏,說:“你要回南,原是人情,只不該破壞了我們三慶的班規。現在我也唱周瑜你看看,沒有了你,我們就唱不成戲嗎?”這天是唱頭二本《取南郡》,程大老闆競唱魯肅,後代周瑜。把一出《取南郡》全唱下來了。也開了後人唱《取南郡》,魯肅、周瑜一個人唱的先例。”
程繼仙、梅蘭芳之《販馬記》
程繼仙說:“沒有的話。曹心泉是小香先生的弟子,民國手裏能談大老班和徐小香的也只有曹先生了。徐小香到北平就沒有回過南,晚年回南,就沒有再到過北邊。大老闆文武不擋,昆亂皆精,確是稟異常人,外邊都說他老人家唱《取南郡》的魯肅和關戲好。其實凡是老生本工的戲,他都會,都行。但是和盧臺子同臺,他就沒有唱過孔明,可知他的戲德高人一等。外邊人又說,大老闆唱過《法門寺》的劉瑾,《白良關》的尉遲恭,《沙陀國》的李克用。曹心泉先生也曾這麼說。可是我生得太晚了,就趕不上知道了。不過徐小香先生在三慶負氣辭班,卻曾有過這一段事實。那還在前頭呢,我也不過聽前輩老先生們說說。”
當時,我請教他是怎麼一個故事。繼仙說:
大老闆執掌三慶,在咸豐年間就做起頭了。小香的年齡比大老闆皆後得多,但是在三慶裏,一位老生,一位小生,也真是牡丹綠葉,相得益彰。年青人不無標勁,小香覺得自己了不起,就和大老闆爭包銀,拿着辭班不唱來做要挾。
大老闆一氣,說:“關他十年功,看他還唱得成,唱不成?”徐小香先生也負氣,竟此辭班八年,除了堂會偶爾參加,就此杜門用功,每天起來頭不去網,足不去靴,拉腿,吊嗓,自己操琴。屋裏立了一面大着衣鏡,忘餐廢寢地對着鏡子,自己揣摹。對人講話,也是搖頭的,他在那裏使翎子。不認識的當他癡子,朋友見了也無不大笑。八年而後,復入三慶,他的名牌真和大老闆雙掛一起。第一天登臺,他指定要唱《借趙雲》而不唱《鎮澶州》,大老闆也依他了(按《借趙雲》是小生正角,《鎮澶州》是老生正角)。
程繼仙的這一席話,使我感到凡一藝術的登峯造極,無不要經過一番刻苦功夫。沒有程長庚的一激,徐小香不會有八年刻苦用功。現在小生行裏提不起這樣一個出類拔萃的人了。
我聽見王瑤青說:“徐小香離開北平,他出世不久,所以趕不上談的。不過聽老輩說,王楞仙的小生算數一數二了,但是梨園的刻薄話,叫他“香灰”。說他是徐小香的灰,又說十個王楞仙,比不過一個徐小香的指頭。徐小香到底好到如何程度,好像說得有些兒神了。不過據曹心泉說,徐小香唱小生是用大嗓的,王楞仙限於天賦,天帶了雌音,後來開了風氣,德瑤如、姜妙香都是青衣改行,才把呂布、周瑜都搞成了雌婆雄了。
陳德霖、王楞仙之《琴挑》
小生唱尖嗓,確有些彆扭,我的意思,當年小生一行都由崑曲改行,崑曲的官生,就是用大嗓唱的,高處彈入雲,如“一彈再鼓”、“冷雨悽風”都用本嗓,沒有假音,用這個尋求徐小香的小生唱法,也許十得其六七了。
現在唱崑曲的,連老生也有用假音的,無怪失之毫釐,相差愈遠了。
(《春申舊聞續》)
懷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