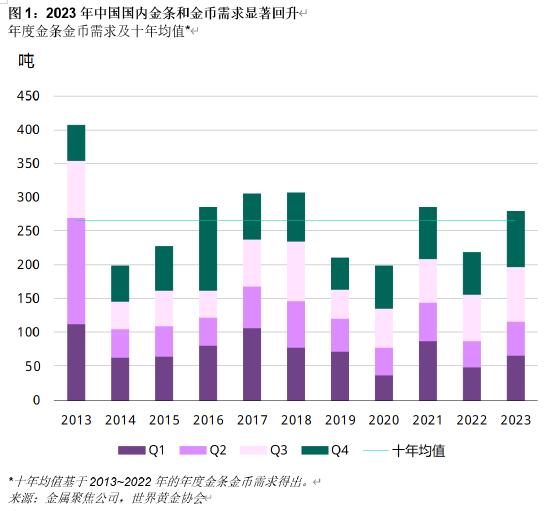敘利亞這片土地上的人,是怎樣活着的?
原標題:敘利亞這片土地上的人,是怎樣活着的?
美國當地時間13日,美軍聯合英法對敘利亞實施“精準打擊”,以作爲對敘利亞“化武襲擊”的回應。14日,美國數十座城市的市民抗議美國總統特朗普對敘軍事打擊。
敘利亞,一個遙遠而模糊的國度。
早在公元前3000年,敘利亞就有城邦國家存在,自前8世紀起,先後被亞述帝國、馬其頓帝國、羅馬帝國、阿拉伯帝國、歐洲十字軍、埃及馬穆魯克王朝和奧斯曼帝國統治。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淪爲法國委任統治地。1946年4月17日獲得獨立。
歷史走到今天,敘利亞現實狀況之複雜遠超一般國家。一方面,在國際上是一個弱國家,另一方面,在國內又實施高壓統治。在情感上,有觀點同情它,也有觀點控訴它。
然而,遠在中國,我們對敘利亞的印象停留在軍事和政治等宏大敘事層面,比如被軍事打擊了,政府與敘利亞反對派產生了武裝衝突。這片土地上的普通人是怎樣生活的?他們是(國際國內)軍事衝突和(國內)高壓政治的實際承受者,更是一個一個鮮活的生命。
阿拉伯語電影《敘利亞的哭聲》(2017)中的一幕。
我們於是去尋找關於敘利亞的書,希望從中理解普通人的生活圖景,他們的日常,他們的思考、愛和自由。只是,原創的和翻譯的都很少,且基本上以通史或政治研究爲主。但有兩本有故事。
第一本《說吧,敘利亞》(Come, Tell Me How You Live)關於法國統治時期的敘利亞。作者是英國偵探小說家阿加莎·克里斯蒂,在二十世紀30年代,她跟隨丈夫馬克斯·馬洛萬到了敘利亞,並寫下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遊記。丈夫是考古學家,她參與了他在敘利亞和伊拉克的每一場發掘。普通敘利亞人的生活形象,在她筆下極爲有趣。
第二本《手中都是星星》則是關於當代敘利亞。作者是德國作家拉菲克·沙米,全書由一個少年數年間的日記組成。在政局動盪的敘利亞首都大馬士革,一位十四歲少年不願像父親那樣做個麪包師,而是夢想成爲一名記者。他擅長寫詩,把自己比作一棵枝葉雜亂的“飛行樹”。在他的摯友沙林伯伯的啓發下,開始寫日記,記錄他的家庭、朋友和學校生活。這是一個倔強的、愛自由的敘利亞少年。
阿加莎·克里斯蒂與敘利亞
作者 | 阿加莎·克里斯蒂
《說吧,敘利亞》
作者: [英] 阿加莎·克里斯蒂
譯者: 何羲和
版本: 上海文藝出版社 2016年5月
阿加莎·克里斯蒂(Agatha Christie 1890-1976),英國女偵探小說家、劇作家。她開創了偵探小說的“鄉間別墅派”,即兇殺案發生在一個特定封閉的環境中,而兇手也是幾個特定關係人之一。點擊標題《阿加莎·克里斯蒂:“人人都有謀殺的慾望”》查看書評君所知道的這位偵探小說家。
他們簡直是謎一樣準點
阿布迪·薩拉姆是個很棒的舞者,在布拉克的夜晚,人們聚集在我們的庭院裏,在阿布迪·薩拉姆的帶領下跳起了複雜的舞蹈——或者說是跳成了某種樣式——有時一直跳至深夜。第二天清晨五點他們又出現在土丘上,這真是個謎。
更讓人想不通的是,住在三十、五十、十公里開外的人每天日出時都能準點到達!他們沒有鐘錶,出發時間也有先後——有的在日出前二十分鐘,有的則提前一個多小時——但就在日出的一刻,他們齊聚到了丘頂,不早也不晚。
同樣令人驚奇的是,收工時(日落前半小時)他們扔掉籃子,笑着,扛着尖鎬,興高采烈地跑——是的,跑十公里回家!他們僅有的休息就是早餐的半小時和午餐的一小時,而且按照我們的標準他們一直都是營養不良的。確實他們幹活的狀態比較悠閒,也就是心血來潮時一鼓作氣幹一陣,但畢竟是辛苦的體力活。挖掘也許是最輕鬆的,鑿松地表後就坐下來抽支菸,等着鏟工將土裝籃。運籃子的小工沒有歇息,除非自己忙裏偷閒。
第一版中文版封面(譯者:肖沉岡;版本:貴州人民出版社 1998年10月),譯爲《情牽敘利亞》。
他們倒很擅長於此,倒土慢吞吞的,翻查個籃子就能花上半天。總體來說,他們是一羣相當健康的人。患眼疾的不少,他們特別關心的則是便祕!我覺得患肺結核的應該也不少,是西方文明帶來的。但他們的恢復能力驚人。一個工人的腦袋被工友割破了,傷勢不輕。工人跑來找我們縫合傷口,我們建議停工修養,他顯得很詫異。“什麼,就爲這個?頭痛都算不上!”兩三天內整個創面就癒合了,儘管他回家後自己的處理肯定是不衛生的。
有個工人腿上長了個很疼的大癤子,馬克斯(即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丈夫——書評君注)打發他回家,因爲他正發着燒。
“工資照付,跟你在這兒一樣。”那人咕嚕了幾句,離開了。但當天下午馬克斯突然看到他在幹活。“你在幹什麼?我讓你回家啦。”
“我回家了,和卓(八公里)。但回到家很無聊。沒人說話!只有女人。所以我回來了。瞧,快好了,腫包已經破了!”
天很熱,我從暗室裏出來時覺得自己就像牆壁上的黴菌。大家忙着供給我相對乾淨的水。先濾掉大團泥塊,再用脫脂棉過濾,分裝到各個容器。處理負片時,至多隻有空氣中的散沙散塵了,結果叫人很滿意。一個工人來找馬克斯,要請五天假。
他們厭倦了荒野的生活回到城市
今天不做工,我們去布拉克做些準備工作。土丘離傑格傑蓋河有一英里,首先要解決的就是飲水問題。我們已派當地人在土丘邊挖了一口井,但水是鹹的,無法飲用,還得從河裏取水。因而便有了索卡西亞人、貨車和水桶(以及馬,而非老婦人)。另外我們在發掘現場還需要一位守夜人。
布拉克遺址。
至於我們自己則打算在河邊的亞美尼亞村莊裏租幢房子。這裏的大部分房屋無人居住。村落的興建最初花了大量錢財,不過並未按照事情的輕重緩急。這些房屋建造時野心過大,空間太大,有過多華而不實的裝飾。這樣經費不夠了,灌溉用的水車——也是村落必需的設施——只好敷衍了事。這個村落開始實行的是集體共有制。工具、牲畜、犁等都由公社提供,生產收益則作爲公社的支出。
然而真正的情況是,人們一個個厭倦了荒野的生活回到城市,離開時帶走了工具器具。結果這些東西需要長期補給,而留下來幹活的人負的債越來越多,這也令他們非常困惑。
水車最終沒能轉起來,村莊也退化成一座了無生氣的荒村。我們租下的房子很氣派,庭院四周有牆,其中一邊有兩層樓高的“塔樓”。塔樓的對面是一排房間,每間都和庭院相通。木匠瑟金斯正忙着修繕門窗,這樣有幾間屋子就可以住人了。
瑟金斯報告說塔樓的房間已經收拾妥當了。我們爬上幾個臺階,穿過一個小小的屋頂平臺,走進兩間屋子。我們都覺裏間可以放上幾張行軍牀,外間則可供我們用餐等。窗戶上裝了幾塊帶鉸鏈可以開合的木板,不過瑟金斯之後會安上玻璃。
阿加莎·克里斯蒂丈夫的考古團隊在對布拉克的遺址進行考古發掘時,出土了大小不一、形狀各異的“眼睛”或“瞳孔”的雕塑物。他們將這個發掘遺址形象地命名爲“眼廟(Eye Temple)”。
邁克爾回來報告說,要他送到丘上的守夜人有三個妻子、八個孩子、許多袋麪粉糧食,以及一大羣牲口。不可能把他們全捎上車。他該怎麼辦?
他帶着三敘利亞鎊又出發了。馬克斯讓他帶上他能帶的,其餘的東西可用驢子運。索卡西亞人突然趕着運水車出現了。他唱着歌,揮着長鞭。
貨車漆成了亮藍色和黃色,水桶是藍色的,索卡西亞人又穿着高筒靴和鮮豔的衣服。整個場面比以往更像是一幕俄國芭蕾。索卡西亞人搖搖晃晃地下了車,揮着鞭子,繼續唱着歌。他顯然是喝得爛醉了!
敘利亞首都的一個追夢少年
作者 | 拉菲克·沙米
繪 | 麼麼鹿
《手中都是星星》
作者: [德] 拉菲克·沙米
繪圖:麼麼鹿
譯者: 王潔
版本: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16年1月
拉菲克·沙米(Rafik Schami),德國作家,1946 年生於大馬士革。1982 年投入文學創作,主要用德文寫作,也用阿拉伯文。他的一系列帶有阿拉伯色彩的作品已被翻譯成20 餘種語言。
如果我能成爲記者該多好!
“記者到底是什麼?”我問,我只知道記者負責寫報紙上的文章。
“噢,記者,”沙林伯伯回答,“記者是非常勇敢聰明的人。他只要用一張紙和一支筆,就足以讓政府、軍隊和警察畏懼。”
“只用紙和筆?”我驚訝地問。每個學生都有紙和筆,但我們連學校門衛的心也打動不了。
“是的,記者能讓政府有所警戒,因爲記者不斷地追求真相,而政府總是想盡辦法隱藏真相。記者是個自由人,就像馬車伕一樣,活在危險中。”
如果我能成爲記者該多好!
翅膀襪子報;繪:麼麼鹿。
聽沙林伯伯講起他的故事
“你覺得你快要窒息,是因爲你已經放棄希望。沙林從來不輕易放棄。我曾經挨餓受凍,像狗一樣在山中生活,只因爲我不想加入軍隊;我也曾想過結束這種沒有尊嚴的生活去從軍,但我還是堅持下去,認真思考該如何渡過這個難關。春天來時,有個牧羊人經過,給了我一些食物喫,並請我爲他工作。”
我沉默了好一陣子,沙林伯伯繼續講着:“他給我假造了文件,因此有五年的時間,我的名字不是沙林,而是穆思塔法。牧羊人的生活其實並不壞。我的很多朋友一開始都取笑我,後來他們全後悔了,因爲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他們中有人受傷,有人失蹤或是陣亡。但牧羊人一直都衣食無虞。你應該再想想看,怎樣可以不用逃跑,也不用去麪包店工作。你頭腦不錯,對大馬士革也很熟,看看能不能想出個好主意來,或者我們可以一起想個好辦法。沙林一向最會謀劃了。而你呢,我的好友,你一定會成爲一名記者的,這點我很肯定。”
友誼與擁抱。繪:麼麼鹿。
我其實並不相信他說的會成真,但他告訴我:“試個半年好了,今天是二月二十六日,六個月之後,我們再坐下來談談,如果情況還是沒有改善,那麼我就親自幫你提皮箱到車站,你要去哪裏都可以。這樣要求會不會太過分?半年!”
好吧,既然這樣,我就待在大馬士革想辦法。反正過六個月我再逃跑就是了。“發誓?”沙林伯伯問。“我發誓!”說完我又爬回牀上睡去了。
我生命中最美好的一天
今天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一天。連續兩節阿拉伯文課讓我獲益良多,這是以前從來沒有過的。全班同學都即席講演自己的題目。卡提布老師坐在我們中間,和我們熱烈地討論或辯論我們寫的故事、童話和詩。輪到我時,我朗誦了《我大聲做夢》和《飛行樹》兩首詩,我已記得滾瓜爛熟。老師覺得我的詩寫得特別好,還說我心裏有個詩人在說話。
我覺得自己一定臉紅了。瑪姆德說我朗讀得很好,雖然我有時聲音太大,讓他耳朵發痛。
甚至下課鐘響了,我們還繼續把課上完,好讓最後五位同學能夠有機會朗誦自己的作品。要是在以前,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我們總是在下課鐘響前,心就飛到操場上去了。
樹;繪:麼麼鹿。
我最好的朋友永遠也不會回來了
今天我發現沙林伯伯說錯了一件事。“死亡,”他有一天說,“就像睡了長長的一覺。”他錯了,死亡是最後的階段,它帶領人們通往某處,再也不會回來。沙林伯伯很可能在樹木、花朵和薊草中繼續活着,每種植物從土中吸取他身上的一部分,再傳遞下去:樹木像他一樣爲人提供蔭庇和安全感,花朵獲得芳香和色彩,薊草則像他一樣有着尖刺和頑強的抗爭心。但這個世界上再也沒有一個生物能夠變成像沙林伯伯那樣的人。
沒錯,我最好的朋友永遠也不會回來了。我覺得好孤單。我愛瑪姆德和娜緹亞,我也非常尊敬哈比比,但沙林伯伯在我心中的地位是無可取代的。
沙林伯伯的鑰匙
“看到這把鑰匙沒有?”他說,“這是我的馬車鑰匙。我當時不得不賣掉所有家當,就是不願意交出這把鑰匙。”他把鑰匙放在一旁,從盒子裏拿出一顆彈珠。“這是我小時候玩的彈珠。這是我的最愛,每次我只要搓搓它,玩遊戲的時候運氣就特別好。”
接着他又從藏寶箱裏拿出一小段乾枯的樹根。“這樹根來自我以前躲藏的那座山裏,這棵植物每年都會被砍,但它總是會再長出來。它怎麼樣都不會被殺死。農夫們會把這種樹根隨身放在口袋,因爲它可以帶來生機。在我逃亡的五年裏,我總是帶着這段樹根。還有這枚金幣,是一個我曾救過的搶匪送給我的。他囑咐我把這枚金幣交給一個走投無路的人。我到後來才意識到,這個搶匪是多麼有智慧,因爲每當我想把這枚金幣送人的時候,總會試着幫那人找出路,也終究會找到出路。”
行李;繪:麼麼鹿。
沙林伯伯沉默了好一陣子,好像在想該許什麼願一樣。“朋友,”他最後終於開口,“我希望你能把這顆彈珠、這把鑰匙還有這段樹根放進我的墳墓陪我。至於金幣,我把它交給你,同樣也把那搶匪的囑咐託給你。”
沙林伯伯的墳墓
今天我到墓園,到沙林伯伯樸素的墳墓前。他的墳墓,和賦予他生命與最終歸宿的大地融爲一體。我在他的墳上放了五朵紅玫瑰。
哈比比的事讓我非常難過,但我還是要快樂地活下去。我不願意放棄任何希望,這是我的老朋友沙林教我的。
“任何事物都會成長,”有一天他告訴我,“任何事物都會成長,除了災難。災難剛發生時最嚴重,但隨着日子一天天過去,它會越來越小。”
墓;繪:麼麼鹿。
本文內容經上海九久讀書人文化實業有限公司與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魔法象授權整合自《說吧,敘利亞》與《手中都是星星》。作者:阿加莎·克里斯蒂;拉菲克·沙米。繪:麼麼鹿。整合有刪減,標題爲編者所加。整合與編輯:西西。未經新京報書面授權不得轉載,歡迎轉發至朋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