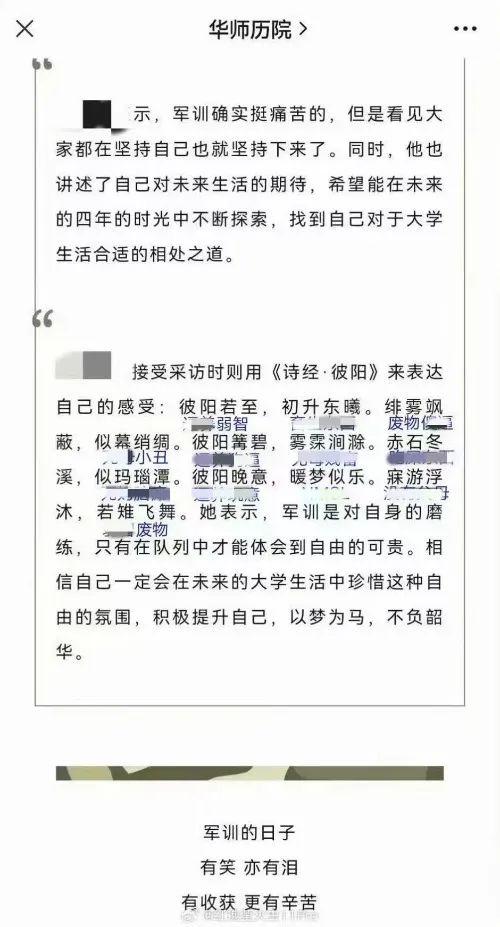陈第:理也者,气之条理也(下)韦力撰
摘要:来到官岭村,在村边遇到一位老人,我向他请教如何找到陈弟墓,老人把我带到了村中央,在中央的十字路口上看到了立在正中的“明一斋陈先生墓道”碑,把墓碑立在村的正中央,此种作法颇为奇特,老人向我解释说,文革中来了很多人,把陈第的墓道全部砸烂了,30多年前从外面来了一个人,此人来到村中后,到处寻找陈第墓的遗迹,后来他从某家的院墙上找到了这块碑,就自己出钱竖在了这里。村中的路都很窄,并且弯弯曲曲,绕来绕去,老人把我带进了一户人家的屋中,一位老年妇女接待了我,她听带路的老人讲到了我的诉求后,坚持让我坐下喝一杯热水,她解释说陈第的墓在29年前县里面来人进行了修复,修复后这块地正好划在了她家的地界内,于是文物部门就指定由其家来代管,其丈夫很是尽职尽责,每年都到陈第墓上去除草,后来发觉完全无人过问这件事,就再也不管了。
除了前面提到的吴棫,同时还有明代的杨慎,他们都对叶音这种说法表示怀疑。到了明晚期,焦竑也怀疑叶音这种说法,可能是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陈第,而陈第经过一系列探讨,认为叶音说根本站不住脚。林海权在《论陈第对我国古音学的贡献》一文中,引用了陈第在《毛诗古音考自序》中的一段话:“夫《诗》,以声教也。……田野俚曲,各有谐声,岂以古人之诗而独无韵乎?盖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亦势所必至。故以今之音读古之作,不免乖剌而不入,于是悉委之叶。夫其果出于叶也?作之非一人,采之非一国,何母必读米?非韵杞、韵止,则韵祉、韵喜矣;马必读姥?非韵组、韵黼,则韵旅、韵土矣;京必读疆?非韵堂、韵将,则韵常、韵王矣;福必读逼?非韵食、韵翼,则韵德、韵亿矣。厥类实繁,难以殚举。”
陈第认为随着时代的变迁以及地域的特色,今古音不同是一种必然,当读出不同音调时,用不着为了诗句的押韵而变更某个字的读音。接下来,他举了几个例子,其中他提到了“福”的本音应当读作“逼”。陈第同时认为,“服”也读“逼”音,陈第做了大量的考证,而他的这些考证也多为后世所引用,我节选其所举例句如下:
《关睢》:“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有狐》:“有狐绥绥,在彼淇侧。心之忧矣,之子无服。”
《葛屦》:“要之襋之,好人服之。”
《蜉蝣》:“蜉蝣之翼,采采衣服。心之忧矣,于我归息。”
《候人》:“维鹈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称其服。”
陈第撰《毛诗古音考》照旷阁《学津讨源》本,卷首
陈第在《毛诗古音考》卷一中为了考证“服音逼”,他从《诗经》中找出了14个例句,以此来证明“服”确实读“逼”,他把这样的例句称之为本证。而后他又从另外的书中找出了10条证据,我转引《宋明理学新探》中的三个例句如下:
《易·谦二三》:鸣谦贞吉,中心得也。劳谦君子,万民服也。
《豫·彖》:天地以顺动,故日月不过,而四时不惑,圣人以顺动,则刑罚清而民服。……
魏繁清《定情》诗:日夕兮不来,踯躅长叹息,远望凉风至,俯仰正衣服。
陈第把在其他书中找到了这些证据称之为旁证,而后他用归纳推理的方式证明“服”字的古音确实读“逼”。对于他发明的这种方式,焦竑在给陈第写的《毛诗古音序》中说:“取诗之同韵者,胪列之为本证也。取《老》、《易》、《太玄》、《骚赋》、《参同急就》古诗谣之类,胪列为之旁证。今读者不待其毕,将哑然失笑之不暇,而古音可明也。”
陈第公园大门口
从福州打车来到了连江县,在这里找到了陈第公园,看到了他的巨形雕像,而后又几经周折,在某个军队的院门口找到了陈第故居原用的石井圈,之后就驶出连江县城,前去寻找陈第墓。
陈第雕像足够威风
陈第墓位于福建省福州市连江县官岭戈沃山中。从连江县城出来向东北方向行驶30余公里,道路是沿着大海边铺设,四车道的水泥路面,宽敞而平坦,司机说此路是刚修好的,以前的旧路在山上很难走。行驶在山海之间,果真令自己的心情大感惬意。
榜磅井
在村中央看到的陈第墓道碑
来到官岭村,在村边遇到一位老人,我向他请教如何找到陈弟墓,老人把我带到了村中央,在中央的十字路口上看到了立在正中的“明一斋陈先生墓道”碑,把墓碑立在村的正中央,此种作法颇为奇特,老人向我解释说,文革中来了很多人,把陈第的墓道全部砸烂了,30多年前从外面来了一个人,此人来到村中后,到处寻找陈第墓的遗迹,后来他从某家的院墙上找到了这块碑,就自己出钱竖在了这里。
我向老人请教,为什么墓道碑竖在了这里?
墓道碑的背面
老人又说陈第墓原来很大,上面有许多雕刻漂亮的石条,但文革中已经拆毁了,我跟老人说,自己查过资料,陈第墓在80年代就被评为省级文保单位,这是文革之后的事情了,因此这个墓不可能完全没了痕迹,老人反驳我说:“文物部门也不一定干正事儿,砸烂文化的本来就是文化人。”这真是很有哲理的一句话,我仍然不死心,希望能找到陈第墓的原址,老人想了想说,我带你去见一位知情人。于是我跟着他前往,在路上他说自己姓游,其称自己的哥哥在北京朝阳区,自己去住过三个月,同时他又说,本村很大,有三千多人,都是靠渔业为生,并且告诉我,这里离马祖不远,如果登上戈沃山,就能看到马祖的一个岛,本村人都很有钱,而他自己也盖了两座小楼。
村中景象
墓道碑旁边一户人家的门牌
村中的路都很窄,并且弯弯曲曲,绕来绕去,老人把我带进了一户人家的屋中,一位老年妇女接待了我,她听带路的老人讲到了我的诉求后,坚持让我坐下喝一杯热水,她解释说陈第的墓在29年前县里面来人进行了修复,修复后这块地正好划在了她家的地界内,于是文物部门就指定由其家来代管,其丈夫很是尽职尽责,每年都到陈第墓上去除草,后来发觉完全无人过问这件事,就再也不管了。
到此时我才明白,为何游老先生把我带到了这里,于是我提出请其丈夫给我带路,老妇人解释称,自己丈夫80多岁了,爬不动山了,但她可以让儿子带我去。说完话,她立即给儿子打了个电话,然后向我解释说她有六个儿子,打电话的是长子,因为长子去过陈第墓。
十余分钟后,其子返回了家,此人看上去约50多岁年纪,人长的很是憨厚,不太言语,于是我们共同走出村,上车后带着我和刚才的那位老人一同开上了戈沃山,在半山腰无路之处停下,踏着石块穿过一条小河,走入了对面的山坡。
山路上长满了三米多高的芦苇,因为这个缘故,所以走到近前就完全看不到方向,只能沿着前人踏出的小径一路上行,然而脚下的小径却时断时续,好不容易攀爬上几个陡坡,却发觉走错了路,于是又原道返回。上去不容易,下来也同样困难,因为很多小径其实根本不是路,要用人的身体在地上爬行。
上山的路
在芦苇丛中钻行
为何路途如此艰难?带路者向我解释说,因为山上野猪多,相关部门又不允许打野猪,在山上种的地大多都被野猪吃了,于是村民就不再种地了,所以山里面的地大多变成了荒草。
从野猪开出的洞爬过
既然是这样,那也只好忍受着眼前的一切,这样往返折腾了一个多小时,在荒芜丛中的洞中钻来钻去,带路者说这就是野猪拱出的道路,我真担心今天和这些野猪狭路相逢,据说野猪的凶猛程度比狼还要厉害。
经过艰苦的爬行,总算找对了大致的方向,爬到半山腰时,带路者指着远方告诉我说,前面的那片松树林就是陈第墓所在。顺其指的方向望过去,原来陈第墓离我的脚下还有着很长的一段话,而最为艰难者,是眼前看不到前行的路径,因为芦苇丛生,其实带路者也仅凭直觉在芦苇内转来绕去。虽然这样,但总算看到了目标,似乎腿上的力气也有所增加,于是努力地向上攀登。
在山坡上看到的棺材
在爬山的路上,还看到一口棺材放在了一块平地上,棺材上蒙着帆布,没有进行掩埋,不明白这是当地的什么风俗,我也没顾上问,继续向上爬,终于听到了带路者在前面喊:“找到了!”
终于看到了陈第墓的文保牌
陈第墓在一个小山头的顶上,四周长满了芦苇,即使离此两米远的距离也难以发现,如果不是遇到在情人,我估计排来一个连队都不可能找到这里来。我在墓前首先看到了立有一块文保牌,此牌是连江县政府1984年所立,我想起那位带路者的母亲所说的29年,从1984年到2013年确实是29年,我惊异于老妇人计算的如此之准,墓的面积不大,前面有块小平台,约20余平米,后面的墓穴嵌入山体中,墓碑的前面写着“明一斋陈先生”底下还有两字看不清楚,年代似乎是“天启癸亥”,后面的落款为“友人黄淙门人徐亮造”。
陈第墓外观
拍照完好原路下山,仍然难以找到路径,并不比下山容易,还是在芦苇丛中,向着大概的方向钻来钻去,好在有了结果,心境也变的与上山时不同,于是我三人边走边聊天。因为聊天的分心,我不小心摔了一脚。
墓碑
芦苇丛中
虽然这跤摔的不狠,但芦苇却把我的手腕划出了一条长口,幸亏不深,但汗水渗入伤口是,让我有着钻心的疼,可惜创可贴没带在身上,王官云看到这种情形,顺手撕下一块芦苇叶,接着他又在芦苇叶上吐了口唾沫,不由分说的给我包在了伤口上,并让我用左手用力按住, 说过一会儿就能止血。到这种地步,也只能用“恭敬不如从命”自我安慰了。
另一个角度
爬过的路
重新上车,将那位带路的老人送回村内。这位老人的体力让我着实佩服,我觉得她的年龄至少在70开外,然而她跟着我上山下山却并不显得有多么吃力,送到她家门口时,我掏出100元表谢意,老人向我摆摆手,而后指着靠边的楼房说:“这几座都是我们家的。”这让我拿着钱的手都不知道怎么放回来,于是郑重地向老人表示了谢意,而后上车再把老妇人的长子送回家。
回到了山底
因为有了刚才的尴尬,这使得我不知应该掏出多少钱酬谢才算合适,于是我向其长子征询意见,他坚决说不可能收钱,这让我觉得特别过意不去。他见此况跟我说:“那咱们就去吃顿饭吧。”于是我心领神会,虽然我本想接着赶往下一程,但既然对方提出这样的要求,我当然要去消费一番。
在路上,我与他聊天,他说自己叫王官云,其实我有个疑问,那就是陈第的墓在他家的山地范围内,为何前来寻找却如此的费力?他说在此前其实仅来过一次,并且也是请一位在山上放牛的人带路才找到者。坐在车内,我又感到了伤口的疼痛,王官云安慰我不要急,到达饭店后他再帮我包扎。我们的车按照他的指挥又回到了村中,而后沿着村边的路驶往了我前来时的省道。
王官云带我来的饭店就在省道边上,从外观看,是二层小楼,营业面积不小,我跟王官云说自己急着赶路,不要准备其它的太多菜,我的潜台词是点几个他所喜欢的菜就可以了,然而他坚持要喝酒,我说自己的确不能喝,如果愿意,他可以多点两瓶带回家去喝,而我只想吃碗面以便于下面的行程,他同意了我的建议。
在等面的过程中,王官云找来了一些纱布要给我包扎,我告诉他车上的包内有很大块的创可贴,于是请司机拿来包,我把自己的手包好。而后催促王官云多点几瓶他喜欢喝的酒,他听到我的催促后却始终没有反应,我猜不透他是怎样的心态。
等面端上来时吓了我一跳,是满满的两大盆,王官云说自己吃了饭了,这是给我和司机点的,一人一盆,盆里面除了面条还有很多的添加物,有很大个的蛏子、鱿鱼、海虾,还有各种不知名的青菜,喝了一勺汤,似乎也是用海鲜特制的,这种面做的的确味道鲜美,这可以说是我在此之前吃过的最好吃的一种面,因为盆太大我要了一个碗,一碗碗的盛出,竟连吃了五碗,我第一次知道自己有这么大的饭量。
这碗面撑的我都难以站起身,我大夸这里的面做的如何之好,同时再次催促王官云多拿几瓶酒,如果他喜欢这里的饮料,也可以搬两箱,我说他拿好后我可以去结账,到这时,王官云才告诉我,这家饭店是他儿子开的,所以他用不着在这里拿任何东西。
这个结果让我有些意外,因为我不知道应该如何酬谢王官云所付出的辛劳,他跟我说,我能前来寻访陈第已经让他很感动,所以他不会收什么带路费。看来他对陈第这位古代前贤也有着本能的敬意,这一点我倒是能够理解,但饭钱总要结,于是我问他儿子一碗面多少钱,他儿子也坚决不收钱。
没办法,只好扔在柜台上200块钱跑上了车,王的儿子追着出来,而后把钱塞在了车玻璃缝上,他不断的说:就是吃碗面怎么能收费呢。吃饭结账本就是天经地意,带路就付出了那么多辛劳,饭钱还不结,这让我心里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然而他的举措是如此的坚决,完全不是虚让,眼前的这种推让让我不知怎么办。
司机劝我不要再推让,这让我的心态很是难受,因为我认为王官云的意思是不好意思收带路费,就把我带到他家的餐馆进行消费,我觉得这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心态,并且认为自己这么做也是心领神会,没有想到他的热情是一片纯真,完全没有我所自以为理解的世故,这让我想起自己对他的揣度就感到羞愧,看来是我的心态太肮脏了,以至于把别人看的也是如此。
在他们父子的坚决推让下,我只好下车,郑重地表示了我的诚挚谢意,王官云向我摆摆手说:“你去忙自己的事情吧。”他的神态像刚才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我只好重新上车,不断地向他们摆手,而后驶出了院落。
在路上我跟司机讲述了自己的这种心态,司机安慰我说没关系,等你回北京后能跟文物部门提提建议,再把陈第墓重新修整起来,我觉得司机说的这个建议不仅是一种安慰,因为在找墓的过程中王官云一直在跟我说,要能把这个墓整修好,就是他的希望,陈第与他无亲无故,他能对于这位连乡贤都不算的古人,有如此的憧憬之情,这种发自内心的尊重前贤真的让我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