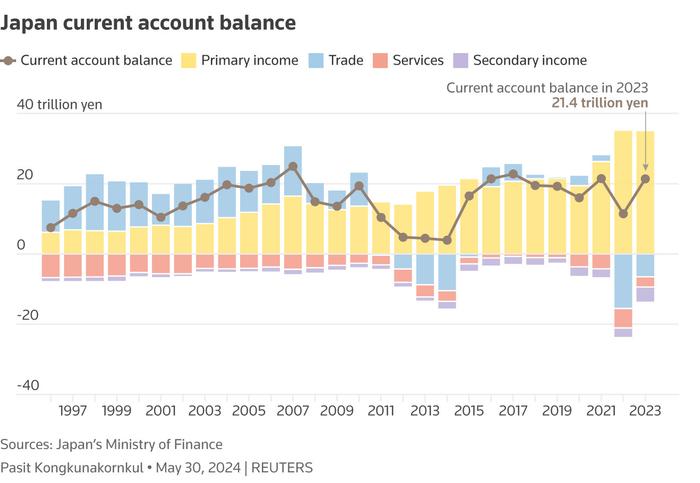譯史||往昔還看今朝——聽退休教授張培基講述“東京審判”故事
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週年紀念日即將到來之際,爲還原更真實鮮活的歷史,激發大學生愛國主義熱情,英語學院分黨委副書記徐文兵帶領英院學生幹部專程採訪了曾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擔任英文翻譯並親身經歷過東京審判的退休老教授張培基先生。
張培基(1921-),福建福州人,中國著名翻譯家,傑出教授。早年移居上海,在那裏接受了初等和中等教育,1945年畢業於上海聖約翰大學英國文學系。先後在解放軍洛陽外國語學院、對外經濟貿易大學任教,1991年退休。他的名字已經被列入《中國翻譯家詞典》,在當今中國翻譯界有着重要的地位。
張培基先生在赴日本擔任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英文翻譯之前,已經從上海聖約翰大學畢業,並在上海工作,擔任《自由西報》(英文)記者、《中國評論週報(The China Critic)》特約撰稿、《中國年鑑》(英文)副總編等職務。
由於東京審判檢察官表示人手不足,便由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美國檢察長季南(Keenan, J.)主持,從上海招募人員協助工作。報界老前輩桂中樞先生作爲季南先生的老同學,推薦了張培基先生前去。我國在國際軍事法庭的檢察官向哲浚先生還親自到上海找到張培基先生等人,從報紙上摘錄一段話讓他們進行翻譯,通過測試之後,張培基先生一行才被正式錄用。
上圖:1946年-1948年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工作人員舊照(右一爲張培基)
下圖:張培基教授近照
東京審判從1946年5月開始,直到1948年11月結束。張培基先生1945年開始參加前期準備工作,從1946年月至1947年都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擔任中國檢察官的助手,工作時間共計2年7個月。工作包括翻譯相關材料和檢察官之間的來往備忘錄等文件,以及幫助整理資料。由於人員緊張,張先生工作十分繁忙,一工作就是一整天。對於喫住的問題,張先生表示一切都由公家提供,沒什麼不習慣,跟着檢察官一起喫,頗爲講究。
拒張先生回憶,戰後的東京早已被轟炸得一片狼藉,而令人稱奇的是國際軍事法庭所在的建築卻完好無損,與周圍環境形成了鮮明對比。這棟樓戰前是日本士官學校,戰爭期間是日本陸軍軍部。
由於工作允許到庭上觀察審判情況,張先生親眼看到了受審的28名日本戰犯。他們面對法官分坐幾排,後面還有一排美國憲兵監視他們。他們態度狡猾,拒不認罪,每人手裏拿着一個布包,裏面裝的是受審時將用到的文件材料。整個審判尤其重視兩個人:關東軍司令板垣徵四郎和特務頭子土肥原賢二,其中土肥原賢二便是令中國百姓談虎色變的“土二爺”。審判結果是7人絞刑,包括臭名昭著的東條英機、板垣徵四郎、土肥原賢二和南京大屠殺製造者松井石根、外相廣田弘毅。死刑犯後來都被關押在東京郊區的監獄裏並被行刑。
審判期間尤其使張先生記憶深刻的一件事是末代皇帝愛新覺羅·溥儀出庭作證。溥儀於1945年被蘇聯紅軍帶到蘇聯,後來中、美、蘇商量好傳喚他作證,起先並不知道自己證人身份的溥儀到庭以後“像看戲一樣”。他一度害怕這一回來會被中國方面判刑,後來才瞭解到是要利用他控訴日本戰犯。他穿着藏青西服,帶着黑框眼鏡,滿口京腔,身後站着兩個日本憲兵,後面還跟着一個蘇聯軍人。溥儀講述了日本人把他從天津弄到大連,再到長春做傀儡皇帝的事情。談及日本人毒死了他患病的愛妻並強迫他娶日本老婆時,他更是怒不可遏,激動地拍着桌子。溥儀表示他作爲名義上“僞滿洲國”的“皇帝”,毫無自由,處處受限,“簡直是猴戲”,以此控訴着戰犯土肥原賢二等人的罪行。溥儀在軍事法庭上連續作證8天,創下了證人作證的時長記錄。審判結束後溥儀回國,中國政府對他很寬待,既往不咎。
張先生還談及在2006年時,中國電影博物館舉辦了電影《東京審判》的看片會,時任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中國法官的梅汝璈的兒子梅小璈和張培基教授作爲親歷者,也被請到了現場。看罷電影,張教授提出了兩點意見:一是戰犯手裏會拿布包、後面會站一排憲兵和法庭的真實佈置等細節在電影裏沒有反映出來;二是法庭用語不夠規範,例如每次開庭前有一位美國軍官喊“全體起立”被翻譯成 “all personnel stand up”;之後法官喊的“全體坐下”翻爲 “all personnel sit down”。 “Stand up”和 “sit down”在口語裏很常見,但法庭上就應該用更正式的 “rise”和 “be seated”。法庭用語與日常用語應該進行區分。張先生認爲電影就要如實地反映歷史,切不可隨意更改。
張培基教授與英語學院分黨委副書記徐文兵及學生合影
在採訪的最後,張培基教授特地提醒年輕人,不光要學習書本知識,更要多關注國內外大事,多讀書報。
本文來源:對外經貿校新聞網
轉自:翻譯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