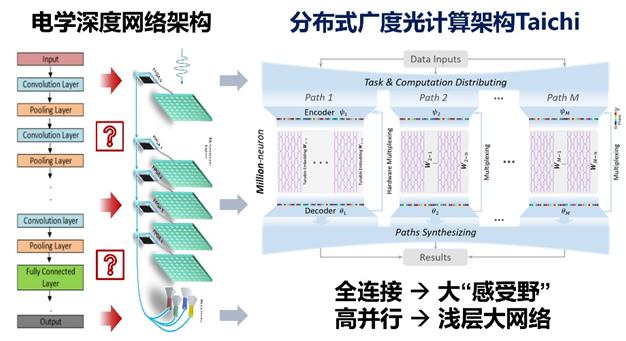1976年9月悼念毛澤東紀實
摘要:下午2時30分,清華大學黨委召開黨支部書記以上幹部會議,800人蔘加,遲羣宣佈了毛澤東逝世的消息,整個會場一片哭聲。”下午4時,廣播了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中央軍委發佈的《告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書》,宣告了毛澤東逝世的消息。
1976 年 9 月 18日, 華 國鋒在 毛澤東追悼大會 上致悼詞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逝世,幾十年來唱着“毛主席, 愛人民……他是人民大救星”的全國人民立即陷入悲痛之中。八億人民“淚飛頓作傾盆雨”。
發佈毛澤東逝世的消息
毛澤東身體原本健康,73歲還能橫渡長江。他的健康惡化,主要是由於林彪事件的打擊,此後病魔纏身。
1976年天安門事件以後,毛澤東的病情進一步惡化。6月1日,毛澤東心肌梗死嚴重,中央向全國各省、市、自治區及各大軍區的領導,通報了他的健康狀況。8月, 中央三次發出特急電報,向有關領導通告毛澤東病危的消息。
9月8日0時至16時37分,毛澤東偶爾甦醒,還要看文件,看書。
9日0時10分,毛澤東的心臟停止了跳動。
中央政治局委員在向毛澤東遺體默哀鞠躬後,立即研究治喪及遺體保存問題,組成了以華國鋒爲首的治喪委員會,並向全國主要機關部門包括各省、市、自治區的負責人通告了毛澤東逝世的消息;要求各地各部門對有關幹部,分層次迅速進行祕密傳達。中共中央、中央軍委下達了《關於加強戰備值班的指示》:“從9月9日上午8時起,全軍進入一級戰備。”
早在7月下旬,周啓才 (中央辦公廳祕書局局長) 和李鑫 (中央辦公廳副主任) 就接受汪東興的指示,起草了訃告《告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書》和悼詞文稿。9月9日晨5時餘,政治局討論通過了他們起草的訃告,並決定當天下午4時對國內外廣播。
下午3時,中央人民廣播電臺開始連續預告:“本臺今天下午4點鐘,有重要廣播,請注意收聽。”下午4時,廣播了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中央軍委發佈的《告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書》,宣告了毛澤東逝世的消息。下午6時、8時分別增加播出關於治喪活動五項決定的《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中央軍委公告》和毛澤東主席治喪委員會名單。此後,每小時廣播一遍。
10日晚,毛澤東的遺體從中南海住處移出,安放在人民大會堂北大廳的靈堂內。
16日下午3時,政治局開會討論悼詞文稿,商定18日在天安門廣場舉行追悼大會的有關事項,決定追悼大會由華國鋒致悼詞, 王洪文主持,並對大會程序作了安排。
自10日起至月底,全國報刊、廣播、電視,主要報道與毛澤東逝世有關的消息。
少數人較早得悉消息時的悲痛之情
實際上,當時人們從報紙上的新聞圖片和新聞紀錄電影上,已看到了毛澤東的衰老形象。翻譯家沙博理 (中國籍猶太人) 記述:“至少已有一年之久,我們知道他將不久於世。但是到最後他逝世時,我們仍感到震驚。”
最早直接從中央方面得悉毛澤東逝世消息的“局外”人,應該是當天凌晨被通知處理毛澤東遺體保存問題的衛生部部長劉湘屏,醫學科學院的楊純、徐靜。他們都感到十分突然,徐靜的腦子裏頓時一片空白。
時任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副臺長的楊正泉,早晨5點多鐘到臺長辦公室開緊急會議, 聽到毛澤東逝世的消息後,他“周身的血液像凝固了似的,木然地站在那裏,淚水順着面頰流了下來……”他向即將參與播音的有關人員傳達了毛澤東逝世的消息,“大家都極其震驚,有的泣不成聲”。
當時在中央軍委辦公廳從事機要工作的傅學正早些時候就得到通知:不要出門, 說不定有急事找你。9日上班,得知全軍進入一級戰備。他聯想起7月6日陳錫聯在一次會議上,講了毛主席病重,又聯想到近來總有中央發給駐京大單位領導人的“絕密”“親啓”的文件,就猜測可能是毛主席出事了。
隨後,駐京軍事單位的領導人被召去西山會議廳開會。傅學正被安排去給軍委顧問、外地來京的大軍區首長傳達中共中央的急電。他接過電報一看,“頭嗡的一聲大了,毛主席去世了。我鼻子一酸哭了”。傅先後給劉志堅、譚政、李聚奎、李志民、陳再道等7人分別傳達了電文,他們都很悲痛。劉志堅聞訊,猛地站起來,流着淚不停地在客廳裏踱步;譚政則“一下子斜臥在沙發上,面色蒼白,喘不過氣來”。經醫生救治後,他不停地嘆氣、流淚。
在301醫院住院的傅崇碧接到軍區機要員送給他的絕密文電,得知毛澤東去世。他悄悄地告訴了一同住院的張愛萍和王震。他回憶說:“我們的心中都無法平靜。我們這些跟隨毛主席出生入死一輩子革命的紅軍老戰士,儘管在‘文化大革命’中受過不公正的待遇和迫害,但是,對毛主席深厚的熱愛、敬仰之情,是永遠不會改變的。”
中午,黑龍江省委常委蘇民通知在省委、省革委會任職的範正美:“告訴你一個極其悲痛的消息,主席去世了。”範正美一路眼淚長流,不知道自己是怎麼回到北方大廈的,“到了會場,我向大家報告了這一不幸消息,情難禁,見着與會者一個個震驚、悲痛的神情,我還是失聲痛哭,臺下也是一片哭泣唏噓聲”。
下午2時30分,清華大學黨委召開黨支部書記以上幹部會議,800人蔘加,遲羣宣佈了毛澤東逝世的消息,整個會場一片哭聲。
下午3時30分,張光年被接到《詩刊》編輯部,“王春同志向我和葛洛、孟偉哉宣佈中央通知,頓時泣不可抑”。
作家浩然下午去會議室,“一進門,只見局裏的吳林泉、石敬野、耿冬辰和田藍幾位領導同志,呆坐在那兒,一個個淚流滿面,我這才得知偉大領袖毛主席逝世了! ……聞知噩耗,我一邊擦着眼淚,一邊開始考慮寫悼念毛主席的文章”。
當時北京的一位中學生蔣健看到,凌晨一架接一架的飛機掠過城區的上空,這是從未有過的事。他感覺,看起來是出大事了。沒到上班的時間,軍人們就被緊急召集去開會。大概在下午3點的時候,北京50中和108中的主樓頂上突然升起國旗,又突然降了半旗。幾乎與此同時,附近的大喇叭突然響了起來,反覆說:“今天下午4點鐘,有重要廣播,請注意收聽!”他猜想,一定是毛主席去世了。
收聽訃告後北京各界人士的悲痛之情
9月9日下午4時整,中央人民廣播電臺開始廣播《告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書》。
楊正泉記述:“全國人民震驚了!八億人民爲失去自己敬愛的偉大領袖極其悲痛! 還沒有收聽完第一遍廣播,便紛紛打來電話,傾訴悲痛之情,寄託哀思。全世界震驚了!開動一切宣傳機器,作爲特大新聞紛紛報道,一些國家和政府的首腦、政黨領導人、社會團體和知名人士接連發表談話、打來唁電錶示極其沉痛的哀悼。”
朱德夫人康克清失聲痛哭:“大半年裏,三個偉人,周恩來、朱德、毛澤東相繼去世,我們的黨和國家損失實在太大了。”
作家茅盾無比悲痛,思緒萬千。
作家葉聖陶在日記中寫道:“巨星隕落,非止我國,舉世將永遠追念。”
人民日報社副總編輯李莊“腦袋頓時一片空白”,他跌跌撞撞回到宿舍,十幾分鐘的路程竟走了一個多小時,想回東單煤渣衚衕卻走到了東四。之後,他折回宿舍,關起門來,自飲祭酒,“多麼苦澀,多少聯想。曠世偉人走了,留給後人無窮留念……”
趙樸初、馮友蘭、蕭軍等人寫輓詩誌哀。張伯駒寫的輓聯是:“覆地翻天,紀元重開新史;空前絕後,人物且看今朝”。
鄧小平女兒鄧榕在院子外面,突然聽見遠遠地傳來奏樂的聲音:“仔細一聽,是哀樂!我趕緊跑到屋裏,告訴父母親。我們一起打開收音機,驟然間,聽到了毛澤東逝世的消息。”
文化部學習班停止學習,改寫文章、大字報,悼念和回憶毛主席對自己的感召。
清華大學全校師生員工和家屬分單位集合在一起收聽,許多人泣不成聲,昏倒在地。被誣爲“反革命”的清華大學女教師陶德堅也痛哭了一場:“因爲我還等着他來解決我的問題,這下子無望了。”
作家浩然走到西長安街上,在電報大樓前徘徊,後來躲到文化局大院最後邊的一個角落,想讓自己鎮靜下來。晚上回家以後, 他從廣播中得知自己是治喪委員會委員,是375名委員中“唯一的一名以作家身份承擔這份光榮使命的人!爲此,我心潮波湧,一夜沒有入睡”。
故宮博物院一警衛正在打盹,突然聽到大院裏人聲鼎沸,像是出了什麼大事,“出去一打聽,才知道是毛過世了,院子裏有幾個人在捶胸頓足地哭泣,過路的人也都知道分寸,無不低頭疾行,恐怕在這個敏感時刻惹出是非”。一個不知情的同事正在御花園堆秀山上高唱楊子榮的那段《我心中自有朝 陽》,警衛隊幾個人衝上去,把他摁倒,拖下山去。他起先還以爲是鬧着玩,唱得更兇,他們就捂他的嘴,弄得他滿臉是土。
被關在北京通縣 (今通州區) 軍營的吳法憲的感受是:“雖然毛主席把我們關起來了,但是我對毛主席思想感情上當時是不可動搖的。”“我一直躺在鋪板上,一動不動, 一方面是毛主席的逝世使我感到悲傷,另一方面是考慮自己的前途。”
北京以外各界人士的反應
毛澤東逝世的消息傳出後,人們普遍的感受,先是震驚,接着是悲痛。
曾任毛澤東祕書、在西安工作的高智回憶說:噩耗使我受到巨大打擊,“我當時呆了,傻了,悲痛得泣不成聲,幾天不思飲食,直到13日,接到北京的電話通知,我懷着極其沉痛的心情,於翌日晚上8時半乘飛機到了北京”。
被下放到長治市嶂頭村的女作家丁玲聽見有人大聲喊她快打開收音機,她急忙打開,聽到了“繼承毛主席遺志”這句話。一下子她什麼都明白了,哇的一聲哭倒在牀上:“曾經希望有一天因爲我改造得較好, 能博得主席對我的原諒……主席逝世了,我永遠聽不到他對我的寬恕了!”
黑龍江省呼瑪縣,上海知青劉琪所在的生產隊開會,老鄉們也哭得死去活來,“好像天真的要塌下來了”。
哈爾濱街上的行人臉色憂悒,低頭匆匆行走。
在黑龍江中醫學院,時爲工農兵學員的陳景文的感受是:“噩耗立時把我們驚呆了,剎那又哭聲四起,悲情痛泣頓時籠罩了整個校園……”
士心所在的武漢一家小廠裏,“哭的人越來越多,幾位年紀大的人邊哭邊喊:‘怎麼樣辦喔,毛主席不在了怎麼辦喔,這要變了天怎麼辦喔,我們又要喫二遍苦,受二茬罪啊’”。在下班的路上,他看到絕大部分人都戴上了黑紗,幾個居委會老太太在街上檢查那些沒戴黑紗的人。
陝西鳳翔師範學校教師王志斌正與同事在農場勞動,“從村裏的大喇叭裏聽到毛主席逝世的消息後,大家一下子震驚了。這時候,我們一下子癱坐在土地上,也記不起勞動的事了,都放聲痛哭……”
噩耗傳到韶山,毛澤東的鄉親們難以接受。毛澤東的堂弟毛澤連說:“廣播裏響起了哀樂,我站在門檻邊上,一邊聽,一邊想,一邊念,是三哥嗎?三哥會過世嗎?三哥不是要回來嗎?我一直不停地問自己……”毛澤東過去的鄰居毛愛桂從她的大女兒那裏得悉毛主席去世了,“我瞪着眼望着她,打死不相信。就這個時候,廣播裏響起了哀樂,這個聲音讓我一下子就傻了。我十分恐懼、害怕。我不知道會發生什麼”。當晚當地舉行了哀悼會。次日人們又來到毛澤東舊居,肅立在毛澤東的遺像前默哀悼念。
遵義、延安等地,無不如此。
南京下關的王朝柱家,9月9日是大兒子結婚的日子。下午4點鐘,接新娘的隊伍正要出發,忽然聽到收音機裏傳來了哀樂。於是,喜事停辦,大門上的紅喜字、紅對聯被揭了下來。
某軍區常委們學習訃告,將軍們抱頭痛哭,“那幾天,我們一輩子加起來,也沒流過那麼多淚水”。
林曉石所在的某部隊連隊中午集合,連長未發話眼裏已湧出了淚水:“請大家摘下帽子。我們的……毛主席……逝世了!”全連都被連長的話震驚了。
被譽爲識字專家、被毛澤東關心過又歷經坎坷的祁建華感到絕望,企圖以拼命勞動而自盡,最後暈倒在菜地裏。清華大學原紅衛兵頭頭蒯大富的感受是:周恩來、毛澤東這兩個人的去世,都讓我很傷心,我的感覺是心裏的依靠一下就沒有了。我當時也估計到是在劫難逃了,不會再有人護着我,也沒有人會和我說話了。
8日晚間,遠在烏魯木齊的王蒙夫婦睡不着,唉聲嘆氣:“我們說‘批鄧’使國家陷入新的天怒人怨、衆叛親離,再一次掐滅了老百姓的希望。老人家一旦仙去,國家會發生什麼情況?我們會遭遇哪些危險?邊疆會出現什麼情況啊?中國沒有了毛澤東,天啊,天要塌下來的啊。”9日下午,王蒙被通知去聽廣播。王蒙回憶:“我已經猜到個八九不離十,我提醒自己,各級各界人士必須充分注意,萬萬不可粗心大意。”
有人使勁掐自己,懷疑自己是在做夢。一個女知青被身旁的同伴捏了一下手,她感到很痛:“我對她點點頭,知道她是在驗證這是不是真的。這一夜,這個知青點無人入睡,卻靜寂得無人一般。直到快天亮,哀婉的小提琴聲從東頭的一間房裏傳出,拉的是《我戰鬥在金色的爐臺上》……如泣如訴的琴聲撩開了醞釀已久的帷幕,按捺不住的啜泣和嗚咽,此起彼伏。”
那天出生的孩子的名字,不少叫作念澤、思東、念東……
南京大學教授王覺非暗想:“一個時代到此結束了!”他感到,大家的心情都很緊張,一時南京街上行人一下子就空了。晚7點教師集體聽廣播,大家板着臉默不作聲。
“老三屆”高爾品和幾個同學在蕪湖的大街上,看到的是“沒有一個人哭,沒有一個人喊。每一個人的臉都鐵青着……”
貴州遵義市人民在遵義會議舊址前悼念毛澤東
北京的弔唁和瞻仰活動
從9月11日至17日,包括全國和首都各界代表以及各駐華使節、來華外賓在內,總共30多萬人前往弔唁,瞻仰毛澤東遺容。
新華社記者報道,弔唁人羣“從毛主席遺體兩側緩緩走過,瞻仰最敬愛的領袖的遺容時,都抑制不住心頭的極大悲哀,失聲痛哭,許多人高喊着:‘毛主席呀毛主席,我們永遠懷念您。’”最後一天,“慟哭之聲整日不絕。人們在毛主席的遺體前,一步一呼‘毛主席呀毛主席’,淚水沾滿衣襟,久久不忍離去”。
第一天,主要是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中直機關、中央國家機關的部長、副部長,解放軍的高級將領弔唁。華國鋒等人弔唁後,即站立在毛澤東遺體旁守靈。
弔唁組的傅學正看到了許世友,“他面目嚴肅,穿一身褪了色的軍裝,足登一雙白線編織的有眼兒的便鞋,鞋的前尖上繫着一撮紫色的纓子。他東瞅瞅,西看看,好像在觀察人們的動靜。在休息室裏,他拍拍腰中的手槍對工作人員說:今天誰搗亂,我就對他不客氣”。
第二天,毛岸青帶着妻子邵華、兒子毛新宇來了。
1965年底就被打倒的羅瑞卿是第三天來的,坐着輪椅,痛哭不止,非要站起來鞠躬。傅學正和羅宇架着他站起來,他“連續向毛主席鞠躬五六次之多”。
參加守靈的浩然記述:“我跟幾位守靈者站列一排,被這千萬人同一的悲哀所震撼,也都陪着流淚。”“在哭泣的人流中, 我認出了大寨的郭鳳蓮。她被人架着,哭着不肯離開,幾乎被人擡出靈堂。我還看到了毛主席的兩個女兒李敏和李訥。她們倒能夠掌握住自己,眼淚枯竭,神情呆滯。她們默默地站到靈牀邊,深深地鞠躬過後,就默默地凝視她們的父親,片刻過後,又默默地離去了。”
14日下午參加弔唁的葉聖陶記述,他“走近毛主席遺體,悵惘之甚,未能佇立瞻仰。記於一九四九年三月間初次見到,今日爲最後一見矣”。
16日下午5時30分,中央政治局成員再一次集體弔唁,並在毛澤東遺體旁守靈,直至6時整,弔唁活動結束。
郭沫若抱病瞻仰了毛澤東遺容,又勉力參加了守靈。
伍修權在瞻仰毛澤東遺容並向其遺體告別時,他看到許多年過花甲甚至古稀的老同志,都孩子似的痛哭起來:“幾十年來,不論什麼危難情況和險惡環境,只要得到毛主席的指示甚至僅僅想到他,我們就有了戰勝一切的力量和勇氣,有他在,我們就有勝利,就有希望,就有光明。現在一下失去了他,我們真像忽然都成了‘孤兒’……”
高智在毛澤東的遺體前站了許久,他的眼淚不斷地往下流:“難以壓抑住自己的悲痛,有千言萬語要向他老人家說,主席,您安息吧!我永遠會記着您。”
1968年曾被打倒的傅崇碧回憶:“我們只被允許列隊看看,給毛主席守靈都不讓我們去。許世友司令對‘四人幫’非常惱火, 責問他們爲什麼不讓我們跟隨毛主席的老同志去給主席守靈。”
青年女工於向真邊走邊流淚,走出大會堂後號啕大哭,同事們紛紛勸解。其實,她是想起了三個月前,在新華社工作的父母出差越南前的囑託:“據可靠消息,毛主席健康已經非常脆弱,萬一他老人家離去,國內局勢有可能失控。……爸爸媽媽把他們設想好的兩套特別方案祕授給我,以便萬一發生嚴重動亂或打起內戰,我好按此計劃先救助家中老輩人,再帶着妹妹逃難避禍。”
規模空前的追悼大會
“偉大的領袖和導師毛澤東主席追悼大會”主會場設在天安門廣場。
披着黑紗的毛澤東巨幅遺像,懸掛在城樓中央。城樓前面,築起了紅色高臺,上面陳放着黨和國家領導人以及江青敬獻的花圈。東西兩側陳放着黨政軍各部門和29個省、市、自治區敬獻的花圈。
天安門廣場莊嚴肅穆。
首都百萬羣衆很早就來到天安門廣場和東、西長安街,一直延伸到東單、西單。他們臂戴黑紗,胸佩白花,列隊肅立。
9月18日下午2時30分,治喪委員會全體成員以及工農兵代表陸續登上高臺。
臺上的江青全身黑裝,黑紗包頭,只露面部。她獻的花圈署名是“您的學生和親密戰友小青” (在弔唁大廳,江青送的花圈上寫着“沉痛悼念崇敬的偉大導師毛澤東主席”;“您的學生、戰友江青暨毛岸青、李敏、李訥、毛遠志、毛遠新”)。
負責實況轉播的楊正泉在即將播音前, 緊張得“喘不過氣來,腿在瑟瑟抖動”。他回憶說:“廣場上靜極了,北京靜極了,只是聽到啜泣,聽到自己的心臟的怦怦跳動聲。”“2點50分,我打手勢告訴方明‘開始’!他打開了話筒的開關,停了一會兒, 像是有意鎮靜了一下,長長地吸了一口氣, ‘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北京電視臺’這聲音立即傳遍北京,傳遍全中國,傳遍全世界!”
新華社報道說:“下午三時整,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同志宣佈追悼大會開始。全場肅立,百萬人默哀三分鐘,由500人組成的軍樂團奏起悲壯的哀樂。大會實況通過廣播和電視傳送到千家萬戶。悲壯的哀樂聲傳到祖國城鄉,傳到高山大川,傳到遼闊的邊疆,傳到全國每一個角落。偉大祖國在靜默,八億人民含着眼淚,肅立志哀……”
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華國鋒致悼詞。
華國鋒說:毛主席的逝世,對我黨我軍和我國各族人民,對國際無產階級和各國革命人民,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都是不可估量的損失。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一定要積極響應黨中央的號召,化悲痛爲力量,繼承毛主席的遺志,要搞馬克思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在黨中央的領導下, 將毛主席開創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進行到底。
軍樂團成員王愛國回憶:“大約講到三分之二處時,也許是過度悲傷,也許是過度勞累,華國鋒身體向前一歪差一點失去了平衡,勉強堅持將悼詞唸完。”
羅瑞卿、傅崇碧、王震、張愛萍、韓先楚等人蔘加了大會。羅瑞卿下了輪椅,拄着雙柺,堅持肅立。
在上海居住的賀子珍派侄女賀海峯、外甥女賀小平,代表她到北京奔喪。
在秦城監獄被關押多年的中央黨校原校長林楓,此時在病房裏,請妻子郭明秋攙扶,面向天安門的方向靜默、三鞠躬。
哲學家馮友蘭在追悼大會上,作了一首輓詩:“紀念碑前衆如林,無聲哀於動地音。城樓華表依然在,不見當年帶路人。”
大會半小時就結束了。
梁漱溟沒有出席追悼大會,早些時候單位就通知他在家,別出去。當天他是在街道革委會看電視實況的。
一些地方和單位的追悼會
各省、市、自治區的政府所在地至各城鎮、公社作爲“分會場”,先收聽北京的現場實況廣播,之後舉行追悼會。
駐烏魯木齊部隊的文存回憶:王洪文的“向毛主席三鞠躬”拖的時間太長,結果我們鞠躬兩次後,他“一鞠躬”纔開始。我們算是鞠躬五次。新疆軍區司令員楊勇致悼詞,“大家心裏難過得像刀割一樣,許多人痛哭起來,淚水止不住地流出。我的心是沉甸甸的”。
知青康成傑參加了黑龍江建設兵團第二十三連的追悼會,“這時的心情是何等的難以描述啊!百感千情,千言萬語,都匯成奪眶而出的淚水,都鑄成一句話:‘偉大的領袖和導師毛主席永垂不朽!’”
東北建三江七星農場的羣衆淚如雨下, 有的躺在地下打滾哭……有30多名羣衆哭得昏了過去,絕大多數是女性。
山東營口市追悼大會開始時,昏暗的天空突然狂風大作,一片厚厚的烏雲隨風撲來。默哀時,狂風夾雨傾瀉下來,真可謂“狂飆爲我從天落”了。默哀後一兩分鐘, 那片烏雲又被疾風席捲而去。
陝西寶雞市追悼大會,有的人邊哭邊唱:“毛主席啊,你老人家怎麼說走就走了啊!”“你是我們的大救星,你走了國家怎麼辦啊……”會場哭聲唱聲此起彼伏。
貴州大方縣的追悼會,高致賢回憶,默哀中“有人哭出聲來以後,接着就是許多人放聲大哭,哀聲動天!誰也不敢勸止,更無法制止……”
福州的追悼大會,暈倒的人很多。知青施曉宇記述:“默哀三分鐘時,倒下的人連扶都沒人扶,不敢扶。”
當時的廈門一中一學生後來回憶說: “我們全校師生到廈門市工人文化宮廣場參加全國的追悼大會。我們隨着喇叭向毛主席的遺像三鞠躬,很多人都哭了。‘國悲啊! 國悲啊!’鄰居一個六十來歲的老太太用福州話連聲道。”有的公社,當廣播裏宣佈追悼大會開始並播放哀樂時,遠遠近近的汽車全都鳴笛誌哀,會場上更是哭聲一片。許多貧下中農在地上打着滾:“毛主席啊,你這一走誰還管我們呀,可讓我們怎麼活呀……”
對毛澤東的悼念,可以說創造了衆多的世界之最,譬如佩戴黑紗的人數之多,佩戴時間之長 (有的長達一個月),靈堂之多 (僅湖南益陽一縣,設靈堂284處,中心靈堂獻花圈271個),追悼大會規模之大 (“分會場”遍佈全國),還有當天下午的全國工廠停工、學校停課、商店關門。
對中國的未來充滿盼望與疑惑
毛澤東逝世後,人們考慮最多的,是今後中國向何處去,自己又該怎麼辦。
翻譯家沙博理的感受是:“誰能想象一個新中國沒有毛主席?沒有了他,我們該怎麼辦呢?特別是現在,中國處境如此艱難。”知青徐友漁認爲:“中國要大變,也許,我們這一代的命運前途也會隨之改變。”知青朱箐箐在日記中寫道:“中國向何處去?!”“我們的祖國會不會變色呢?!”有些青年議論,政治局面會緩和一些,不會大搞政治運動了,因爲沒人具備毛澤東那樣的威望。有的人擔心自己還能不能調回城市。韶山羣衆擔心會不會打仗。在“批鄧”時期,茅盾就擔心毛主席逝世後,國家將大亂。
時任四川省委宣傳部副部長的馬識途與知心同事,企圖從報紙上的每一條新聞、每一篇文章的縫隙裏,每一張照片的背後,看出一點消息來,“我們看到毛主席治喪委員會的名單排序和追悼大會站位,主持人和致悼詞人名單,感到忐忑不安。除了華國鋒, 那一幫子人佔優勢,如果華國鋒被他們架空,失去了最高權力,他們就可以以多數興風作浪,矯詔奪權”。
軍事學院院務部政委董鐵城對朋友說: “‘四人幫’要上了臺,我們就準備上山打游擊。”
知青張鐵生與劉繼業9日深夜向遼寧團省委領導彙報思想,表達了對國家領導人, 對國家命運和前途的擔心,“特別要警惕中央出修正主義”。
一些人還準備聆聽毛主席遺囑的發表。
耿飈認爲沒有遺囑:“如果要有什麼遺言的話,在毛主席去世後,中央《告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書》以及華國鋒同志所致悼 詞中一定會提及的,可是在這些文件中隻字未提這件事。”原毛澤東警衛隊隊長陳長江也說:毛“沒有留下任何遺書,也沒有向任何人交代過遺言”。
毛澤東逝世不久,以華國鋒爲首的中共中央和“四人幫”的鬥爭就暗地展開了。
在北京追悼大會上,臺上的治喪委員會成員當時都想了些什麼,無人得知。
浩然回憶說:“我和其他成員站在華國鋒身後,聽着他宣讀悼詞,看看主席臺下海洋一般的人羣,再看看主席臺上各方面的代表人物;雖然是萬里晴空,卻隱約感到烏雲翻動,變幻莫測,最後在心裏暗暗地想:國喪辦完,我必須離開北京,回到農村去……”
形勢變化急驟。
1976年10月6日,華國鋒、葉劍英等人採取了斷然措施,一舉粉碎了“四人幫”,結束了長達10年的內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