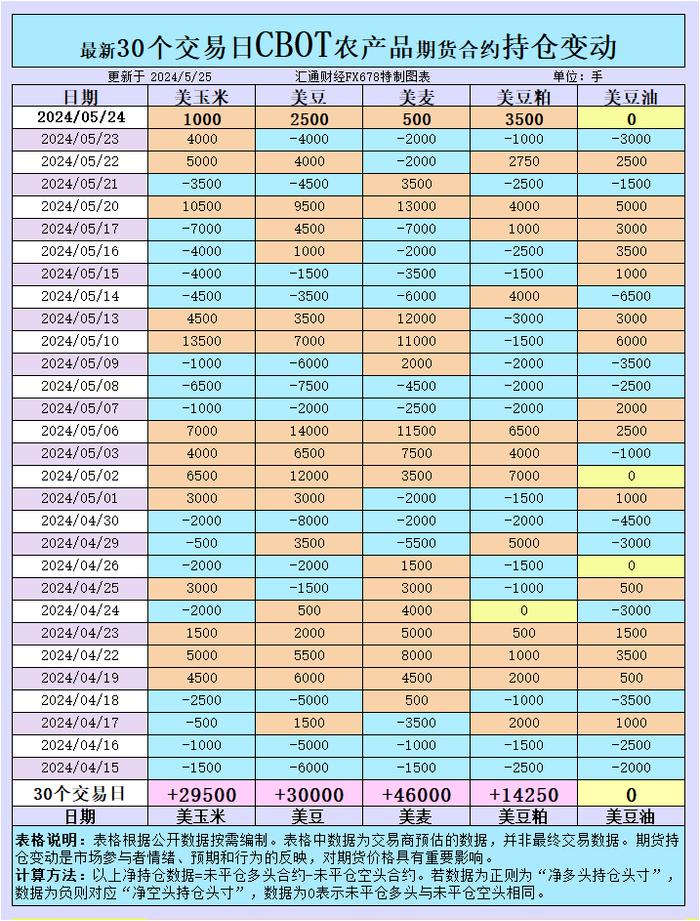「萧乡文学」衣者先生|渴望刀疤的疼
在我的脚面上有一道半圆形的刀疤,它已经伴随我成长了29个春秋。
我出生在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家庭,打小父母就教育我:农民家的孩子没有吃闲饭的,不下地干活,早晚饿死……也正是在这样一个家庭,我不到10岁,就被早早地赶到地里干活,弄了把小锄头,人家一根垄我一边沟,累得死去活来,偶而铲着铲着睡在地里了……我那时哀叹,为什么我们家天天都是早上顶着星星下地,晚上看着月亮回家,打我记事起,似乎年年如此,有忙不完的农活,还有父亲那唧唧歪歪的责骂声。
89年,那年我12岁。秋天,父亲早早地为我准备了一把细把镰刀,并对我说,他12岁已经是劳力了,能挣为家挣工分了,我也应该向他一样,做一个男子汉。现在想来,对于一个体弱的孩子,他们怎么能忍心让他同他们一样去割玉米呢,并且把他们的成长经历强加在我的身上,他对我的期望如同他一样,早早地成为家庭的劳动力,成为一个所谓的“男子汉”。在不断地训斥中,我艰难地割着玉米,手疼,腿疼,腰疼,总之各种疼痛交织在一起……想撂挑子,偷偷跑掉,一想到跑掉后的挨打远比这疼痛严重得多,我曾不只一次地想过是不是他们亲生的,是不是象他们说的那样从粪堆里捡回来的。
劳动依旧,骂声依旧,心里的抱怨依旧……
母亲是一个很会过日子的人,春天的玉米缺了苗,他会补种上大红豆,丝丝络络的豆角秧会爬玉米杆上,割起来相当费力,难度可想而知,对大人亦是如此,何况是孩子……脚一滑,身子一偏,刀偏走了方向,没有落到玉米上,而是划到了脚面上。脚面上一片肉伴随着钻心的疼掀开了,淌出鲜红的血来,再后是麻苏苏的……坐在了地上,告诉自己是男子汉,是董存瑞、黄继光一样的坚强人物……骂声又来了,什么偷懒了……母亲见我迟迟没起来,猜想可能出了问题,奔了过来一见很多血,赶紧用衬衫将脚包起来,哥把我抱到装满玉米的牛车上,我手里依旧握着那把吃饭的家拾儿……
坐在牛车上,看着渐行渐远的玉米地和听不到唧唧歪歪的骂声,突然觉得这很好,庆幸这也是解脱的一种方法。
牛车很慢,脚很痛,但相比那繁重的农活和父亲的责骂,我更倾重于负伤。到了家,我老姨在做饭,看到伤这样,立即抓了把花椒面洒了上面,并且信心满满地说,具有消炎止血的疗效,再吃点糖水罐头,几天就好。说着转身扯了块红布,细致地包在伤口上,腿上系了根红绳,说截住起线,至今我也不晓得什么意思。我就在炕上养伤,无人问津了。
我的脚一天比一天肿,起初能穿二姐的鞋,再后来父亲的鞋都穿不了,疼得都睡不着觉了,并且发烧了。母亲背我去了村里的赤脚医生那里,那时,我真的很崇拜这个大夫,因他什么都能治,也什么病都敢治。打开红布,脚又肿又红,伤口已经化脓。清洗后,发现伤到了筋,立即手术把化脓的肉割掉,我当时大哭说啥不让他割,无耐上了药,换了纱布,继续养着……
人随贱随贵,天生地养。一段时间后,伤口自然愈合了,我到现在都不知道那筋恢复成啥样。以后的十年,每逢阴雨天,脚面很痒,而且很红。再后来的十年,疤痕淡了,阴雨天不痒了……
而后,每年地里农忙依然有我劳作的身影,后来上了学,工作了,娶了妻,成了家,也一直都在农忙时节去劳作。只是随着父母的年岁大了,渐渐地听不到那唧唧歪歪的责骂声。尽管父母年过七旬,但是我们还是拗不过他们每年秋天园子里必须堆满玉米的意念。
人至中年,每每看到脚面的疤痕,似乎父亲忙碌的身影历历在目,训斥声依旧,那心底不服的反抗与怨恨已荡然无存了,反而更渴望那情景再现,哪怕只有一次,可是父亲已骂不动了,腰也变成月牙形了,有的只有二老立在门前盼我们归来的身影,和一遍又一遍啥时回家的询问。
有人可能说父母真狠,然而正是这狠却给我一个好的品格,勤劳的品格,是我一生都用不完的财富。而父母那看似不尽人情的做法,不正是让我在逆境苦苦坚持的韧性吗?
好了伤疤不忘疼,不能忘的是自己成长的经历,是仍然想听父亲唧唧歪歪骂声的渴望,还有那纯朴时代的往事……
查看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