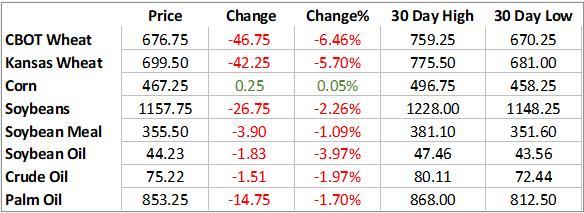「蕭鄉文學」衣者先生|渴望刀疤的疼
在我的腳面上有一道半圓形的刀疤,它已經伴隨我成長了29個春秋。
我出生在一個地地道道的農民家庭,打小父母就教育我:農民家的孩子沒有喫閒飯的,不下地幹活,早晚餓死……也正是在這樣一個家庭,我不到10歲,就被早早地趕到地裏幹活,弄了把小鋤頭,人家一根壟我一邊溝,累得死去活來,偶而鏟着鏟着睡在地裏了……我那時哀嘆,爲什麼我們家天天都是早上頂着星星下地,晚上看着月亮回家,打我記事起,似乎年年如此,有忙不完的農活,還有父親那唧唧歪歪的責罵聲。
89年,那年我12歲。秋天,父親早早地爲我準備了一把細把鐮刀,並對我說,他12歲已經是勞力了,能掙爲家掙工分了,我也應該向他一樣,做一個男子漢。現在想來,對於一個體弱的孩子,他們怎麼能忍心讓他同他們一樣去割玉米呢,並且把他們的成長經歷強加在我的身上,他對我的期望如同他一樣,早早地成爲家庭的勞動力,成爲一個所謂的“男子漢”。在不斷地訓斥中,我艱難地割着玉米,手疼,腿疼,腰疼,總之各種疼痛交織在一起……想撂挑子,偷偷跑掉,一想到跑掉後的捱打遠比這疼痛嚴重得多,我曾不只一次地想過是不是他們親生的,是不是象他們說的那樣從糞堆裏撿回來的。
勞動依舊,罵聲依舊,心裏的抱怨依舊……
母親是一個很會過日子的人,春天的玉米缺了苗,他會補種上大紅豆,絲絲絡絡的豆角秧會爬玉米杆上,割起來相當費力,難度可想而知,對大人亦是如此,何況是孩子……腳一滑,身子一偏,刀偏走了方向,沒有落到玉米上,而是劃到了腳面上。腳面上一片肉伴隨着鑽心的疼掀開了,淌出鮮紅的血來,再後是麻蘇蘇的……坐在了地上,告訴自己是男子漢,是董存瑞、黃繼光一樣的堅強人物……罵聲又來了,什麼偷懶了……母親見我遲遲沒起來,猜想可能出了問題,奔了過來一見很多血,趕緊用襯衫將腳包起來,哥把我抱到裝滿玉米的牛車上,我手裏依舊握着那把喫飯的家拾兒……
坐在牛車上,看着漸行漸遠的玉米地和聽不到唧唧歪歪的罵聲,突然覺得這很好,慶幸這也是解脫的一種方法。
牛車很慢,腳很痛,但相比那繁重的農活和父親的責罵,我更傾重於負傷。到了家,我老姨在做飯,看到傷這樣,立即抓了把花椒麪灑了上面,並且信心滿滿地說,具有消炎止血的療效,再喫點糖水罐頭,幾天就好。說着轉身扯了塊紅布,細緻地包在傷口上,腿上繫了根紅繩,說截住起線,至今我也不曉得什麼意思。我就在炕上養傷,無人問津了。
我的腳一天比一天腫,起初能穿二姐的鞋,再後來父親的鞋都穿不了,疼得都睡不着覺了,並且發燒了。母親揹我去了村裏的赤腳醫生那裏,那時,我真的很崇拜這個大夫,因他什麼都能治,也什麼病都敢治。打開紅布,腳又腫又紅,傷口已經化膿。清洗後,發現傷到了筋,立即手術把化膿的肉割掉,我當時大哭說啥不讓他割,無耐上了藥,換了紗布,繼續養着……
人隨賤隨貴,天生地養。一段時間後,傷口自然癒合了,我到現在都不知道那筋恢復成啥樣。以後的十年,每逢陰雨天,腳面很癢,而且很紅。再後來的十年,疤痕淡了,陰雨天不癢了……
而後,每年地裏農忙依然有我勞作的身影,後來上了學,工作了,娶了妻,成了家,也一直都在農忙時節去勞作。只是隨着父母的年歲大了,漸漸地聽不到那唧唧歪歪的責罵聲。儘管父母年過七旬,但是我們還是拗不過他們每年秋天園子裏必須堆滿玉米的意念。
人至中年,每每看到腳面的疤痕,似乎父親忙碌的身影歷歷在目,訓斥聲依舊,那心底不服的反抗與怨恨已蕩然無存了,反而更渴望那情景再現,哪怕只有一次,可是父親已罵不動了,腰也變成月牙形了,有的只有二老立在門前盼我們歸來的身影,和一遍又一遍啥時回家的詢問。
有人可能說父母真狠,然而正是這狠卻給我一個好的品格,勤勞的品格,是我一生都用不完的財富。而父母那看似不盡人情的做法,不正是讓我在逆境苦苦堅持的韌性嗎?
好了傷疤不忘疼,不能忘的是自己成長的經歷,是仍然想聽父親唧唧歪歪罵聲的渴望,還有那純樸時代的往事……
查看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