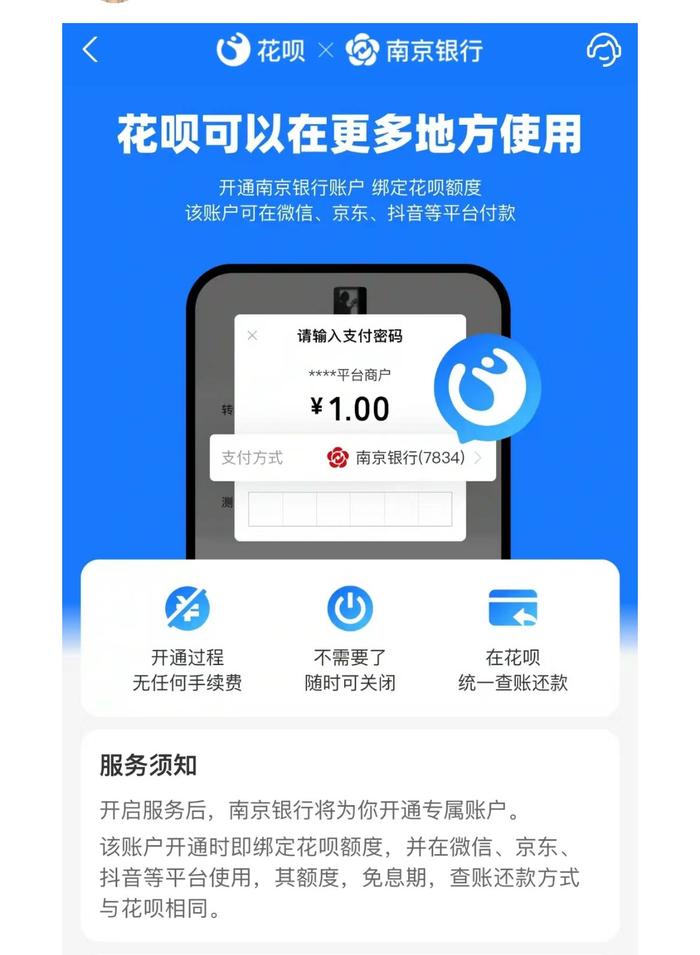中興的33年輪迴
本文來自微信公衆號:伐柴商心事(Fachai_story),作者:伐柴,虎嗅獲授權發表。
1980年8月26日,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五次會議通過了由國務院提出的《廣東省經濟特區條例》,批准在深圳設置經濟特區。深圳,這個昔日和千萬普通沿海小縣城一樣平淡無奇的地方,從此插上翅膀,成爲了新中國經濟的增長極。
此時,遠在在千里之外的西安691廠技術科長侯爲貴,被派往美國負責半導體相關技術和設備引進。這個在國企裏呆了12年的中年男人,在美國看到了真正公司的模樣,接觸到了“市場”的概念。
1984年2月,鄧公第一次視察深圳時題詞道:“深圳的發展和經驗證明,我們建立經濟特區的政策是正確的。”深圳人長長地鬆了一口氣,蛇口工業園門口“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的標語牌再也不用被不停地拆下換上了。這“衝破思想禁錮的第一聲春雷”震醒了被計劃經濟支配多年的國人。深圳,成爲人們發家致富的夢想之地。
鄧公南巡的第二年,見過大世面的侯爲貴被691廠派到深圳,希望尋找商機。於是,中興半導體有限公司成立了。這一年,侯爲貴43歲。
一
雖然叫半導體,但是創立之初的中興跟半導體沒有半毛錢關係。創立初期的中興,和大多數中國公司一樣,經營着來料加工、來樣加工、來件裝配和補償貿易的 “三來一補”業務。侯爲貴帶領創業初期的38個人,在深圳沙河草叢中的廠房里加工電子錶、電子琴和電話機。雖然利潤低,但是憑藉着喫苦耐勞的精神,中興一年就賺了35萬元,成爲公司的第一桶金。
在做電話機生意的過程中,侯爲貴敏銳的認識到通信行業未來必將有更大的發展。那時候,國內通信行業的交換機有“七國八制”之說,整個市場被7個國家廠商8種制式的機型完全佔領。公司成立的第二年,侯爲貴力排衆議,用做貿易掙來的錢成立研發小組,專攻交換機領域。
4年後,中興研發出自己第一臺數字程控交換機ZX-500,打破了國外產品一統天下的局面,中興也正式轉型爲通信設備製造商。1992年,憑藉ZX-500,中興合同銷售額突破1億元,利潤2000多萬元。
1990年,中興成功研發第一臺程控交換機ZX-500
中興半導體成立時,由691廠、香港運興電子貿易公司及其隸屬航天部的長城工業公司深圳分公司共同出資280萬元,成爲深圳特區最早的一批技術類合資公司之一。但公司和人一樣,往往可以共苦,卻不能同甘。有了錢的中興反而由於分紅等問題使得股東間矛盾激化,嚴重影響了公司的效率。
1992年,那是一個春天,鄧公第二次南巡。航天部領導漫不經心的一句話“實在不行你們可以自己出來幹”,讓焦頭爛額的侯爲貴茅塞頓開。趁港方股東因自身經營不善倒閉並退資的時機,他推動中興半導體的創業元老們投資成立民營企業中興維先通,希望打破體制壁壘。
1993年,侯爲貴率領維先通與691廠、深圳廣宇工業公司進行了第一次重組,成立深圳市中興新通訊設備有限公司,維先通持股49%,691廠持股34%,深圳廣宇持股17%。這是深圳第一批股權清晰的“混合所有制”企業之一。
鑑於之前的教訓,新的中興董事會確定由中興維先通承擔經營責任,保證國有資產增值,若出現經營不善,則需用股本進行補償;兩家國有企業不參與運營。中興在國內首創了“國有控股,授權經營”,即國企民營的全新模式。侯爲貴被任命爲總經理,正式進軍通信設備行業。
縱觀整個八、九十年代的企業史,魯冠球、李經緯們無不是被產權所困,都在爲理清產權而疲命奔走。而93年的中興,就解決了桎梏那一代企業家的枷鎖,爲未來發展奠定了基礎。
二
中興的國企民營企業模式,在當時賦予了經營團隊極高的自由度,並充分調動了他們的積極性,使得中興的業績火速攀升。1997年,中興新通訊改制成立“中興通訊股份有限公司”,並在深交所上市,市值4.4億元。4年時間,升值了140多倍。而中國通信市場的紅利期,纔剛剛到來。
1999年2月,中國電信移動業務被正式剝離。面對固話利潤下降、部分高端客戶被移動運營商分流的局面,中國電信急需獲得一種既可避開政策限制、又可變通地進入移動市場的業務。彼時,大鬍子吳鷹的UT斯達康剛剛整合日本的PHS技術,在國內推出小靈通。中國電信馬上跟進,與UT斯達康開展相關的推廣工作。看到這一形勢,1999年7月,中興正式開始大規模啓動小靈通項目。儘管期間監管部門對於小靈通的政策幾經反覆,但是中興基於對未來前景的樂觀預計,一一應對,最終狠賺了一波。
2000年,中興的合同銷售額超過了100億元。2001年全球電信業務面臨前所未有的低谷,而中興憑藉小靈通產品獲得了近24億元收入,爲度過行業低谷起到了巨大作用。
奠定中興無線通信領域強者地位基礎的是CDMA,中興也是第一個打破外國企業對中國CDMA系統設備壟斷的中國企業。2001年,中興通訊參與到國內CDMA骨幹網建設,獲得聯通110萬線CDMA合同,打破外企的壟斷。雖然當時中興在這一期建設中所佔份額只有7.5%,短短三年後,中興已經成爲聯通在CDMA領域的第四大合作伙伴,市場份額接近20%。
2004年,中興營業收入達到212億元,並在香港H股上市。侯爲貴轉任董事長,獲得當年的“CCTV中國經濟年度人物”。
三
侯爲貴創立中興的三年後,44歲的轉業軍人幹部任正非由於在南油集團下屬電子公司經營中被騙200萬元,最終被迫“下海”。更爲不幸的是,生活的壓力也讓他的家庭解體。帶着身上僅有的21000元,離異中年大叔任正非在南油新村的一個居民樓裏創立了深圳華爲技術有限公司。
一個偶然的機會,任正非幫做程控交換機的朋友賣設備。和侯爲貴一樣,他看到了裏面巨大的商機,也決定自己研發交換機。通過早期購買、組裝、貼牌生產出來的用戶交換機,華爲積累了資金和經驗技術。
1991年,任正非說服本來要去清華讀博士的華工老師鄭寶用,在蠔業村工業大廈三層用一年時間開發出了HJD-04 500門交換機。在那裏,他們喫喝拉撒睡全在公司,也因此形成了流傳至今的“牀墊文化”。
1992年,華爲開發的交換機開始批量進入市場,當年產值就高達1.2億元,利潤超過1000萬。
這時候,中興和華爲站在了同一起跑線上。早期中興的公司文化深受侯爲貴的個人影響,就像教書先生侯爲貴喜歡的牛一樣,勤勉、溫和、中規中矩。而華爲則有着任正非強調的狼性文化,在當時“軍閥混戰”的通信市場,並沒有人認可這個名不見經傳的民營公司。任正非爲了快速佔領市場,說服17個省市級電信局合資成立了莫貝克公司,任正非承諾每年給予33%的高額回報。這種捆綁利益的打法,使得華爲銷售額激增。
1996年,華爲銷售額達到26億元,而中興只有6.8億元。到了2000年,華爲的銷售額增加到220億元,超過中興一倍多。
但是,憑藉前期小靈通和CDMA的佈局,中興在2003年營業收入激增,達到160億元。而那時,華爲正在絞盡腦汁圍剿舊將天才李一男的港灣科技,營業收入增長放緩,爲221億元。這是二者進入新世紀 最爲接近的一年,從此,華爲一騎絕塵,把中興遠遠甩在了身後。
2017財年,華爲整體收入高達6036億元,淨利潤達到475億元。而中興通訊的營業收入爲1088.2億元,歸屬上市公司股東的淨利潤爲45.7億元,連華爲的零頭都不到,徹底淪落爲華爲眼中的26。
四
幸福的人都是相似的,不幸的人各有各的不幸,甚至,更加不幸。4月15日,美國商務部工業與安全局在毫無預兆的情況下,激活了針對中興的出口限制令。禁令限制及禁止中興通訊申請、使用任何許可證或許可例外,或從事任何涉及受美國出口管制條例約束的物品、軟件或技術的交易。這意味着,中興將無法使用美國進口的芯片、軟件和EDA工具。由於從基礎芯片、板卡、手機、交換機和基站全系列產品都對美國芯片和軟件嚴重依賴。如果禁令生效,整個公司將徹底陷入癱瘓。
美國商務部制裁的理由主要是不誠信和整改措施不到位。雖然目前看來這是大國政治角力的藉口,但不可否認,中興這些年來的乏力也是有原因的。
侯爲貴從南昌大學畢業當老師,再到軍工廠工作,一直都是學者型處事方式。人們對他的評價都是“儒雅、親和、簡樸”,然而具體到戰略制定上,就略顯得保守。在技術路線制定上,除了CDMA中長期戰略成功以外,大多都在跟隨和保證公司有利可圖的前提下佈局產品。小靈通雖然讓中興賺了大錢,卻鋪了過多的人、財、物力在這個過時的技術上。而2004年擔任總裁的繼任者殷一民,更是技術出身,在他的治下,中興被華爲遠遠甩在身後。
雖然中興是國企民營的經營模式,但從他創立伊始,就離不開國企的管理文化。中興的管理層級分爲5級,最下面的兩級分別叫科長和部長,有着明顯的行政感。在管理中流程管理大於結果管理,所有的人僅對眼前的流程正確性負責,並不對事件響應的後果負責。於是,管的人多,越管越亂的情況時有發生。諷刺的是,這次美國商務部展示的違規文件,就是各級領導層層審批的結果。
中興在經過股改、上市後的20多年發展中,股權結構變得越來越複雜。侯爲貴和其他高層通過維先通持有中興通訊約15%的股份。而其60多家子公司和10多家聯合經營的企業,股東名單上多多少少都有中興通訊高管和骨幹的身影。子公司的好壞纔是一些人關心的重點。而對於基層員工來講,更羨慕的是華爲的全員持股,將個人利益與公司發展綁定。當然,華爲這幾年也沒有多少內部股可發了。
客觀的說,這是每一個國企甚至大型企業都有的通病。而中興的病症,只是發的不是時候。
尾聲
中興的尷尬和窘境,只是整個科技行業的一個縮影。2016年,我國集成電路進口額高達2271億美元,連續4年成爲最大進口商品。FPGA、高性能AD/DA、高速光電子芯片、CPU、存儲器等核心芯片的國產化率最高不超過15%,有些甚至爲0。任何一家高科技企業遇到中興的遭遇,都會被判死刑。
中國飛速發展的四十年,造就了深圳速度。而在這種狂飆突進的速度中,絕大多數人都變得急功近利。就連國家的高科技項目,對標國外頂尖指標,有10年甚至更長時間的技術差距,往往也要求在2到3年內結題驗收。伐柴的一位朋友,是業內知名的清華教授,有一次實在忍不住自揭傷疤:“連續3年,畢業的學生沒有一個搞集成電路的,不掙錢”。
1981年,691廠正是在錢學森的要求下主攻半導體元器件研發,派遣侯爲貴出國考察。而後來成立的中興半導體,如今也栽在了半導體上。
33年,是一個輪迴,很多人在這個紛繁的世界裏,忘了初心。
本文來自微信公衆號:伐柴商心事(Fachai_story),作者:伐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