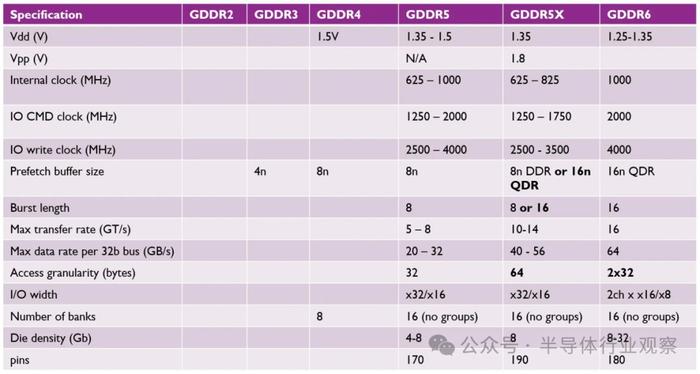西安東大街的美術家畫廊
摘要:我們的親密交情源於他父親陳笳詠先生,陳老是陝西美術界元老級人物,中國美協西安分會的創始人之一,著名美術理論家、書畫家,在“長安畫派”的崛起和發展中貢獻卓著。當然,陝西美術館舉辦的有影響的畫展,遠不止我說的這些,還有蘇聯油畫展,波蘭、瑞典的現代繪畫展,韓國郭元柱山水畫展、臺灣六人畫展,以及於右任書法展、華君武漫畫展、黃秋園山水畫展、關山月畫展,長安畫派的創始人石魯、趙望雲、方濟衆、康師堯等名家的畫展。
西安東大街587號的陝西美術家畫廊,也叫陝西美術館,當年是西安唯一專業美術展館。位置在東大街鬧市中心案板街口,與唐城百貨大廈同一座樓,佔據大廈東邊約有十米多寬。
1949年前,美術家畫廊原址上曾有一家名叫金城的電影院,後來成了中蘇友好協會西安分會的地址。20世紀60年代中蘇關係破裂,中蘇友協也解散了,這塊地方被當年兼任中蘇友協祕書長的石魯先生帶到美協作展覽廳使用。1964年,中國美協西安分會在這裏舉辦全國美展草圖觀摩會,石魯創作的中國畫《東渡》草圖,蔡亮的《貧農的兒子》草圖等,都在這次會上展出、討論。全國美協當時主持工作的領導蔡若虹、華君武、力羣等赴會。當時面對《東渡》,美術理論家蔡若虹先生在肯定這幅大作的同時,還就一些具體細節與石魯先生展開爭論。當時這種學術氣氛很正,真正體現的是“百家爭鳴”。
據陝西省美協幾位老先生回憶,這一批作品後來在西安新城廣場新城區文化館舉辦的“全國美展西北五省(區)分展”上展出,在全國美術界引起轟動。尤其是石魯的《東渡》氣勢磅礴,金石畫法,十分震撼。可惜“文革”時期,石魯慘遭批鬥,這幅鉅作也丟失了,連個照片都沒留下。
“文革”期間,四大協會(即作協、音協、劇協、美協)解散,這塊美協用於展覽的地方也被西安市商業局收走,改建成了“躍進旅社”。
1979年,四大協會恢復,省美協即中國美協陝西分會也召開了會員代表大會,石魯任主席,李梓盛任書記、常務副主席,全面恢復工作。當時美協向省上打報告,申請撥款修建畫廊。而西安市商業局也準備蓋唐城百貨大廈,於是經協商,拆掉當時案板街口市商業局下屬的“紅霞商店”和相鄰的產權歸美協的“躍進旅社”,由市設計院設計,省三建司施工,因畫廊所佔地盤,東大街方向小,後邊地方面積大,所以統一蓋一個樓。
但因缺乏資金,工程進展不下去,這塊地方一直是一個基建挖出的大坑,一下擱置了四五年。
大廈1984年才建成。美術家畫廊居大廈東邊,由石魯先生題寫“中國美術家協會陝西分會-美術家畫廊”,用鋁合金鑄字掛在樓上,很是耀眼。
美術家畫廊,建築面積5100平方米(地上六層,地下一層)。大展廳5個,面積350平方米,小展廳4個,150平方米。展線共計約500米,一次可容納觀衆5000餘人。另設會議廳1個,可供發佈新聞和研討會等使用,主要承擔全省美展及學術交流活動等。
大樓蓋起後,迎來的第一個大型展覽即是1984年慶祝新中國成立35週年舉辦的“第六屆全國美展”,西安作爲宣傳畫、水彩、水粉畫分展覽區。修軍先生具體負責主持。當時陳紹華、郭線廬的宣傳畫《綠·來自您的手》《信息是開發人類智力的契機》分別獲得金獎。這兩件作品爲陝西爭得了不小的榮譽。陝西在國畫展區、雕塑展區、連環畫展區都有銀牌、銅牌入賬,比如劉文西的國畫《山姑娘》獲銀獎;邢永川的雕塑《楊虎城將軍》獲銅獎。陝西省美協還獲得了組織獎。
陝西美術家畫廊,對全省乃至西北地區美術活動影響很大,被列爲全國十大美術館之一,排於京、滬、寧之後。十多年來,陝西美術館先後舉辦了各類書畫展覽600餘次,學術交流活動200多次,觀衆達80餘萬人次,高峯時日觀衆量達萬餘人次。
美術家畫廊是我非常熟悉的地方,參加過不少畫展的開幕式,欣賞了不少當年陝西優秀的美術作品,在美術上給我最美的享受。八九十年代連續幾位廊長(館長)都是我的朋友,其中有趙振川和耿建,再有接他們班的陳玄,如今都是著名畫家。
1987年4月25日,在隆重紀念“長安畫派”創始人趙望雲先生逝世十週年時,在畫廊舉辦了“趙望雲師生畫展”。趙望雲先生作品佔一個大廳,另一個大廳是他的學生蜚聲中國畫壇的著名畫家黃胄、方濟衆、徐庶之、韋江凡、趙振川的作品。黃胄先生,與著名美術史論家、學者黃苗子先生親臨現場,並且參加了同時舉辦的紀念會議,黃胄、黃苗子、方濟衆、徐庶之等都作了發言,紀念大廳擠滿了人。後來媒體都作了報道,陝西電視臺對黃胄先生作了專題採訪,影響非常之大。通過這個活動,讓更多的人對“長安畫派”的創始人、奠基人之一趙望雲先生有了更進一步瞭解與認識。
這次畫展我有幸受趙振川先生委託,參與宣傳與新聞報道事宜,邀請了陝西省電視臺新聞中心主任張書省和西安市文聯副主席、《西安晚報》總編助理商子雍。並佈置讓青年作家杜愛民(後任西安市文聯副主席)撰寫了趙望雲先生紀念文章,讓商子雍在《西安晚報》發表。還在由我任特邀編審的《西北航空》雜誌發表趙望雲先生的歷史照片和繪畫作品。趙振川兄很滿意,也很高興。豪氣大方的他,主動贈送給我和張書省各一幅畫,給商子雍二幅,全是四尺三開,讓我非常感動。
記得振川兄贈我的《趙振川畫冊》扉頁上寫有“嘔心瀝血,耗盡生命而終身無悔”之語。讀來我震撼,這是他以生命獻身藝術的宣言。振川兄遂成爲我學習之榜樣,成爲藝術道路上探索不止、追求不息、知難而進的動力。後來我寫了《太白有鳥道——記趙振川山水畫創作之路》的評論文章,還爲振川兄十多幅山水畫配詩。
耿建先生1985年秋調到陝西省美協,很快就成爲美術家畫廊負責人,我把他叫廊長。他還擔任美協藝術委員會副祕書長。我和耿建1970年就認識,當時我在銅川市歌舞團,他在銅川市中心文化館,我們同處一個大院子。“銅歌”在市工人文化宮排練演出,他的辦公室在文化宮舞臺後邊,經常成了我們團領導的指揮部。而我們彩排時經常幹到後半夜,臺下就剩一個觀衆,就是他,因之被我們稱爲“銅歌”的五好觀衆。後我調進中心文化館,我們又成了同事。可以說是四十多年都廝混在一起的,狗皮襪子沒反正,無話不說的哥們朋友。他給我畫的畫不計其數,少說也有百十幅。記得1970年時我在銅川住的窯洞,燒的煤煙爐子,煙筒有縫隙把牆燻黑了一大塊,我讓耿建兄畫一張畫用糨糊牢牢貼上牆遮住,過一年畫被煙熏火燎,也撕爛了,全不把耿老兄大作當回事。這事我早就忘了,而耿建兄始終耿耿於懷,每當我問他要畫時,他都會拿這事來調侃,羞辱我一番。
唉!我也真是拿金子、銀子當廢銅爛鐵,耿建的畫後來值大錢了,而且藝術水準之高,深獲行家好評。他的畫以形入神,大氣磅礴,快意揮灑,筆力遒勁,滿紙風煙,場面宏闊。我給他寫過畫評,爲他人物畫《黃土高原是我家》等一批作品配過詩,還記得幾句:“縱橫在你滿布滄桑的臉龐上轅莽蒼荒蕪籠罩着神光靈氣轅那深如褐色的黃河水轅從高原鴻溝大壑的深邃裏轅掙脫束縛轅流瀉出一派萬古洪荒的恣肆”。
陳玄當館長時已是新世紀之初,他曾在陝西省藝術研究所任《藝術界》副主編,後調陝西省美協任《美術通訊》主編,兼業務辦主任。我們的親密交情源於他父親陳笳詠先生,陳老是陝西美術界元老級人物,中國美協西安分會的創始人之一,著名美術理論家、書畫家,在“長安畫派”的崛起和發展中貢獻卓著。曾任陝西省美術家協會常務理事、陝西省美協創作研究室主任、國家一級美術師。1994年在美術家畫廊舉辦“陳笳詠先生繪畫作品展”,我應陳老邀請出席開幕式,並與陳老和梁耘三人合影留念。我20世紀70年代就認識陳老,因了梁耘介紹,“文革”期間1974年左右陳笳詠先生被下放到銅川陳爐陶瓷廠,而當時梁耘也被貶到陳爐的山溝裏,因爲當年我經常上陳爐陶瓷廠找梁耘,也與陳老認識了。在我印象裏陳老先生是位慈祥寬厚、謙虛謹慎、對人熱情的大好人。雖正在受難的他,以苦爲樂,對自己終生追求的繪畫藝術事業絕不放棄。
接着,1996年陳玄在畫廊辦展,我自然也來捧場。到2018年11月10日陳玄在西安高新二路力邦藝術館辦畫展,我接陝西省藝術研究院院長丁科民電話,亦排除干擾,不顧才做了眼睛視網膜脫落手術,興致勃勃前去觀看。陳玄幼承家傳,自小紮下童子功,不但畫畫得好,古體詩也寫得出類拔萃。我尤喜他畫的蘭草,併爲他的《蘭幽香風遠》配詩:“幾枝最幽然的柔美,映亮一片小天地的聖潔。走近你,讓香風沐浴我的虔誠,潔白的力量,能盪滌一切的污濁。以素雅佔盡風流,誰讀懂了你最愜意的恬淡。抵住繾綣之思,遙遠了我一季的輕愁。”
而梁耘先生還在銅川工作時的1991年,就在陝西美術家畫廊舉辦首次個人畫展。我幫他布展,跑前跑後,聽他調遣,開幕式時還邀請西安畫壇我熟悉的一批畫家前來捧場,畫展引起轟動效應。梁耘是我1970年銅川歌舞團團友,也是40多年的摯友,當年他任銅川市美協主席,中國美術家協會會員。後調入西安太華路上的陝西科技大學當教授,創辦了陝西省山水畫研究會,並任首屆主席,開闢了一方天地。
當然,陝西美術館舉辦的有影響的畫展,遠不止我說的這些,還有蘇聯油畫展,波蘭、瑞典的現代繪畫展,韓國郭元柱山水畫展、臺灣六人畫展,以及於右任書法展、華君武漫畫展、黃秋園山水畫展、關山月畫展,長安畫派的創始人石魯、趙望雲、方濟衆、康師堯等名家的畫展。
西安東大街上的陝西美術館,在我心中挺神聖,也挺神祕的。例如當年畫廊有一裱畫的陳師,名陳天生,河南人。老先生藝術鑑賞力之高,令我驚歎!20世紀80年代末,我一陝西歌舞劇院導演老師,手中有兩幅何海霞先生的四尺山水畫,要找一高手裱畫,我帶他來找陳師。記得陳師評價這兩幅畫說,一幅能代表何先生的水平,屬於上品,一幅弱一些。後果然應驗,這兩幅何大師作品上了廣州一拍賣會,一幅陳師評價爲上品的畫,拍出百萬好價錢,一幅竟然流拍,僅賣了十多萬。還有一次我到耿建畫室,滿牆都掛耿建新創作的畫,正遇幾位我認識的朋友來買畫,我推薦其中一幅畫評價畫得如何好,但朋友們皆不認可,我氣憤地說這幅我要了。這批畫耿建讓陳師裱,誰知一上牆,陳師就對耿建說:這幅不敢賣!於是,耿兄馬上跑到市文聯找我,這幅畫他借回去了。後來耿兄在北京美術館和澳大利亞辦展覽,這幅畫都在展品中,成了耿建老兄的代表作。你說陳師神不神。
而如今處在東大街拆遷改造中的陝西美術館,已蕭條得早已今不如昔了。我專門去了一趟想看一下究竟,竟發現蜷縮在破敗的唐城百貨大廈東邊的門口,還掛有一個“陝西美術館”的木牌子,證明着它苟延殘喘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