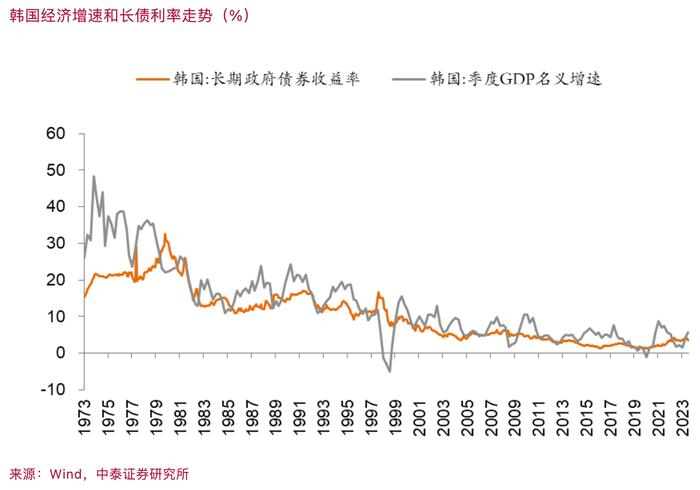WTF?全球最富有26人資產=全球最窮一半人口(38億)資產(上)
物競天擇,適者生存。
國際慈善機構樂施會(Oxfam)週一發佈的最新報告顯示,全球最富有26人擁有與世界上最貧窮的一半人口(38億人)相等的財富,而2017年數據爲最富有的43人。
這份名爲“公共財富或私人財富”的報告是瑞士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上公佈的。同時,該報告指出:如果對世界上最富有的1%的人的財富徵收的稅率提高0.5%,籌集到的資金將足夠用於教育2.62億兒童,並提供可挽救330萬人生命的醫療保健。
那麼,這些年發生了什麼?(以歐洲老大哥德國爲例)
上層階級——富人只滿足於富有貝爾託·布萊希特曾經說過:“在暗處者,不示人。”
時至今日,卻成了:“在高處者,不示人。”
不爲人知的富裕階層一般來說上市公司尤其需要一張面孔或者說是一個代言人,代表其在媒體 、在全體股東大會上或者是在投資者面前發言。因此,“高級經理人” 們由於職業的原因就成了看得見摸得着 的富人。由此,人們便產生了一個錯誤的認識 :高級經理人等同於財富階層。而事實上,以德國爲例,德國的高淨值個人中只有5%的人是高級經理人,其中還包括了處於領導位置的上市企業所有者。可見,“高級經理人” 們只是財富俱樂部中的邊緣羣體 。儘管如此 ,他們的報酬在十年間確實比企業中其他僱員增長得更快。
對富人徵稅!!!前面我們提到:如果對世界上最富有的1%的人的財富徵收的稅率提高0.5%,籌集到的資金將足夠用於教育2.62億兒童,並提供可挽救330萬人生命的醫療保健。
可是回顧歷史,一些發達國家的政府又做了什麼呢?
路德、維希·艾哈德(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前經濟和勞動部長、前總理)在二戰結束後曾對財富階層採取了截然不同的稅收政策——爲了支付戰時或戰後受財產損害者的賠償費用,他向 財富階層提出了 “負擔均衡” 的要求。
這一政策的實質是讓富人交 出一部分財富 ,並且數額巨大。1948年 ,政府對財富階層所擁有的財產進行了評估。富人們需要向政府繳納其一半的財富,分30年交清,每年繳納其中的1.67%。“負擔均衡” 政策的收益佔了當時德國國內生產總值的1%。
如今若德國政府採取這種措施,想必會被認爲是“無知”的社會主義者~
納稅?不存在的根據瑞士證券經紀公司Helvea分析師的計算 :單單在瑞士的銀行中就有約2000億歐元未 經納稅的財富來自德國國內。而在盧森堡、列支敦士登 、開曼羣島等其他避稅天堂裏的德國財富還沒有計算在內。德國稅務工會估計,每年德國大約有300億歐元的資金被非法轉往國外。
而經合組織對此項數據的估計值還要更高。該組織的稅法專家傑弗瑞·歐文斯說 :“我們是在談論上千億歐元 ,通過對稅法的嚴格執行每年德國政府可以增加20%的稅 收。”這對德國來說意昧着1000億歐元的額外收入,但前提是對現有稅法更加有力的貫徹 ,因爲在納稅上耍花招已經成爲財富生活的一部分。
財富階層之所以將逃避納稅視爲真理所當然的生財之道 ,原因是一個避稅行業的存在。
稅務顧問的人數只在2000年至2010年這 10 年間就增加了30% 。這些收費不菲的稅務專家的人數說明了避稅行業和金融投資行業一樣 ,都爲財富階層創造了豐厚回報。
(下半部分我們會詳細闡述富人如何避稅)
下層階級——窮人缺的不是錢我們從一個故事說起:
來自德國魯爾工業區的彼得和安雅·維爾克這對夫妻爲了他們的“疾病”可以說是絞盡了腦汁,他們的目的卻不是爲了重獲健康,而是一心想讓政府蓋章認可他們身患疾病。因爲只有這樣,政府就業中心纔不會再拿工作和職業培訓來麻煩他們。
彼得最初嘗試了用抑鬱症來矇混過關,“我發覺自己越來越敏感 ,” 他笑着說 , “總是馬上就激動起來 ,特別是覺得自己被不公正對待的時候。”
記者在2010年開始與這對夫妻接觸的時候,他們和兩個孩子佳在一間差不多 100平方米的舒適公寓裏。彼得當時已經失業13年 ,而他的 妻子安雅也是有7年沒工作過 。政府每月給他們的所有補貼加起來大約是2000歐元。
“說實話 ,我再怎麼也賺不了這麼多錢,更別說安雅了,我說他們就應該別來煩我們。”
當一個人缺乏現實的謀生手段時 ,也同時失去了要早起 、學習、制定目標和追求效率的理由。
工作這件事就這樣漸漸從下層階 級的視野中消失了。由此產生的是一種新的生活形態 ,工作及與之 相關的一切在其中幾乎不佔奇任何地位 ,也無法傳承給下一代。
下層階級用來維持這種生活形態的金錢理所當然地從政府源源不斷而來,就像是插座中的電流。
從政府部門想方設法地多領點救濟金對於這些人來說遠比工作來得划算。
下層階級的典型標誌之間並不存在太大的區別,其根源均可以追溯到教育層面。但是匱乏的教育只是下層階級的標誌,他們同時被大量的社會問題所困擾。
教育的責任在於國家,而教養則是家長的權利。正是本着這一原則,德國憲法法庭在 1998年做出裁決:幼兒園不再屬於教育範疇。雖然德國人發明了幼兒園 ,真他國家不但引入了這一發明,甚至連德語名字都照搬了過去。但在宮的發源地德國,這個人生中最重要的教育機構卻被排除在教育的範疇之外。
另外大多數人以及政客都覺得 :那些生活在社會底層的人和他們一樣屬於有能力、有抱負的人羣 ,區別只是這些人的手裏沒什麼錢。
這個假設不但讓人放心,還提供了簡單的解決方法。對於缺錢的人 ,只要往他手裏塞錢就行了。
再多的政府救濟金也不能讓其走出現有的困境。因爲金錢不會替他們打掃房閱,不能督促孩子刷牙 ,早晨也不能叫他們起牀 ;金錢不能給孩子唸書 , 也不能對孩子唱歌或說話 ,更不能告訴孩子業餘時 間除了看電視還能幹點兒別的事情。
由此看來,單純將這一階級的本質簡化爲 “貧困” 必然會對導致救助政策的失敗。
點擊關注,更多深度解讀即將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