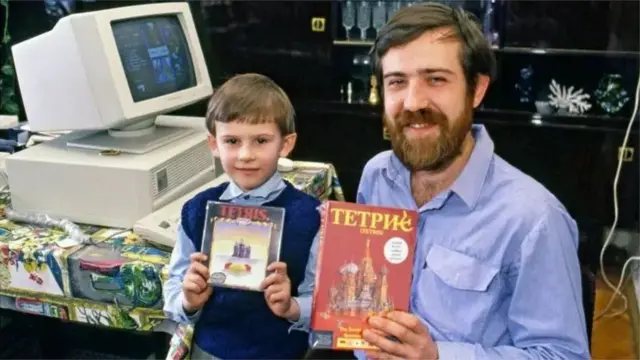《湄公酒店》|鬼魂·囈語·重構歷史
阿彼察邦·韋拉斯哈古,這位泰國新浪潮時期的先鋒,以對敘事時空的可能性探索與東方神祕主義而聞名。
他的影片拋棄了類型片的敘事規則,淡化故事,主題多以夢境、自然/超自然、歷史重構等組成。

除了長片以外,他拍攝的短片、視頻裝置等同樣引人注目,《湄公酒店》便是如此。
在泰國東北部臨近老撾邊境的湄公酒店,生活着幾位居客,他們從陽臺和圍廊欄杆中俯瞰着湄公河的河景,談論着各色民間傳說故事和過往生活經歷。
他們似乎真實存在,又似乎是鬼魂;可能是扮演鬼魂的演員,也可能是同一個人在不同時代中的輪迴往復。時空不再是線性的流動,它存在與此端,也存在於彼端,隱性時空在顯性時空的言語中得到闡釋,也會時而發生斷裂。

阿彼察邦的這部《湄公酒店》便是這樣一部三言兩語即可說清楚的“散文詩電影”。不僅結構簡潔、情節淡化,連同其中的神祕主義和政治訴求、歷史追憶,都被相當程度地簡化了,以一種單調重複卻令人分辨不清虛幻與現實界限的混淆時空的狀態,將鬼魂的囈語緩緩道出。
在一個狹小的房間裏,芳與她的母親通靈。“我的遊魂被判困在水下,水下又黑又冷。”母親的亡靈坐在芳的身邊,平靜地說出這番話。母親死了,但舉止和常人一樣,年輕的記憶被傾斜而出。與此同時,一場特大洪水的突發新聞通過電視廣播滲進她們的閒聊裏。冥冥中一切都存在着關聯。

在這個場景裏,日常的幻覺被重新構建。這好像是個夢境,又彷彿午憩初醒。在母親的囈語裏,故事開始走向未知。湄公酒店裏的鬼魂與常人在同樣的演員裏切換,處於相似的空間(陽臺/房間),擁有着不同的記憶。
湄公河是串聯起這一切的根源,浸透着無數過往的祕密。但它淹沒的這些伴隨着陣痛的回憶,在觀衆看來,卻無法身入其中,也不能感受到其中的痛苦,反是一份淡然。阿彼察邦並沒有在這部作品中訴求批判,而是對其進行了重構,跨越了紀錄與劇情、歷史與真實的界限。

20世紀60年代的“老撾危機”,在影片中被漫不經心地提起。那場危機將這個有着600年曆史的國家推向了瀕臨崩潰的邊緣。在一系列政變與反政變中,國家的政權幾度更迭,難民衆多流離失所。
借影片中的母親之口,阿彼察邦將老撾人從附近的邊境來到泰國,停留在人山人海的警察局,修建難民營的歷史情境用言語營造出來。當時的泰國,是個老撾人被餵飽,自己人卻沒東西喫的“國中之國”,政治洗腦無處不在。

當然,如阿彼察邦其他作品一樣,“政治性”從未成爲他所要強調的話語。對這件龐大且混合了血淚的歷史事件的呈現,絲毫不存在歷史性宏大敘述的痕跡,一切都出自私人的記憶、幽默的口吻,與分不清是人是鬼的角色形象融爲一體。
其他角色亦是如此,在前一場戲中,男主人公馬薩託還在啃食着狗的內臟,是一個飢餓的遊魂,接着他召喚出芳的遊魂,訴說“我不知道要投胎多少次,才能投胎到人類”式的蜜語;而在後一場戲中,他又變成了同性戀者,與同伴談笑着自己與第三任男友的情感。二者的身份切換不着痕跡。

阿彼察邦繼續實驗着自己的個人風格——通過挖掘固定演員在具有神祕主義的場景中演繹日常,並循於自己的節奏與風格,在不經意中改變身份,從而創造出現實的神祕性。

出現在《湄公酒店》中的演員,也同時出現在《祝福》、《戀愛症候羣》、《能召回前世的布米叔叔》、《幻夢墓園》裏,彷彿構成了“邦哥宇宙”。不同維度裏每個角色間細微的差異與身份的調轉,都是阿彼察邦對自己作品序列的印記,他對這些從河底浮現出的遊魂進行形象再現,並賦予其靈異的表象與現實的生動。
在吉他小調的不斷重彈中,阿彼察邦編織出了失常生活中靈韻的詩意。他在最終用舉重若輕的姿勢——船隻劃過水面的弧線,令影像陷入長時間的冥想狀態,引導觀衆在影片結束之後開始直面屬於自我的故事。
2018.5.20(日)
15:45-17:45
法國文化中心放映
《湄公酒店》
湄公河畔的一家酒店內,圍繞着一對母女之間情感的羈絆展開,一部真假難辨、虛實相間的電影在正在反覆排練。《湄公酒店》中的鏡頭,在洪水中不斷建構和解構,交織着漂泊不定的未來幻夢。
本片可說是阿彼察邦憑藉《能召回前世的布米叔叔》摘得金棕櫚獎之後,給觀衆們的獻上的一份姊妹篇禮物。相較前者,本片中對泰國民俗、靈性文化和當代社會政治的呈現更加深入淺出,但依舊秉承了阿彼察邦電影引人入勝的神祕色彩。
阿彼察邦 · 韋拉斯哈古
Apichatpong Weerasetha
阿彼察邦· 韋拉斯哈古是泰國獨立藝術電影的旗手級人物,同時他也以影像藝術家的身份活躍於全世界的美術館和藝術機構。除了自己創作,阿彼察邦還成立了公司Kick the Machine,致力於推動實驗電影和獨立電影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