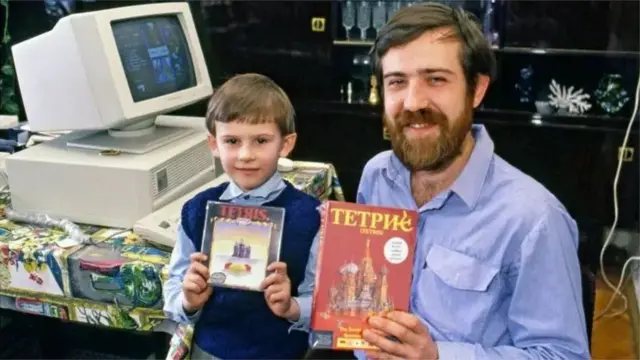看見小時候——農村的童年
小時候的家,就是並排的三間土牆瓦屋,門像朝南。堂屋正中央擺放一桌一椅,右牆掛着“向毛主席學習”的鏡框,據說是父母親結婚時,舅舅送的,只有簡單潦草幾個大紅字。右邊是父母與四姐的房間,左邊是五個哥哥姐姐的房間,牆邊連着竈屋。
哥哥姐姐的房間只有兩張牀,兩排並放,一排是大哥跟二哥,另一排則是大姐、二姐、三姐。都是簡單的木架牀,中間架幾塊木板,冬天墊一層幹稻草,再鋪墊被、牀單、蓋被。夏天撤去稻草,鋪上編織而成的竹片,四角打結,再將草蓆鋪上,張設蚊帳。牀靠牆那邊,大姐經常在上面拿炭枝畫滿半邊牆。姐姐們的牀頭,靠門放一張紅漆漆的桌子,那是大姐上初中買來的桌子,這張桌子跟隨了大姐整個初中,旁邊還用白色的漆塗上“城月二中 唐彩琴”,大姐初中畢業之後,這張桌子就歸大姐所有,父親駕着牛車去二中拉回鄉下。因爲使用日久,再加上調皮,二姐喜歡在用鉛筆刀在上面摳出一個洞,還模仿魯迅的《三味書屋》裏的情節,刻了兩個字“學習”。
屋裏的地板是純黃土,由於時常踩踏,亮得發光。每天早上母親都要指使姐姐屋裏屋外都要打掃一遍,地面凹凸不平,難免會有坑窪的地方,用掃把小心把裏面的垃圾挑出來。父母的房間老是堆積很多農作物,這種地方老鼠自然喜歡竄來竄去的。過年前大掃除,把農作物搬出去,發現一窩小老鼠,很小,粉嫩粉嫩的,可愛,眼睛都睜不開,大姐還打趣說這是一羣小豬。父親一看見小老鼠就把它們全部弄死,小孩子自然不懂大人爲什麼那麼殘忍。家裏用的掃把,每年都會換新,到收成的季節,父親都帶着三個姐姐去山上砍一大堆不知名的植物,擺在院子裏曬乾葉子,父親就會在門口將它們一把一把紮起來,成了新掃把。在秋天收割好的稻穀在穀場曬的時候,我們都喜歡用新掃把,因爲新的很軟,很厚,收稻穀的時候可以掃得很乾淨。
在鄉下的我們,並不是特殊的。遠近的村子上的家裏一般都有五六個兄弟姐妹,在農村,我家並不是特殊的,兄妹成羣這種情況在農村並不是說很少見。
計劃生育在二姐出生後就開始推行,超生的孩子是沒有戶口的,稱作“黑戶“。
農村的大人們一看到這些小孩子,往往都要說上一句:“你沒有爸媽,你是從路撿來的。“
我被這麼說,往往會生氣攥起拳頭準備打架的戰勢,往往落敗的是我,人多勢衆,無非表示我好像沒有資格存在在這片土地上。
農村的田和園都是公家的,按照每戶人口,土地的肥沃分土地的,我和六姐是黑戶,便是沒有田的。隨着政策的改變,黑戶也漸漸變少了,或許是老馬主動交全了計劃生育的罰款並且做了結紮手術,我和六姐也在戶口本上有了名字,也是個有“身份“的人了。
到了六姐做黑戶的時候,計劃生育是非常嚴格,母親經常帶着我東躲西藏的。連在家的小孩子衣服都要收起來,萬一被別人看見還有小孩就麻煩了。我長大之後經常聽到這樣的一個故事,母親怎麼樣抱着她逃過計劃生育的人,並頌揚母親是偉大的母親。
那天母親住在老馬的夥計家躲計劃生育,門鎖緊,突然門有撞擊的聲音,計劃生育部的人在外面大聲喊道:”趕緊開門,例行檢查。”母親一聽,意識到不對,抱着我,從這棟樓房頂跳到另外一棟樓,或許是農村出生腿邁得快,計劃生育的人開着車在後面追,但是母親跑的是田野的路,機動車不好使,轉眼間母親又趟過寬寬的水溝,躲進別處去了。
懷我的時候,母親孕吐很厲害,這使得父親抱着樂觀的驚異,認爲這次一定是個兒子。酷暑的夏天,凌晨2點,煤油燈發出一絲光亮,父親穿着大褲衩,人字拖,急匆匆往姑奶奶家跑。早上7點,父親抱着剛出生的我,唉聲嘆氣,臉都黑了,沒看到小雞雞,連大姐都感到失望,家裏七姊妹不就是爲了多生個男孩,開枝散葉。
父親淬了淬嘴:”又是個賠錢貨,哼。”,坐在門口拿着煙筒一個人悶悶的抽着。 煙波一縷縷飄出來了,纏繞着,沒有一絲平坦,像是在表達的是以後這一家子細水流長的苦日子有多難過。母親只是坐在牀頭默默的別過頭沒有說話。
出生恰逢農耕時節,父親把我交給大姐之後,就一聲不吭扛起犁頭,牽着老黃牛在田裏,一深一淺移動。
後來父親在縣城裏的好友聽說父親又生了個女兒,想討過去當養女,因爲伯伯生了五個兒子,一直想要個女兒。縣城伯伯家的女兒,的確是比鄉下種田人不知好多少倍,但是母親卻沒有答應。
歡迎關注:十點書齋,更多精美美文、故事敬請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