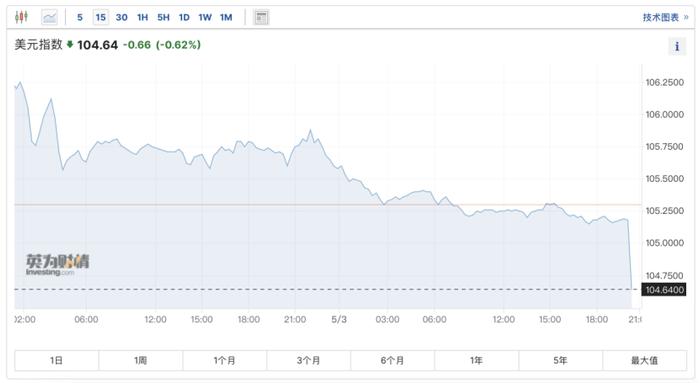王旭東:應當釐清公衆史學與公共史學的區別
公衆史學public history
公衆史學爲您推送精品閱讀
作爲兩個看似一字之差的概念,“公衆史學”完全等同於“公共史學”嗎?倘若並非完全等同的話,那它們的區別何在?當然,我認爲這兩者之間實際上是有區別的,不能簡單地混爲一談。爲此,應當釐清公衆史學與公共史學的區別。
1
首先想談的一個問題是,公共史學的本質所在是什麼。國內對應地譯作“公共史學”(當然也有依據public原本就有的多層含義,譯成公衆史學)的英文“PublicHistory”,是近些年由美國傳入我國的。大體來看,這個興起於20世紀70年代的公共史學,實際上發端於美國的歷史教學領域。如此便需要我們注意兩個重要的關鍵點:其一是,起步時的背景所反映的倡導、推動和實施公共史學的主體。公共史學的首倡和推動者並非來自民間,而是來自高等教育系統中的歷史學教授或教師。毫無疑問,這些人應屬於專業的歷史學家或史學工作者,不能歸類爲業餘的歷史愛好者。其二,公共史學創立的初衷和目標規定的首要任務。從一些文獻中討論或表述的內容我們不難看出,美國一些從事歷史教學的工作者最初發起公共史學的首要任務和目的,是爲了解決大學歷史專業的畢業生所面臨的社會出路難的問題。既然如此,我們便不能過於簡單地把公共史學的起點看成或臆測成,那些“高、大、上”的史學家們主動地從象牙塔走向民間,目的就是爲了培養社會大衆成爲歷史的書寫者而最終能夠書寫大衆自身的歷史。正因爲有上述這兩個關鍵點在起着作用,所以美國公共史學纔會帶有更加看重社會應用/實用性這樣的特點。這樣的特點具體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着眼於社會用人單位如圖書館、檔案館、城市規劃部門等的具體需求來培養歷史系畢業生。
爲此,公共史學通常尤爲注重探討如何將傳統的歷史學同當代的影視技術和信息化應用技術(諸如數字化、網絡信息化和信息可視化技術等)更好地結合起來的問題。二是刻意地、培養目標明確地(具有明顯的就業針對性)對歷史學專業的學生,進行與社會需求相接軌的知識技能方面的培訓,通過傳統知識和新技能之間的交匯融合,來系統強化歷史學服務於社會的功用性。對此,我們只要查閱相關的網上資源如美國一些設立/開設公共史學專業或課程的大學網站便不難看到,美國的公共史學的確比歷史學的其他領域更加強調,歷史系的學生應當如何去掌握先進的影視手段,通過與之結合來實現歷史內容的最佳效果的呈現;應當如何利用數字化和信息化技術,以基於互聯網或局域網的數字虛擬圖書館和數字虛擬博物館等形式,去展示/傳播歷史知識;應當如何讓歷史學知識更好地服務於社會公共機構當中的歷史檔案管理等。現在看來,正是這樣的起點,賦予了美國長期持續的公共史學看重社會應用功能和實用性的傳統。而這一點,我們是能夠從美國公共歷史全國委員會(NCPH)網站發佈的“我們的任務”中清晰看到的。例如其明確宣稱:“拓展專業技能和工具”;“激發公衆參與”,使之“通過歷史實踐來培養批判性反思能力”,等等。
鑑於以上所述,我們可否能夠以這樣的一種從特殊到一般地抽象理解,來解釋興起於美國的公共史學。即,所謂的“公共史學”,是專家引領、教育導入、公衆參與互動,側重於多樣且個性化表達的一種在公共領域進行歷史建構的歷史學實踐活動。將這種歷史學實踐活動納入到大學的歷史學教學體系之中,便形成了歷史學的應用學科。當然在今天看來,公共史學興起的理論意義和社會價值,可能還不僅僅在於其所主張或強調的公衆對歷史學領域的參與,而更在於專業歷史學服務對象意識的增強所帶來的歷史學“公共轉向”(publicturn)。其實也正因如此,“PublicHistory”才更應譯作“公共史學”,而非譯成“公衆史學”。上述的思考實際上還使我們得以進一步概括出如下的結論:通過對美國的公共史學產生及其存在的學術生態和狀況的考察,我們完全有理由認爲,公共史學的確是自上而下、由內而外地產生和發展起來的。這裏所說的自上而下,是指大學裏的歷史學專業權威,受畢業生就業形勢所迫不得不放下了架子、降低了身份;而所謂的由內而外,則是指歷史教學的課程編排和內容設計,不得不爲了開拓或滿足於社會的應用性普通需求,而從專業史學象牙塔裏走出來,去更加直接地貼近服務於社會的公共事業。這便是我首先要談的問題,即公共史學它的本質所在。
2
現在國內學術圈裏時而會出現這樣一種現象,談論或使用某一概念時,爲了讓人們“更明白”些,往往會在中文用詞之後附加上英文詞彙。對於那些海外舶來/引入的概念來說,如此之舉無可厚非,甚至有時稱得上是必要的。但具體到一些中文裏原本就有、且含義界定早已明確了的概念來說,就出現了一個問題,即,難道中文詞彙唯有附上了英文詞彙纔算具有“正確/準確”的概念內涵嗎?就某些人而言,“公衆史學”這一概念用詞的認知和使用,似乎就落入了這一“用英文來解釋/理解中文”的怪圈之中。“公衆”一詞無須加註任何英文詞彙,國內的人們都會有一個共識,將其理解爲“社會上大多數的人”。至於“史學”這一概念用詞的含義所指,在國內便更不會產生歧義了。既然如此,這兩個詞彙組合成的“公衆史學”概念,理應有着自己的一個不難定位的概念釋義,而毋須假借英文來附署。並且,倘若非要認定“公衆史學”這一概念用詞的提出必須是而且也只能是用作英文概念“PublicHistory”的對應譯詞,那麼還要費盡周折地轉義論證幹嘛,直接使用“公共史學”一詞不是更好些嗎?爲此,今天的一些學者選擇“公衆史學”而不是“公共史學”來稱謂自己竭力倡導和努力建構的學科理路,一定是在潛意識裏就明白區分出兩者——中國的公衆史學與美國的公共史學,是不能等同的。或者,至少是想建立一個不同於美國的、屬於中國自己的公衆史學。所以,在這裏筆者想談的第二個問題是,公衆史學的本質所在是什麼。
雖然在中國,“公衆”這個概念只是20世紀裏才形成的概念;且“公衆史學”更是21世紀最近若干年裏才提出/使用的概念用詞,但從客觀的角度看,我認爲就概念指代的事物源流而言,公衆史學實際上發端於民間的歷史傳統,例如民間說史、民間寫史和民間傳史,均表明民間有這樣一個歷史傳統存在的。而且不論西方還是東方,這樣的歷史傳統其實都存在。世界各國都有,尤其以咱們中國最爲突出。
爲什麼要這樣說呢?因爲:
第一,西方的歷史學起源於民間。從留存至今的一些史著來看,像古希臘的希羅多德和修昔底德,恐怕都不能說他們是在以官方身份寫史;古羅馬帝國時代的權力者撰史,具有着某種意義上的“官方”修史性質了,但這些人的身份是統治者而非“史官”;西方中世紀時期的教會史,可以視作帶引號的官方修史的產物,因爲同教廷有用意/目標明確的安排纂史有關係。有意思的是,這些近似“官方”的色彩卻沒能直接導致西方的歷史學的專業化。我們現今常常提起的西方歷史學專業化進程,真正開啓卻是很晚近時候的事情,即到了19世紀,才以歷史學的學科化趨向表現出來。不過,儘管學科化是專業化的表現,但也不能直接了當地將其視作官方化。因爲相當一段時間裏,西方歷史學中的學科專業化趨向並非是官方所爲,如19世紀的蘭克史學,應當屬於大學裏任教的專業歷史學家的自發產物。如此來看,西方修史的民間傳統還是很濃的。
第二,我們再來看一看東方。總體上講,東方的歷史學與西方一樣,也是起源於民間的。但是,具體到中國卻有所不同。
在中國的民間,應當說歷史學很早就有一種專業化的分離趨向,而恰恰是這種專業化分離趨向,培育/發展成官方修史的傳統。例如,史學史中講到的“孔子作《春秋》”,便可歸類爲專業學者治史的行列。至於中國歷史上的職業史官修史,不僅屬於專業性質的修/治史,更是在以官方的身份從事專業修/治史了。倘若統觀中國的史學史,我們還可發現官方治史的特點存在着一條基本的演進路徑。一句話來表述,便是由早期的“撰”史,到後來的“修”史,再到更加後來的“纂”史。撰、修、纂這三個字,構成了中國的官方治史所經歷的三個階段。具體來說,“撰”寫歷史的最傑出的典型代表是西漢的司馬遷。司馬遷治《史記》,其中有相當一部分內容來自民間。一些資料的採集,可以說是通過某種社會調查的方式獲得的。《史記》不論體例還是內容的表述,都具有開創性,是司馬遷憑藉自身獨具的文采和史觀,以其個人的觀察現實、思考歷史的視角和評判觀點寫出來的。所以,我們對其治史採用“撰”這個字來概括。那麼,“修”寫歷史最典型代表是誰呢?我個人認爲是宋代的司馬光,因爲他以其《資治通鑑》爲自己奠定了這個的位置。在司馬光所處的時期,已經有了不少的前人歷史學成果問世,而他又據此重新按照編年的方式修寫了一部通史。至於“纂”歷史的代表,就是如我們常說的二十四史或二十五史中把“前四史”(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拿掉之後,剩下來的那些歷朝歷代的正史。它們都可謂是“纂”出來的。因爲前朝先做好了實錄,後朝的史官只不過再把實錄彙集在一起整理纂編而已。這便是我們在上面說的中國歷史學官方治史特點的一條基本演進路徑。有了官方治史,不被吸納其中的社會上其他任何人所治之史,便“理所當然地”被劃歸爲“野史”了。這些“野史”的成書過程乃至最終流傳下來的歷史文本,倘是以今天的眼光看,不正可算作當時的“公衆史學”及其“成果”嗎?
面對歷史現實的我們確實可以,也應當這麼看。因爲僅就中國的文化傳統而言,民間社會對於歷史的發掘、處理和承襲,也完全稱得上淵遠流長。爲此,若將民間的歷史書寫和歷史知識的社會應用實踐,看作當今的公衆史學的前身或“早期的公衆史學”,那麼在中國,公衆史學實際上始終都在以下面這樣的兩條線形式而存在着。第一條線可謂,自下而上、由外到內,即從民間專業歷史家的史述/史著,到後來的官方歷史學家的史學;第二條線則爲,民間歷史說書/史者(民間說書藝人口耳相傳和戲劇藝人的演繹)和民間歷史家(中國的典型代表如蔡東藩),他們以講述歷史故事的這種紮根於社會的行爲,始終如一地書寫/“說”(敘述)“傳”(傳播)着歷史知識(包括歷史闡釋)的學問。其中,民間的不論專業歷史家,還是歷史說書者(包括史詩吟誦人)及歷史戲劇創作者,所起的作用恰恰是連接甚至是溝通正史與“野史”的橋樑或管道。成書於朝廷的正史所記載的歷史內容,通過這些人散佈到了民間;而成形於民間的“野史”所講述的歷史內容,也是通過這些人在社會上廣爲傳播,以至於被官方的職業歷史家所知曉。所以,從這兩條線來看公衆史學,其實更多的是一個專業或職業歷史學家的“治史”,同民間“書寫”歷史,相互之間的交匯/交互或互動的問題。
將東西方的有關歷史情況予以綜合比較,我們獲得的總體印象實際上會變得更加地清晰起來。宏觀上講,西方社會本應能夠有一個很好的民間治史傳統,因爲非官方的專業歷史學家是後來的歷史學學科化的主要力量,且不具備官方治史的傳統,故而也就應當形成不了對民間治史的壓制。但實際情況似乎並非如此。由於西方的歷史上官方治史傳統的缺乏,倒是造成了長久以來社會的治史意識較之東方的中國淡漠了不少。反觀中國的歷史,恰恰是悠久的官方治史傳統直接影響着社會,從而使得社會的治史意識較之西方來說要濃郁了許多。例如長久以來,中國的百姓幾乎盡人皆知“青史留名”、“名彪青史”、“留取丹心照汗青”和“遺臭萬年”等警句名言。當然於此同時也不可否認,亦是由於官方壟斷着正史的書寫,結果使得民間社會的治史只能流於“野史”、演義,或假借其他藝術表現形式而寓於戲曲之中了。
3
如今看來,公衆史學作爲某種中間環節,已然成爲一種存在的必要。因爲其可以變成,專業史學家走下象牙塔、走向民間、走入社會大衆;民間業餘的歷史愛好者爲提升自身史學素養水平和研史/寫史方法技能的專業化水準而走近專業歷史學家,雙方互爲溝通/融合的橋樑。在職業歷史學家的參與和專業指導下,社會公衆自主地撰寫出關於自己的具有專業水準的歷史著述,以此來彌補職業歷史學家和官方治史之遺缺疏漏,進而讓人類社會的歷史變得更加豐滿充實。這,或許就是公衆史學的本質所在吧。
總而言之,正是上述從歷史到現實各自具有的差異性,決定了公衆史學與公共史學的區別。並且,僅憑中國悠久的治史傳統,以及數千年來民間的社會大衆對歷史書寫特有的喜好和對歷史述說表現形式擁有着豐富多彩的傳承,中國的公衆史學就應當有自己的理論和體系,而不該去扮演一個舶來品的角色!
作者:王旭東,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研究員
摘自:《徐州工程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