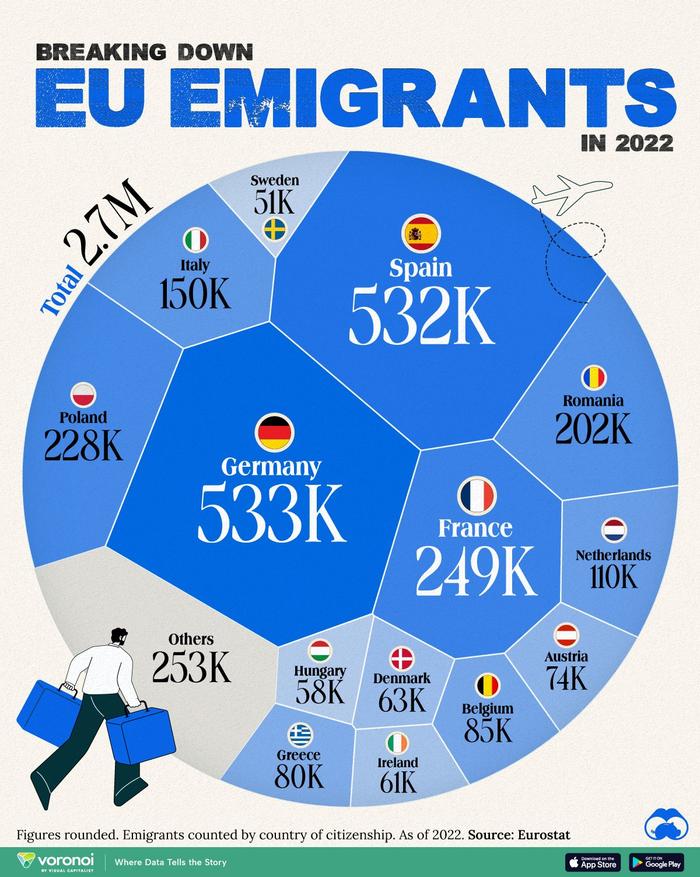上海大同裏原住民口述⑥|袁永定後人憶教育經歷與移民
【編者按】
大同裏是上海市靜安區的一條里弄,建成至今已有九十餘年曆史。大同裏的住戶中,有幾家在上海乃至中國近現代史上都有不可忽視的地位。《大同裏舊事》的作者邵光遠經過對王季堃家族、童潤夫家族、岑培遠家庭、周銘謙家族、袁永定家族、顧廷芳家族、周其音家族和陳子幀家族後人的採訪,築成了大同裏的一段風雲往事,也體現出海派文化下市民生活的別樣風采。
澎湃新聞請講欄目經上海文化出版社授權,刊發大同裏原住民的系列口述文章,邀讀者一同品味上海老弄堂舊事。

大同裏25號外景,前方建築物爲原崇德女中校舍。
大同裏25號到33號是一排新式石庫門房子,其中25號是典型的三上三下式石庫門建築,正門進入是客堂間,其兩側爲東、西廂房,其中的廂房又分爲前廂房、中廂房和後廂房三個聯通房間,這樣同樣的房型上下共兩層。整棟房的建築面積約300多平方米,如果要計算房間的話,25號有東西雙側上下兩層共十二間廂房,加上上下客堂間及一間亭子間就有15間房間。在25號建築的西北側後廂房處還建有一間汽車間,因爲袁家有輛奧斯汀汽車。大同裏這一排石庫門房子裏,只有25號是左右對稱廂房三上三下式樣的,其他門牌號都是單一側廂房的二上二下石庫門。

袁永定家族譜系
採訪時間:2014年5月8日、7月8日
受訪者:袁兆熊、鄒秀珍(袁家奶媽的女兒)
採訪者:邵光遠
採訪者:袁先生,你家很多親戚都已經不在上海居住,大部分都在海外生活了。請袁先生介紹一下你們家族的奮鬥史以及居住在大同裏時的一些情況。
袁兆熊:我祖父袁永定是從寧波定海到上海學生意的,從夥計開始做起,一點點積累起了原始資本。後來,就和我們家的世交徐家共同開辦了一家鴻康電料股份有限公司。當時在這家公司裏,我祖父擔任總經理,我父親袁世偉擔任襄理,主要負責對外業務。我叔叔袁世良也在這家公司上班。這個公司屬於家族企業,因此我舅舅也在公司裏上班。後來,公司業務開展得比較順利,不過我父親當時很年輕,思路較廣,認爲公司不應該僅僅只是經營批發買賣,也可以自己加工開發工廠,所以1949左右,他就有了自己的加工工廠。可惜,我父親去世得比較早。1953年,時年41歲的父親英年早逝,我當時也只有18歲。我們家族中我叔叔去世也比較早。我家我是老大,下面另有三個小妹。我叔叔家有我三個堂房弟弟。所以當我父親和我叔叔先後去世後,我母親和嬸嬸就挑起了兩個家庭的重擔,是很不容易的。我父親和29號的陳子幀年齡相仿,他們之間關係密切,如果我父親在世的話,他一定可以說出很多關於陳子幀的故事。

袁永定

袁永定妻子丁修曾

袁世偉、謝彬霞夫婦合影。
採訪者:你祖父是什麼時候去世的?後來工廠發展又如何?
袁兆熊:我祖父是在1966年去世的。工廠在公私合營的時候,變成了上海人民電器廠,在中山公園附近,目前這家廠依舊存在。
採訪者:據我瞭解,你們袁家也是一個大家族,在25號這一整棟兩層樓面的石庫門大宅中居住了整個家族的成員,而且還有幾位幫傭工也住在其中。你們家和傭人們的關係也很好,就像自家人一樣彼此信任,和現在的僱傭關係很不一樣,現在幾乎不可能有這樣深的感情了。
袁兆熊:確實,在我家中幫傭的僕人都很忠心。作爲主人,我們也沒有把和他們的關係當做純粹的僱主和幫傭的關係來看。例如我二妹的奶媽,她不但餵養了我二妹,還帶大了我的三妹,我的兒子出生後也是由她帶大的,並且家中所有的家務都由她負責。另外,我祖父的司機也住在25號,後來司機的孫子和我們家關係也很好。現在我年紀大了,只要一個電話,他就會立刻來幫忙。
有件事我記憶深刻。“文革”時,我們家裏人都在上班,紅衛兵來抄我家。爲了保護家中的一些財物,奶媽靈機一動,把家中從香港寄來的油罐全部打開,防止被他們抄走。以前我上班是在閔行,週末時我和太太一起到25號來居住。當我們夫妻在管教自己兒子時,奶媽又會出來,主張在25號這裏不能打孩子,要教訓就回閔行再打,奶媽真的是把我們的兒子當作她自己的兒子一樣。平時的家庭事務都是由奶媽來掌管,所以她很瞭解家中每個人的口味,每次買菜都會動足腦筋來安排食物。

袁永定長孫袁兆熊。
採訪者:今天有幸,你們家奶媽的女兒鄒秀珍也在。那就請鄒女士介紹一下你所知道的袁家的事情。

奶媽的女兒鄒秀珍。
鄒秀珍:我母親原來是在常熟鄉下的。1940年左右,她的丈夫和大兒子被日本人殺害,當時她懷裏還抱着一個喫奶的小兒子。一個20多歲的女人,拖着一個襁褓中的孩子無依無靠,生活很是艱難。這時相鄰的好心人介紹她來上海做奶媽。她就把小兒子送給人家了。自己孤身來上海,就到了袁家爲兆熊大哥的二妹做奶媽。後來,我母親又通過別人介紹認識了我父親,我出生後就是一直由我母親帶着生活在25號,我和兆熊大哥,包括他的幾個妹妹都是以兄妹相稱的。兆熊大哥的媽媽我叫她好媽媽,因爲我們感情一直很好。1966年,袁家的人都被掃地出門,但我和母親還繼續生活在25號。母親十多年前去世,當時兆熊大哥、大嫂,還有他們的兒子,包括袁家所有在上海的親屬,都來參加我母親的大殮。
採訪者:我記得當時“文革”開始後,袁家全部被掃地出門,而你和你母親還是住在大同裏25號一樓東側後廂房。東側前廂房以及西側廂房做過生產組的工場,後來又做過託兒所。
鄒秀珍:“文革”開始後,我和我母親還是延續着以前在袁家的居住方式,依然居住在25號一樓東側後廂房。25號底層的許多房間都做過里弄裏生產組的工廠。生產組的成員主要是由一些家庭婦女、病休在家的知識青年和殘疾人士組成。後來,生產組撤退後,又改成託兒所,也辦了好幾年。後來,就逐漸有其他人家入住。整個25號最多時住了13戶人家。
採訪者:請問袁先生,你們家在子女教育問題上有什麼特別的要求和規範?這樣的家庭教育模式對你本人有什麼影響?
袁兆熊:作爲家族中的長孫,我從小就被長輩們以一名家族事業接班人的要求來培養。作爲子女,我們能感覺到,即使是家庭富裕,長輩們仍然對我們要求很高。當然,優越的家庭條件也很好地支持了我們的發展。我中學一開始就讀於聖約翰中學,這爲我的英語打下了良好的基礎。初三就讀於育才中學,高中就讀於南洋模範中學,目標就是要考取上海交通大學,爲接手家族事業做好充分的準備。大學讀的是交大通訊專業,由於成分關係,只能進入電信局實習,畢業後被安排到位於閔行的一機部的部屬中專做教師。如今,這所學校已經升級爲上海電機學院。我幾個妹妹都在聖瑪利亞女中就讀,大妹考進了上海外國語學院,先學俄文後改學英語,並留校做了老師。二妹畢業於華東化工學院(現華東理工大學)抗生素專業,後就職於中美合資施貴寶藥業有限公司,任工程師。三妹畢業於復旦大學英語系,後任教於華東師範大學外語系。現在我們都已經退休,幾個妹妹都移民海外。三個堂弟“文革”後移居香港,由於在中學時打下了良好的學習基礎,所以在香港各自的事業上都有所造詣。

袁兆熊和母親謝彬霞合影。

袁兆熊長子和祖母謝彬霞合影。
採訪者:袁先生,你覺得年輕求學時能夠給你留下深刻印象,並有切身體會的事情有哪些?
袁兆熊:我們中學求學時,長輩們把我們安排到一些知名的學校去學習,雖然我們當時並不太理解長輩們頻繁給我們換學校的動機何在,但等到長大懂事後,我們就體會到他們對我們的良苦用心了。我記得那個時候我父母還給我們請了家教,而且都是一些很有名的學校的老師。這些老師不僅擴大了我們的知識面,而且還教會了我們一套很有效的學習方法,這些東西對我們都是終身受用的。90年代初,我小兒子在美國留學,並且被波音公司入取。但他突如其來的一場疾病使我在毫無準備的情況下趕赴美國。不過因爲在中學時打下的語言基礎,讓我初到美國後,在語言方面並沒有碰到太多的障礙。雖然這是很平常的事情,但卻讓我深切地感受到,這和自己在青少年時期所受到的紮實的基礎教育是分不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