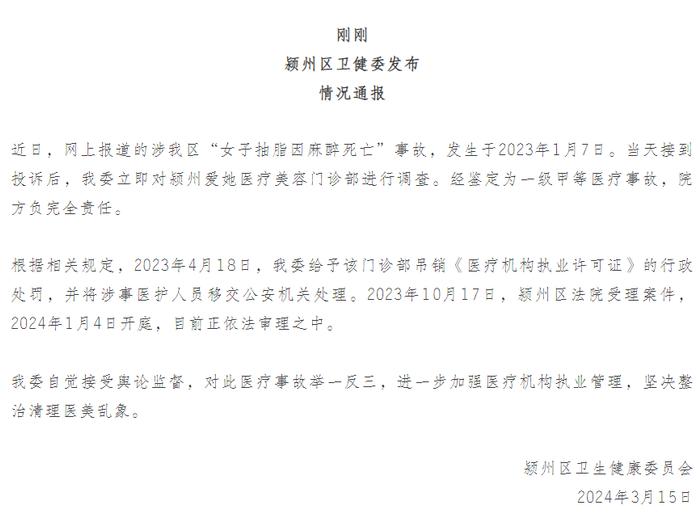不只器官能移植,糞便也可以
可能從沒有什麼醫療手術讓你光看名字就覺得噁心,糞便移植做到了。所謂糞便移植就是字面上的意思:把糞便移植到另一個人的大腸裏。它應該是醫學史上技術含量比較低的手術了。 爲什麼要把糞便移植到別人身上?理由通常是因爲接受者大腸裏的細菌種類嚴重失衡,捐贈者的糞便能爲彌補缺少的細菌重新達到平衡。 之所以會造成細菌不平衡,通常都是因爲艱難梭菌(簡寫爲C. diff)影響。艱難梭菌會在抗生素破壞腸道細菌之後出現,腸道菌羣,通常都是互相控制保持平衡的。但是艱難梭菌的出現佔據了它們的繁殖空間。而且艱難梭菌產生的毒素會傷害腸道的細胞,導致抗治療的腹瀉並且反覆發作甚至可能致死。每年有超過25萬人感染艱難梭菌,其中約14000人死亡。 艱難梭菌感染不僅因使用抗生素而生,還能用抗生素來治療。腸道微生物狀況因爲抗生素進一步失去平衡,艱難梭菌又繁殖更多,因此又要用更多抗生素來治療,循環往復陷入惡性循環。糞便移植能有效阻擋艱難梭菌繁殖,經過一次治療能治療94%的艱難梭菌感染,相比之下抗生素的治療效果只有31%。 但是,從法律上講,糞便移植(有時也被成爲FMT,即糞便菌羣移植)是存在問題的:它們是藥嗎?還是捐贈的器官、組織?食品藥品監管部門要不要監管糞便?就算要監管,又要如何實施? Michael Graziano導演在他2014年拍電影《抵抗》(Resistance)時對此一無所知,《抵抗》的主題是當抗生素不再有效了會發生些什麼,刻畫了許多個令人心痛的患者故事。其中一個故事是說田納西州15歲的女孩Lauren,因爲因爲耐甲氧苯青黴素金黃葡萄球菌而服用了強劑量的抗生素,醫生花了兩年時間想要把它治好結果女孩的病情卻越來越嚴重,由此Lauren的家人得知了糞便移植…… 本文作者問了導演幾個問題,想知道他爲什麼要花幾個月的時間去創作關於他人的糞便的影片。 Maryn McKenna(作者):是什麼讓你決定講述這個關於糞便移植的故事? Michael Graziano:在籌劃拍攝《抵抗》這部電影的時候,我對人類微生物羣有了很大興趣,通過了解生活在我們體內或皮膚上的微生物生態能開創出人類未來健康的新天地。我之前從沒聽說過艱難梭菌也不知道糞便移植,但當我瞭解了之後我發現我認識的、交談過的人中也沒有任何人知道這個東西。我想我得盡力彌補人們對糞便移植的知識空白。 糞便移植是很隱私的事情,你是怎麼說服這家人蔘與電影的? 我很幸運地跟一些坦誠、熱情又誠實的醫生、研究人員和病人合作過,其中包括範德比特大學(Vanderbilt University)醫療中心。有個朋友引薦我認識了那裏的胃腸病學家Maribeth Nicholson博士,他出演了這部電影,還頻繁演示了幾次糞便移植。Lauren就是他的病人,Nicholson跟她及其家屬介紹了我的計劃。他們告訴我,如果在最初被告知Lauren感染了有害細菌時對此有更多瞭解就好了,並同意了參與電影幫助其他經歷同樣痛苦的家庭。 糞便移植目前仍被部分醫療機構視爲不合法的手術,你也有這種感覺嗎? 它之所以很難被接受主要是審美原因,直白點說就是覺得噁心。不過可能也有關於這個手術的長期影響的顧慮,畢竟這方面還沒被百分百研究清楚。弄懂其醫學原理。但我看到同行評議期刊上的文章都在證明糞便移植的有效性,還和做糞便移植的手術交談了,它的好處已經不能更明顯了。有數據顯示,糞便移植的安全性非常高——零不良反應。相比較更真實也更令人生畏的抗生素治療法,糞便移植值得我們更多的關注。 你感覺它會越來越普遍嗎? 沒錯,因爲越來越多的醫生、患者和普通人瞭解它。但糞便移植的普及面前擺着很多挑戰,醫療系統對抗生素很熟悉;抗生素有明確的生產和監管機構。而這些條件在糞便移植上都不存在,雖然我們看到很多事實證明糞便移植能產生明顯效果,代替抗生素來應對因濫用抗生素導致的耐抗生素感染危機。但是糞便移植沒有形成明確的商業模式,管理、操作方針也並沒有百分百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