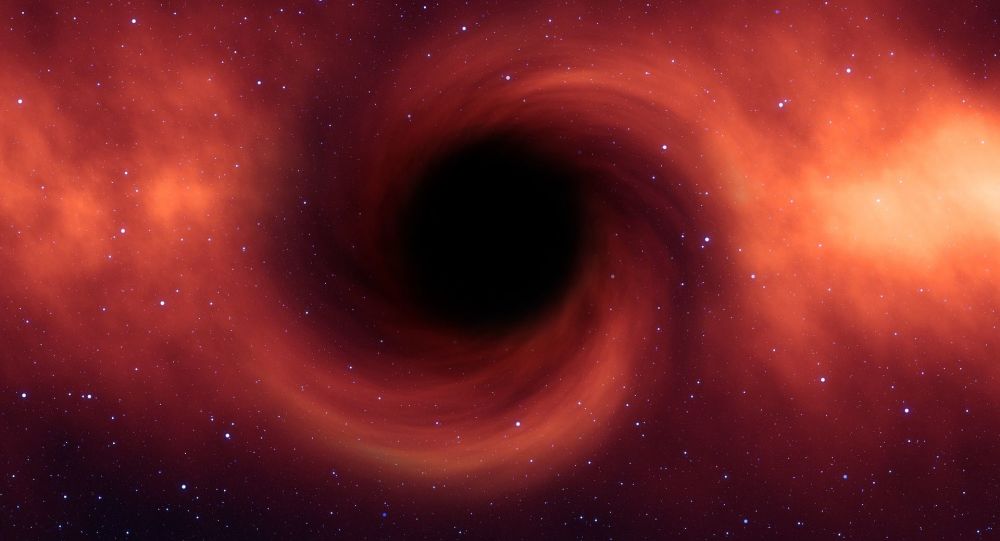紙巾與烘手機的“百年戰爭”
摘要:紙巾和烘手機各有長短。2015年,英國威斯敏斯特大學微生物學家基思·雷德韋教授安排紙巾、普通烘手機和Airblade同場競技。
廁所是藏污納垢的地方,公共廁所尤其如此。如果你能意識到被無數如廁者摸過的門把手上棲息着多少有害微生物,最不講究的人恐怕也會到水池邊洗個手。
那麼問題來了:你是把溼漉漉的手放到烘乾機下,等待氣流帶走水分,還是從紙盒裏抽出一兩張紙巾擦手?
這個問題聽起來無聊,背後卻隱藏着一場紙巾與烘手機的“百年戰爭”。
較量從最開始就不對等
和許多人的認知不同,擦手紙巾和烘手機都是20世紀初的發明。1907年,紙巾在美國費城斯科特紙業公司誕生。14年後,史上首臺烘手機在紐約註冊了專利。
此後100年的大部分時間裏,紙巾是公共廁所的王者。1965年,英國演員喬納森·羅斯在專著《好廁所指南》中註明了倫敦所有烘手機的位置:100多間公廁中,配了烘手機的只有5個,其他的僅提供紙巾。在當時的人們看來,紙巾的優勢是壓倒性的:無需百無聊賴地等待,無需忍耐高達90分貝的噪音,更不用擔心被突然壞掉的機器弄傷。
紙巾一枝獨秀與烘手機制造商的不思進取不無關係,情況直到二戰後才逐漸改觀。1948年,喬治·克萊門斯在芝加哥成立“世界烘手機公司”時,恰逢木材匱乏,紙價飆漲。克萊門斯趁勢推出裝有圓形金屬按鈕、酷似小坦克的Model A型烘手機,上市即成爆款,世界烘手機公司由此成爲行業巨頭。即便幾經易主,該公司始終堅信,Model A是同類產品的巔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據說,該公司有員工申請研發資金,上司回覆:“誰需要更好的烘手機?”
2006年戴森Airblade橫空出世,紙巾的地位才真正被動搖。據預測,到2020年,全球公廁紙巾的銷售額有望達到40億美元,烘手機的銷售額將上升至8.56億美元。戴森公司發言人表示,2012年至2020年,烘手機將從造紙商手中搶走8.73億美元。
Airblade的前衛設計是其賣點。它向上吹風,好似“開口笑”,使用者得把手整個放進它的“嘴”裏;流線型的銀色外殼未來感十足,曾無縫融入2009版科幻劇《星際迷航》;風速每小時600公里,機器啓動10秒後,雙手殘留的水分不超過0.1克;能過濾99.95%直徑0.3微米以上的顆粒……它的售價也相當“美麗”,是普通烘手機的3倍。
Airblade不是世上第一臺高速烘手機,卻憑藉出挑的外觀和大膽的營銷顛覆傳統,讓烘手機逐漸成爲提升公廁檔次的重要配件。由此,烘手機與紙巾開始勢均力敵。
早期的烘手機故障率高、噪音大。圖片來源 英國《衛報》
紙巾的劣勢其實很多
紙巾和烘手機各有長短。對公共衛生設施的運營者而言,首先考慮的是成本。
“我跟客戶說,一臺烘手機的前期成本大概是三四百英鎊,但每年只需5英鎊電費。”烘手機公司Veltia英國區總經理馬特·安德森告訴英國《衛報》,“而紙巾每年要好幾千英鎊。”
如果用紙巾,就得派人不斷把空盒裝滿,把廢紙簍清空。一旦動作慢了,廢紙巾“溢出”到溼乎乎的地板上,很快就會變得像爛泥一樣。更別提總有人隨意把紙巾扔進馬桶,造成堵塞。美國田納西州立大學把紙巾盒統統換成烘手機後,每年省下了用於疏通下水道的10萬美元。
紙巾帶來的麻煩不止於此。英國一大學公廁裏的紙巾經常不翼而飛,校方給紙巾盒上了鎖,很快,盒子也丟了。2018年,美國某社區大學連續4次失火,都是因爲有人點燃了廢紙簍。
從環保角度看,紙巾同樣不是個好選擇。即使是再生紙,二次使用後也無法回收。“我媽都覺得幹我們這行就是在砍樹。”歐洲紙業協會(ETS)主席法尼斯·帕帕科斯塔斯自我揶揄道。
烘手器製造商揪住這一點大做文章。2011年,戴森公司委託麻省理工學院進行了一項對比研究:用紙巾擦手,每人每次用兩張紙巾;烘手機吹乾手最快要12秒,最慢的要30秒。結果顯示,在生產、運輸和使用環節,紙巾比最高效的烘手機多產生70%的碳排放。
戴森公司憑藉出色的產品設計和性能,改變了烘手機的弱勢地位。圖片來源 美國The Verge網站
烘手機因衛生隱患丟分
面對烘手機的兇猛攻勢,紙業巨頭不肯坐以待斃。他們幾經思量,決定打出“衛生”這張牌。他們贊助了更多學術機構,相關研究大多圍繞兩個問題:烘手機會不會讓雙手沾上更多病菌?烘手機會不會像“秋風掃落葉”一樣,幫細菌和病毒去更遠處旅行?
2015年,英國威斯敏斯特大學微生物學家基思·雷德韋教授安排紙巾、普通烘手機和Airblade同場競技。研究人員把手浸泡在病毒溶液中,分別用三種方式把手弄乾,再將培養皿放在不同的距離,捕捉擴散的病毒。實驗結論令烘手機的擁躉冷汗直冒——Airblade傳播病毒的範圍是最大的。
《Airblade傳播病菌是紙巾的1300倍》《烘手機把細菌帶到你手上》《烘手機比大便還髒》……雷德韋的論文發表不久,種種聳人聽聞的標題紛紛霸屏。雖然戴森反駁說,實驗的設計有問題,但在媒體推波助瀾下,在公衆的恐慌情緒中,它的自辯被淹沒了。
“烘手機能迅速把水吹乾,也會把殘留的微生物吹到空氣中。”英國利茲大學微生物學家馬克·威爾科克斯向澳大利亞廣播公司解釋道,“洗淨的手上也有細菌,不乾淨的手細菌更多。最糟糕的是把手衝一兩秒,然後吹乾。這樣還不如不洗。”
恐慌一產生,便會以幾何級數擴散。一名微生物學專業學生把培養皿放在Airblade中吹3分鐘,然後培育。48小時過去,令人震驚又噁心的場面出現了:培養皿中的真菌和細菌瘋狂繁殖,長出一團團白毛。這位學生在社交媒體上發佈了培養皿的照片,一週內有50萬人分享。
在這一波輿論戰當中,戴森落了下風,但它不甘心把陣地拱手相讓。據英國《每日電訊》報報道,雷德韋的研究成果發表不久,戴森便在YouTube上發佈了視頻《紙巾的骯髒小祕密》。“你今天用紙巾了嗎?它可不像你想得那麼幹淨。”一個親切但略帶威脅意味的畫外音說,“高達88%的未使用紙巾攜帶大量病菌。一旦進入洗手間,空氣中的細菌乃至上一名如廁者手上的細菌,就會通過紙巾傳給你。”
開始爭論前,請洗手
這場事關公共衛生的爭論在理想主義和實用主義間搖擺,至今未落幕。以雷德韋教授爲代表的一派稱,衛生間應儘可能遠離健康風險。戴森公司領頭的陣營則主張,更重要的是現實地評估風險,“我們每天都接觸各種各樣的細菌,但並沒天天生病。”
雙方隔空過招久了,有時也會狹路相逢。雷德韋回憶說,在荷蘭舉行的一場展會上,戴森公司的幾位高管闖進他的演示現場,大大咧咧地在前排就座。“看到他們,我的團隊成員有點兒緊張。我告訴同伴們,‘別擔心,我們會捍衛自己的’。”
戴森方面給出的說法有所不同。當天在場的一位高管稱,有個ETS的人守在門口簽到。“我們出示工牌時,她像見了鬼一樣,阻止我們進去。”在這名高管眼中,那次會議“的確是對戴森的公開攻擊”。戴森員工向雷德韋提出質疑時,沉悶的會場氣氛變得緊張。“這個會很無聊,因爲我們的出現纔有了點兒看頭。”他笑稱。
美國The Verge網站評論說,在紙巾與烘手機的持久戰中,恨意超越了理性,聳人聽聞的報道無異於煽風點火。科學在金錢面前沒能守住底線。“如果你事先得知自己的研究成果會被贊助機構用於何種目的,那麼,你就不會特別認真謹慎地對待它。”
有人指出,雙方的爭論忽略了一個關鍵事實:洗手纔是關鍵。世衛組織給出的建議很少提到該用紙巾還是烘手機。英國有調查顯示,只有32%的男性和64%的女性上完廁所後洗手。
所以,從現在開始,如廁後要記得給雙手塗上肥皂或洗手液,按“洗手六部曲”完成所有步驟,在心裏唱兩遍《生日快樂歌》,然後用清水沖洗。只有這樣,我們纔有資格繼續討論,紙巾和烘手機到底誰更好。
原文刊載於《青年參考》6月13日13版
作者 胡文利
編輯 張昊天
微信製作 母傳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