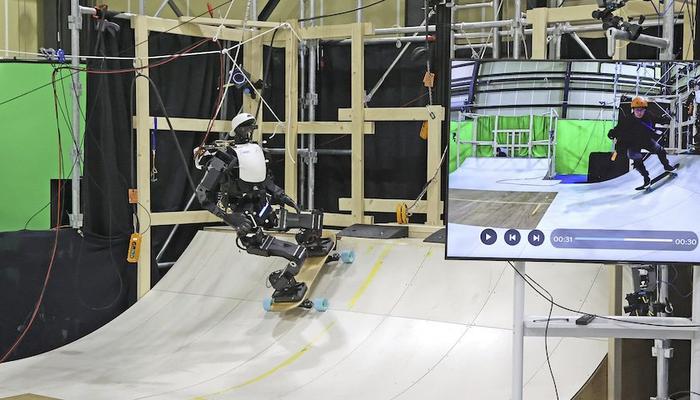曲波夫人劉波回憶林海雪原的日子
讓我們一起傾聽親歷者的故事,感悟歷史中的人、人的歷史……
1945年日本投降後,膠東地區的共產黨部隊主力奉命與國民黨軍隊搶佔東北。曲波所在的部隊沿着遼東一路打到五常縣。又奉上級命令到北滿剿匪,沿路很多人蔘軍。到了牡丹江就發展成兩個團,曲波擔任牡丹江二團副政委,當時22歲。
楊子榮確有其人
楊子榮是山東膠東半島人,1945年參軍,在曲波所在的部隊,一直打到東北。楊子榮年紀大,打過遊擊。曲波覺得楊子榮經歷多一些,性格穩當,善於與人講各種故事,就讓他當偵察排長。曲波在部隊表揚楊子榮,說他對付土匪有大智。他是在活捉匪首座山雕以後的戰鬥中犧牲的。當時《東北日報》刊登了戰鬥英雄、偵察英雄楊子榮犧牲後,二團領導、海林縣委領導抬着楊子榮棺槨,葬於海林縣境內的報道。這份《東北日報》至今仍收藏在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內。
1981年,海林市重新選了墓地遷葬楊子榮,建立了烈士陵園,豎起了高高的墓碑。 2003年,我回到海林市故地,專門參觀了烈士陵園裏的楊子榮陵墓。在參觀中我還得知,曾擔任過“楊子榮排”的排長們聚在一起,到楊子榮陵前祭奠過,並捐款萬元用於陵墓的修繕。
一身功勳的楊子榮沒能看到剿匪的最後勝利,這使活着的戰友們永生痛惜。
祕密創作《林海雪原》
1950年12月,曲波依依不捨地脫下軍裝,擔任瀋陽機車車輛廠黨委書記、副廠長,後來又到齊齊哈爾車輛廠當書記。他是二等甲級殘廢,當時都是拄着雙柺奔波。1955年還在東北時,他因反對蘇聯推行的“一長制”而挨批,在委屈情緒中不由想起了槍林彈雨中的生死戰友,便在寫檢討的稿紙上列出一串戰友的名字:楊子榮、高波等。他有了創作長篇小說的想法,便偷偷地試寫了一部分文字。
1948年受傷的曲波和妻子劉波
1955年初,曲波和我奉命來到北京。曲波擔任一機部第一設計院副院長。到了北京後,他又接着寫下去,還是保持着祕密狀態,一下班就躲藏在屋子裏寫作。那時家中寫字桌中間的抽屜一直是半開着,一聽一機部鄰居同事來找,曲波就立即把稿件塞進抽屜。他這個人的缺點是愛面子,自尊心強,怕寫不好鬧得滿城風雨。
曲波親身經歷並指揮了林海雪原剿匪戰鬥,驚險激烈的戰鬥經歷使他積累了大量素材。當小說初稿寫完前3章、15萬字時,他感到自己的文字不能表達內心的情感,一氣之下把原稿付之一炬。可犧牲的戰友的英勇事蹟激勵他堅持寫下去。一天夜裏,當曲波寫到楊子榮犧牲的章節時,抑制不住自己的情感,潸然淚下。他把我叫醒說,他寫到楊子榮犧牲,寫不下去了……所以,《林海雪原》開篇就寫道:“以最深的敬意,獻給我英雄的戰友楊子榮、高波等同志,以表達對戰友的深切懷念。”
我支持他寫作,是他作品的第一讀者,也是他的抄稿員。參軍前我是小學四年級水平,他是小學五年級半。他小時候看了《三國》、《水滸》、《說岳》等,影響不小,參加革命後又讀了《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受到很大的教育和鼓舞。他有時一天寫1萬字,我再用兩三天抄出來,遇到他空着的地方和自己生造的字,我再去查字典補上。
家中房間少,放不下兩張桌子,我就在縫紉機上抄稿。每抄完一個章節,就用毛線和布條裝訂起來。家務事我全包下,到了星期天,我特意帶4個孩子到公園去玩,讓他在家安心寫作。
有一次,一機部辦公廳召開傳達中央文件的大會,曲波事先已看過文件,就坐在會場裏專心寫出了“小分隊駕臨百雞宴”一章。經過一年半業餘時間的艱苦創作,小說《林海雪原》終於寫完了,約40多萬字。我買了兩米布,剪了兩個包袱皮,將文稿裝了兩大包,我倆一人拎着一包稿件就到了我家斜對過外文局大樓的《中國文學》編輯部,但發現裏面多是外國專家。他們建議我們去東總布衚衕作家出版社投稿。
我們坐公交車去了。曲波對接待的人說:“我不是作家,你們看看行不行?如不用,你們打個電話我來取。”曲波再三叮囑打電話一定要打到家裏,怕機關知道走漏了風聲。出版社的龍世輝等編輯看了,打電話到我們家,說:“你來吧。”曲波去了以後說:“我取稿子來了。”沒想到龍世輝卻說:“我們確定要出你的稿子,需要做一部分修改。”《人民文學》副主編秦兆陽知道後,先在《人民文學》選發了《奇襲虎狼窩》章節,並在“編者按”中寫道: “作者是一位解放軍的軍官,現在工業部門工作……這本書將是我國文學創作上的一個可喜的收穫。”1957年書出來後有不小的反響。
書裏書外的愛情故事
我和曲波是山東黃縣老鄉,但參加革命前彼此並不認識。“七七”事變後,全國掀起了抗日高潮。我倆受抗日思潮的影響,於1938年參加了八路軍。曲波16歲就在膠東軍區13團當文化幹事,17歲當指導員。我15歲在膠東軍區後方醫院當護士長,同年入黨並任醫院黨委委員。1942年,曲波帶領工作檢查團到醫院檢查工作,我們第一次相識。1946年,曲波由於腸道疾病住院治療。共同的戰鬥經歷、特殊的醫院環境使我們結下深深的情意。這一年在組織的安排下我與曲波舉行了簡樸的婚禮。婚後第二天,曲波就去參加剿匪戰鬥了。
剿匪鬥爭非常艱苦,曲波帶着部隊長時間在深山密林打仗,我們很少有時間住在一起。當時我擔任政治部祕書,曲波回來了就住在我們辦公室的單人牀,往往是住一晚就走,第二天就得趕到剿匪駐地。每次回來人都顯得非常疲倦,有時鞋襪都不齊全,腳趾露在外面。1946年冬天,他回來時身上長滿疥瘡,兩腿都是,我從醫院找來藥膏,讓他烘爐子,使勁地全身擦抹了幾遍。
曲波生前曾談過“小白鴿”藝術形象的創作過程。他說,在茫茫林海中,我們面對的是極其兇殘的敵人,惡劣的環境根本不允許小分隊帶女兵作戰。爲什麼要寫一個女衛生員呢?他想,我們的戰爭是爲了和平,在森林裏除了大雪就是野獸和土匪,單純地記敘這些太冷酷、太單調了,所以他有意識地創造了一個“小白鴿”。“如果你們要問‘小白鴿’是參照何人塑造的?我可以告訴你們,是我的愛人。她活潑伶俐、聰明能幹,14歲參加抗戰,15歲就成了膠東軍區後方醫院的護土長、醫院黨委委員。我就以她的性格特徵,創作了白茹這位‘萬軍叢中一小丫’,以此烘托和平的氣氛。”曲波說,“小白鴿”爲傷員擦身子的細節,融進了抗戰時期我和一些護士的故事,也加進了我們夫妻之間同患難的感情。所以,小說《林海雪原》中的人物有生活的真實,也有藝術創作。
有一次賀龍元帥在醫院和曲波熱情交談。賀龍很幽默又很認真地問:“白茹呢?白茹怎麼沒陪你來?”曲波忙解釋說:“我愛人叫劉波,不叫白茹。”賀龍元帥笑道:“不行,改過來,叫白茹!”賀帥風趣的話把大家都逗笑了。
終生牽念林海雪原
在戰爭年代,我們倆都在前方後方工作,只有到了齊齊哈爾纔有了一個家。工廠離宿舍較遠,有時踏着大雪歸來,就會想起飛襲威虎山的狂風暴雪的日子。
那時,曲波與戰友們一起商討剿匪方案,由楊子榮帶5名偵察員裝扮成上山入夥的土匪,潛入匪巢活捉了座山雕。座山雕被抓住後,關在政治部保衛處。我見過他,是一個70多歲的小老頭,長得有點怪。解放軍在屋裏、走廊養了幾盆花、幾隻兔子,讓他種花、喂兔子,沒有對他懲罰,後來他自己老死在裏面。
曲波一輩子都記掛戰友們,思緒時常回到茫茫的林海雪原。他在《林海雪原》的後記中這樣寫道:“及抵家,一眼望見那樣幸福地甜睡着的愛人和小孩子,一陣深切的感觸湧上我的心頭……我的宿舍是這樣的溫暖舒適,家庭生活又是如此的美滿,這一切,楊子榮、高波等同志沒有看到……”
《林海雪原》中少劍波的形象有80%的成分取自曲波自己的經歷。他總說自己身上有一股革命的英雄主義。在小說中,可以找到他們那一代軍人犧牲奉獻的高尚精神和英勇頑強的時代內涵。
曲波晚年因病於2002年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