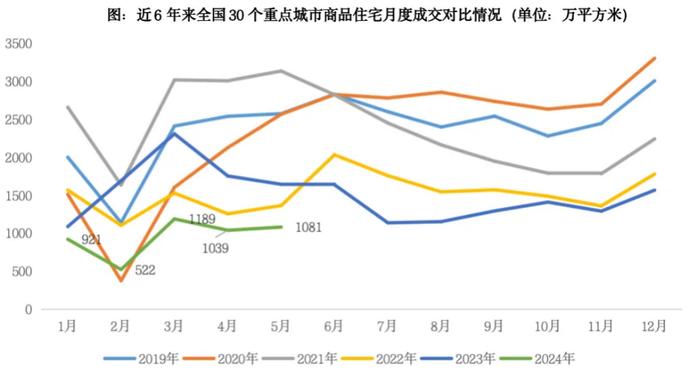实地跟拍抑郁症患者的一天:请给他们多一点关爱!
凌晨两点,37岁的杨思明站在4米高的屋顶上,猛得嘬了口烟,望着西南方向。那是山西运城的空港经济开发区,能隐约看到霓虹灯照耀下的高楼。那是他向往的“城里的世界”。杨思明患抑郁症18年,他因此退学,数度走出村庄到城里打工,却一次次因犯病而被禁锢回黄土地。“要是有那么一天,我病好了,还是想感受城里的世界。”
杨思明所在的村子,坐落在中条山山脚下。仰赖着黄土地,举村搞起了蔬菜大棚规模经营。通往村子的路颠簸荡尘,但村子里不少人家年入十几万,开着私家车。图为杨思明正在自家的蔬菜大棚上放草帘子,远处就是中条山。
中学时代的杨思明,成绩稳居班里前十,他想着有一天能去城里生活,不再像父辈一样在几亩地里靠天吃饭。高二开始,没有来由的,他变得沉默,一天说几句话,一只手都能数得出。成绩一次次下滑。夜深,室友鼾声起,杨思明在上铺憋得难受,他跳下床,跑到厕所里,一个人喘着长气低吼。图为杨思明正在照顾自家的蔬菜大棚。
这样的日子过了两年,没人注意到他的痛苦,大家只觉得杨思明越来越不爱和人打交道。高三退学时,班主任捶着他的胸口说“你这小子就不好好学。”回到村里,杨思明的状态仍不见好转。“年纪轻轻就在村里扛个锄头,能干啥,别人小瞧你。”杨思明想挣脱农民的身份,他去运城打工,做水泥工、搬砖工。“到干活儿的时候没劲儿,做不了。晚上怎么都睡不着,快憋疯了。”最终,他因抑郁重回村庄。图为杨思明正在自家的蔬菜大棚上收草帘子。
最终,他一次次出村、打工,又一次次犯病、回家,折腾了18年。在被折磨的起初5年里,杨思明一直以为,自己是神经衰弱,伴随着失眠、头痛。直到2003年,快被熬疯的他到北京挂了专家号,才第一次知道,自己得的病叫抑郁症。
2005年,杨思明在村里结婚生子,认了农民的身份。他想把自己当成家里的顶梁柱,可因时不时看病住院,十亩地依然要靠61岁的父母种。抑郁严重的时候,杨思明觉得自己要被掰成了两半。“那种痛苦我说不出来,绝望,就是想死。”
无数次,他想到死,他琢磨过在屋后上吊,也常站上自家的屋顶,想跳下去,但又怕死不了反成残疾,拖累家人。“我真的想死了一万次。”可上有父母,下有儿女,杨思明说自己剩下的只有一个字——熬。杨思明家房顶上的一把摇椅。他说,看城里做生意的躺在摇椅上睡得很香,自己总睡不着,于是买了把,想靠它好好睡觉。刚开始可以,但很快就也不管用了。
抑郁症患者,敏感、多疑、爱钻牛角尖,有着和其他疾病一样完整的生化过程,最大特点就是不能如正常人一样生活,有自杀倾向。据北京安定医院精神科主任医师姜涛介绍:对于抑郁症,多数人的认识还非常肤浅。目前全国有超过9000万人患抑郁症或有抑郁倾向。目前全国地市级以上医院对抑郁症的识别率不到20%,换言之,即80%的患者被误诊或漏诊,在现有的抑郁症患者中,只有不到3%的人接受了相关药物治疗。
杨思明的妻子掩面落泪,这么多年她也没搞清楚丈夫的病,她是结婚后才知道他有病。她只想好好过日子。村里比谁家房子盖得高,她就借了13万元盖起了新房和3米高的大门。她想,盖起新房,丈夫的病也许就好了。结果,房子盖起了,杨思明的病还没好。她又想,生个儿子就好了。现在,儿子出生快2年了,病还没好。
在长达8年时间里,杨思明每天服用大量的氯硝西泮片。这种药有镇静催眠的作用,长期服用会产生依赖性,但他起初并不知晓,直到2012年才被运城市中心医院告知不该大剂量服用,可他已经戒不掉了。在生活重担下,杨思明每月仍需花600-700的药钱,去太原看一次病就花去了7000多块。他想做心理咨询,运城一小时500元的价格让他只做了一次就再不延续。而同类的咨询,北京私人专家一小时300-400元,安定医院医保范围内20分钟只需20元。
杨思明坐在自家的蔬菜大棚上发呆。他最羡慕的是别人能顺畅打牌,这是村里最常见的消遣方式。得病后,他明显感觉到思维迟钝,村里人叫他斗地主、打麻将,他不敢去。有时他强迫自己坐到了牌桌上,可是一手顶好的牌,被他打烂,嘴快的同村人脱口而出:“你脑子被驴踢了吧!”
杨思明习惯把摩托车油加满,加足马力,在去运城的柏油马路上,漫无目的地疾驰。风吹打着头发,他有一瞬觉得,所有烦恼都被带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