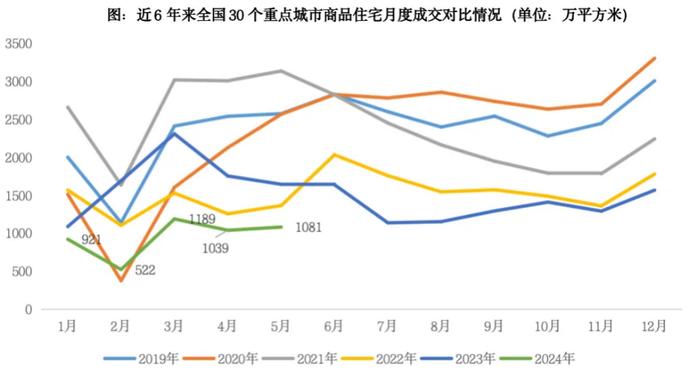實地跟拍抑鬱症患者的一天:請給他們多一點關愛!
凌晨兩點,37歲的楊思明站在4米高的屋頂上,猛得嘬了口煙,望着西南方向。那是山西運城的空港經濟開發區,能隱約看到霓虹燈照耀下的高樓。那是他嚮往的“城裏的世界”。楊思明患抑鬱症18年,他因此退學,數度走出村莊到城裏打工,卻一次次因犯病而被禁錮回黃土地。“要是有那麼一天,我病好了,還是想感受城裏的世界。”
楊思明所在的村子,坐落在中條山山腳下。仰賴着黃土地,舉村搞起了蔬菜大棚規模經營。通往村子的路顛簸盪塵,但村子裏不少人家年入十幾萬,開着私家車。圖爲楊思明正在自家的蔬菜大棚上放草簾子,遠處就是中條山。
中學時代的楊思明,成績穩居班裏前十,他想着有一天能去城裏生活,不再像父輩一樣在幾畝地裏靠天喫飯。高二開始,沒有來由的,他變得沉默,一天說幾句話,一隻手都能數得出。成績一次次下滑。夜深,室友鼾聲起,楊思明在上鋪憋得難受,他跳下牀,跑到廁所裏,一個人喘着長氣低吼。圖爲楊思明正在照顧自家的蔬菜大棚。
這樣的日子過了兩年,沒人注意到他的痛苦,大家只覺得楊思明越來越不愛和人打交道。高三退學時,班主任捶着他的胸口說“你這小子就不好好學。”回到村裏,楊思明的狀態仍不見好轉。“年紀輕輕就在村裏扛個鋤頭,能幹啥,別人小瞧你。”楊思明想掙脫農民的身份,他去運城打工,做水泥工、搬磚工。“到幹活兒的時候沒勁兒,做不了。晚上怎麼都睡不着,快憋瘋了。”最終,他因抑鬱重回村莊。圖爲楊思明正在自家的蔬菜大棚上收草簾子。
最終,他一次次出村、打工,又一次次犯病、回家,折騰了18年。在被折磨的起初5年裏,楊思明一直以爲,自己是神經衰弱,伴隨着失眠、頭痛。直到2003年,快被熬瘋的他到北京掛了專家號,才第一次知道,自己得的病叫抑鬱症。
2005年,楊思明在村裏結婚生子,認了農民的身份。他想把自己當成家裏的頂樑柱,可因時不時看病住院,十畝地依然要靠61歲的父母種。抑鬱嚴重的時候,楊思明覺得自己要被掰成了兩半。“那種痛苦我說不出來,絕望,就是想死。”
無數次,他想到死,他琢磨過在屋後上吊,也常站上自家的屋頂,想跳下去,但又怕死不了反成殘疾,拖累家人。“我真的想死了一萬次。”可上有父母,下有兒女,楊思明說自己剩下的只有一個字——熬。楊思明家房頂上的一把搖椅。他說,看城裏做生意的躺在搖椅上睡得很香,自己總睡不着,於是買了把,想靠它好好睡覺。剛開始可以,但很快就也不管用了。
抑鬱症患者,敏感、多疑、愛鑽牛角尖,有着和其他疾病一樣完整的生化過程,最大特點就是不能如正常人一樣生活,有自殺傾向。據北京安定醫院精神科主任醫師姜濤介紹:對於抑鬱症,多數人的認識還非常膚淺。目前全國有超過9000萬人患抑鬱症或有抑鬱傾向。目前全國地市級以上醫院對抑鬱症的識別率不到20%,換言之,即80%的患者被誤診或漏診,在現有的抑鬱症患者中,只有不到3%的人接受了相關藥物治療。
楊思明的妻子掩面落淚,這麼多年她也沒搞清楚丈夫的病,她是結婚後才知道他有病。她只想好好過日子。村裏比誰家房子蓋得高,她就借了13萬元蓋起了新房和3米高的大門。她想,蓋起新房,丈夫的病也許就好了。結果,房子蓋起了,楊思明的病還沒好。她又想,生個兒子就好了。現在,兒子出生快2年了,病還沒好。
在長達8年時間裏,楊思明每天服用大量的氯硝西泮片。這種藥有鎮靜催眠的作用,長期服用會產生依賴性,但他起初並不知曉,直到2012年才被運城市中心醫院告知不該大劑量服用,可他已經戒不掉了。在生活重擔下,楊思明每月仍需花600-700的藥錢,去太原看一次病就花去了7000多塊。他想做心理諮詢,運城一小時500元的價格讓他只做了一次就再不延續。而同類的諮詢,北京私人專家一小時300-400元,安定醫院醫保範圍內20分鐘只需20元。
楊思明坐在自家的蔬菜大棚上發呆。他最羨慕的是別人能順暢打牌,這是村裏最常見的消遣方式。得病後,他明顯感覺到思維遲鈍,村裏人叫他鬥地主、打麻將,他不敢去。有時他強迫自己坐到了牌桌上,可是一手頂好的牌,被他打爛,嘴快的同村人脫口而出:“你腦子被驢踢了吧!”
楊思明習慣把摩托車油加滿,加足馬力,在去運城的柏油馬路上,漫無目的地疾馳。風吹打着頭髮,他有一瞬覺得,所有煩惱都被帶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