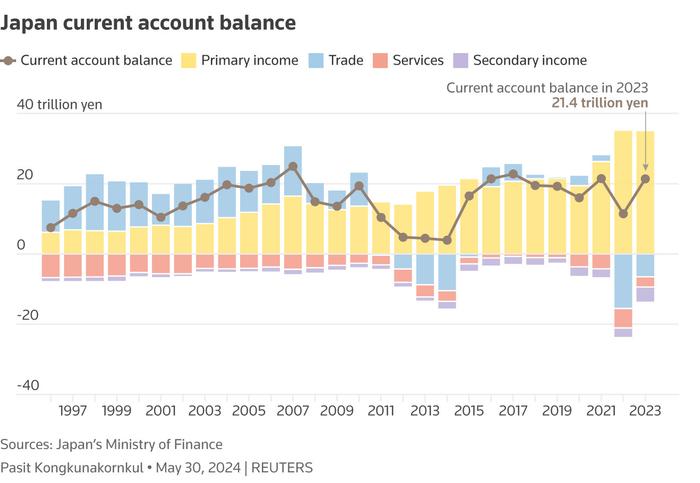緬懷彭小蓮導演·故文推送 | 日本導演小川紳介讓我感悟到的
6月19日,中國著名導演、編劇彭小蓮女士因病去世,享年66歲。這位曾創作出《上海紀事》《美麗上海》等知名影片的優秀導演突然離世讓我們倍感惋惜。2005年7月彭小蓮導演曾在《人民中國》發表文章,談到了她剪輯日本小川紳介導演的《滿山紅柿》的故事,以及她對人生,對中日關係的思考。現在,我們推送這篇故文,以此表達對彭導的懷念。
今年(2005年)的2月7日我在紐約東三街的電影院裏放映《滿山紅柿》,當最後跟觀衆對話的時候,我突然發現這一天正是影片的第一任日本導演小川紳介去世13週年的紀念日。在那個時候,我心裏充滿了一種莊嚴的感覺,對死亡有了新的認識。因爲在那一刻,我發現原來死亡並不可怕,當一個人離開我們後,他留下了比他生命更長遠的東西,而那東西里面還有他的精神和靈魂。我們不僅在銀幕上看見了栩栩如生的小川,我們又一次聽見他急速又敏銳的提問,更加讓我們激動的是,他的思考、他對人生的認識,連同他的電影一起溶入我們的生活,這些都成爲永恆的。世界原來是這麼神奇和豐富,在生和死麪前,小川讓我超越了恐懼。
與小川導演(左一)在一起(左二爲筆者)
《滿山紅柿》是小川在1985年拍攝《古屋敷村》的時候拍下來的,當時他非常喜歡關於村子裏的人手工製作紅柿子的故事;可是放在《古屋敷村》的影片裏卻又顯得那麼不和諧,有點多餘,於是他把這個故事從影片裏面剪掉了。長達十七個小時的膠片就那麼完整地存放在倉庫裏,呆了整整16年。一直到他去世六年以後,他的夫人白石洋子終於籌集到部分資金,於是決定把影片補拍一部分,再做最後的努力,剪接、混錄配上音樂將它完成。花了很多努力,洋子找到了我。
很多人都會問,一個日本人怎麼會找你,一箇中國人,還是一個做故事片的導演來完成小川的作品的呢?當我在日本山形農村偏遠的村子裏補拍和做剪接的時候,教日本電影的美國人馬克也是這麼問我的。他聽完我的故事,他甚至以爲我應該把這個故事,放到電影裏面。但是,我知道這些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完成小川最後的片子。
重新認識日本人和日本的文化
1937年抗日戰爭開始了,我母親朱微明當時是新四軍《前鋒報》的總編,因爲漢奸的出賣被日本人抓去,在囚車上,他們就開始鞭打母親,然後將她關在男犯人的牢獄裏,她獨自躺在溼膩膩的泥土上。更恐怖的是,夜晚日本兵試圖調戲母親,她嘶喊着,那絕望的呼喊把她的形象撕裂得支離破碎。所有的男犯人隔着監獄的鐵柵欄,集體喊道:“不許日本人調戲婦女!”、“日本人滾出中國去!”日本兵在驚恐中逃跑了。在鞭打和受盡凌辱後,新四軍終於幫助母親逃出了監獄。
母親朱微明解放初期照片
父親彭柏山,當皖南事變發生的時候,在傳達新四軍的重要決定的時候,因爲叛徒的出賣,和警衛員一起被日本人抓去關進了憲兵隊……同樣在受盡折磨以後,在搬運軍火的途中,從那裏逃跑出來。幾十年以後,他的身上一直殘留着日本人鞭打的傷痕;母親由此患上了嚴重的關節炎。
對於日本人的仇恨,就這樣和着父母的命運一起延續下來,流入我的血液。直到有一天,我在小川的工作室對他敘說着這些往事的時候,小川低着頭默默地聽着我的敘述,他沉默了很久很久。我不知道小川會是怎麼想的,在那片沉默中我感到一份驚恐,有一種不可名狀的緊張在我們中間蔓延着……持續了有那麼一會兒,小川突然抬頭跟我說:“我們日本人對你們中國人是有罪的!”他說的是“我們日本人”,他說了“我們”。是的,他把自己也放進去了。他把日本軍國主義犯下的滔天罪行加在自己的身上,他爲這段黑暗的歷史背起沉重的負罪感。
這時候我才意識到,日本人是和日本的政府,日本的軍國主義是必須要分開來認識。更多的日本人是正直的,有良心的。他們在自己國家醜惡的歷史面前表現出了正義。是花了很久很久的努力,我也在努力,努力去理解日本人,去仇恨日本的軍國主義。特別是今天當我看見日本某些人又在那裏纂改歷史教科書,否認對中國的侵略行爲所犯下的罪惡,當我心裏充滿着仇恨的時候,我還是知道,在我心裏的那個角落,在我心的深處,小川依然是我深深熱愛的一個日本人,一個偉大的日本人,他不僅爲日本留下了偉大的文化,他也給世界留下了一筆豐富的財產。
散發着小川導演生命氣息的電影膠片
記得在山形的小村子裏剪片的時候,外面開始下雪,屋子裏沒有暖氣,也沒有熱水。洋子特意爲我買了一個暖風機,白天的時候就把它放在剪接室的門口,對着小屋不停地吹着。但是,我似乎從母親身上帶來了先天性關節炎,到了這麼寒冷的冬天,即使穿着大棉褲,關節炎還是發作了。膝關節疼得不能彎曲,常常是坐下來就很難站立起來,我似乎都能聽見骨頭與骨頭之間發出的摩擦聲。那時候,我不知道日子是怎麼渡過來的。早晨起來,還沒有明白一天將會如何開始的時候,我已經坐在剪接臺前了。小川當年的副導演見角先生,他把所有的準備工作都做好了,我只需要將小川拍過的膠片放到轉盤上,擰動了開關就可以工作了。時間,突然就在那個瞬間消失,一切都不存在於我的意識和記憶中,來來回回地看着小川拍攝的東西,我體驗到一種難以表達的快樂,那種着迷和享受我至今回想起來依然會激動。我似乎感覺到小川的存在,我從流暢的電影語言裏面感覺到小川的生命,他對人、對情感以及對村子的熱愛。一點一點漸變的燈光裏,讓人讀到日本文化的一種人文氣質,還有村間柴草的香味。
小川拍得那麼完美,以至於我不知道從那裏下刀子,我總覺得他拍的所有的素材都可以用上去。但是,電影還是受限制的,我必須來來回回地在機器上回放,審視着,希望找到最準確的下刀的地方。出門來山形的時候,我的攝影師林良忠就跟我再三關照着:“一定要好好剪,不然人家會說,這麼好的一部電影就讓一箇中國女導演給糟蹋了!”每每想到這些,我都感到一份恐慌和懼怕。
在小川導演墓前致哀
《滿山紅柿》留給我的寶貴財富
2002年初的時候,影片在柏林電影節放映的時候,五六百人的劇場坐滿了觀衆,當最後響起熱烈的掌聲的時候,我對自己說,我可以向小川交作業了,我完成了他的作品,我無愧於自己的名字作爲第二期導演出現在字幕上。
2005年2月,在紐約東三街的電影放映結束後,我坐在Stella教授的辦公室裏,我在回答她的提問。我不停地說着小川,我突然發現,完成了小川的《滿山紅柿》以後,我拍的電影《假裝沒感覺》《美麗上海》突然沉靜下來,在捕抓細節的時候有了點靈氣,不再那麼愣頭愣腦。似乎對人物的刻劃上我也多了一份含混。我漸淅地看明白了一件很簡單的事情,人的悲觀並不是由於發現了惡,而是由於發現了含混。懷疑之窮追不捨,宇宙諱莫如深,把人引向悲觀的最後一個層次。它比痛苦更甚,那就是開始了恐怖。
但是,小川在自己一生的追求中,在他同樣充滿了茫然和困苦地尋求裏,他在作品裏爲我們留下了希望,留下了一份真誠。他說:“拍電影是來描寫人的心靈。想在描寫心靈的同時,和活在同時代的人們共同分享勇氣,分享活下去的幸福,分享光明,分享和苦難鬥爭的勇氣。再進一步講,要把這些都真實地告訴我們下代的孩子們。”
文:彭小蓮(《人民中國》2005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