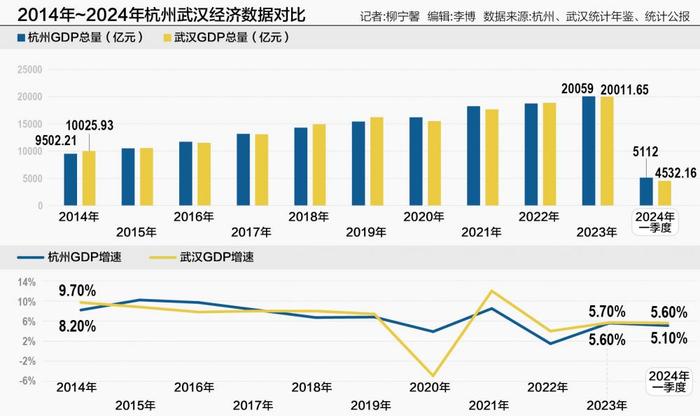徘徊在武漢將軍一路的那個“殘障人士”
//
武漢東西湖區將軍一路,雷和平在這裏工作了七年。其實,在介紹他前理應加上“叔叔”二字。
1983,是武漢各大工廠“喫大鍋飯”體制被推翻的一年。雷叔在尋覓承包對外合作午餐裏奔波往返,高強度的勞作使他的腳部患下了四級殘疾。
即便走路沒有了重心平衡,如今61歲的他仍堅持開着一家飯館爲一大家子奔波生計。
將軍一路的景象,和被人熟知的武漢主城區存在着直觀的視覺差異。八百工棚和工業園幾乎包攬了周邊的工作單位,來往工地的工人和低矮破舊的居民樓對年輕人吸引有限。當然,其中也不乏一些殘疾人。
往返的殘疾人拖着小車,在被大型泥土車壓出坑坑窪窪的路面緩步移動,但凡遇到雨天,對他們更是雪上加霜。行動不便、飽受歧視、貧困潦倒而沒有一技之長,當然殘疾人的標籤遠遠不止這些。
可這羣人每天必須往返於此,這是他們工作的必經之路。
這一切,雷叔看在了眼裏。面對現實拋給他們接二連三的黑色幽默,有人猶豫不決,有人默認嘆息,而感同身受的雷叔決定以贈免費午餐的方式試圖緩解他們的清貧。
雷叔算是一個地道武漢人,性情耿直爲人正義,早些年就開始從事餐飲相關的工作。因爲熱愛烹飪燒魚,做的一手好菜被身邊鄰坊熟知。
行善對於雷叔更像是一種生活習慣,這家人的熱心腸也早已在周邊出名。
飯店裏的員工,除了雷叔的妻子其餘都是同個工廠共事的夥伴。
工廠倒閉後,有些年事已高或同樣殘疾的夥伴,沒有地方可以繼續工作,雷叔就把他們都招來了自己的飯店打下手。
“因爲自己本身是殘疾人,所以懂得作爲殘疾人的異常艱辛和不被理解。如今發展的這麼快,武漢這麼多家餐館如果都能一起做這件事,那更多的殘疾人就能喫到免費午飯了。這件事對一家餐館是件小事,對那些殘疾人來說卻異常珍貴。”
有些人會偏執以爲,他們無非就是想獲取一份午餐的免費饋贈。其實不然,除了一頓飯,他們更需要大衆與之相對的善意和包容。
當雷叔將免費贈與午餐計劃告訴家人夥伴的時候,得到了一通讚許和支持,也讓雷叔的決心愈加強大。今年五一當天,雷叔在大門窗上張貼贈送殘疾人免費午餐的紅色告示。街坊路人以十傳百,至今已送出超過1000份愛心午餐。
雷叔和很多身患殘疾的人一樣,經歷過一段自我抗爭。
一個人不管多樂觀,多堅強,如果遇到否定自己的環境,都會經歷挫傷。在乍明乍滅鄙夷充斥的日子裏,他曾一度灰心沮喪。但他發現一味自我沉淪毫無用處,反而拖累家人。
自打開店後,雷叔每天清晨天未亮就奔波菜場選材買料,上午在店打掃歸置,一到中午就灰溜溜的躲進了後臺廚房,手把手教導廚師燒魚炒菜傳授祕訣。遇到生意忙的時候,他就出來幫夥伴一起打下手,收拾衛生。
不論何處,每每遇到有人注意他行動不便,將目光轉移到腳上,他都不自然的縮了縮腿。外界越是鄙夷,雷叔做事越是麻利高效——這是從一個極端到另一個極端的延伸。
經過選購、運輸、醃製、配料、燒製,他家館子的招牌燒魚肥美白嫩,湯汁入味鮮香。此外的家常菜和海鮮更是不在話下的甜鮮下飯,還原了菜品原本的味道。真正家常菜館幾乎不上大衆點評,不擺架子也不端着。它是老闆展示廚藝的後方舞臺,味道究竟如何,一喫便知。
當飯店如火如荼的順利經營着,這顯然不是雷叔所有的生活重心。腿腳健全與否,並不能決定他的夢想歸依。他開始做了慈善愛心午餐的事業,正如眼前的狀態而言,非常不錯的進展。未來他還希望可以讓更多的店主加入其中,成立殘疾人基金會,幫助到更多殘疾人。
正視自我,勇敢上路,雷叔花了差不多十年的時間,他也在學會接受自己的能與不能。
這個世上就沒有“正常人”一說,每個生活在社會的人都有可能是殘障人。每個人都會變老、視力變弱、身體變差。
從“殘廢”,到“殘疾”,再到“殘障人士”,公衆的措辭在進步,以人們更爲接受的方式延展。但不得不說,至今仍有媒體和輿論,會使用“正常人”、“殘廢人”等詞語來區別看待。
或許是自身經歷了太多,或許是對於殘疾人現狀看過了太多,提到對殘疾人的看待,雷叔一時不知道該怎麼陳述道來。在他心裏,有些畫面始終都讓他揪心不已,難以忘懷。
前些天,張師傅聽說鄰居說“有個雷老闆送免費午餐”,於是來這裏準備領飯。他試探性的在門口問了問這件事是真的嗎。確認過後,拿出殘疾證,雷叔瞥了一眼,二話沒說進店把飯打包好拿給了他。
在遞給他的瞬間,張師傅低了低頭,卡在嘴邊的感謝沒能脫口而出。雷叔安慰他,“沒事的,不夠喫了再來我這裏拿。我自己也是一個殘疾人,不用不好意思。”
後來得知,因爲張師傅夫妻倆都是殘疾,勒緊褲腰帶供兒讀書,家裏全部的經濟來源主要靠低保和撿破爛爲生。如今物價上漲,節省這樣日常的三菜一湯的價錢,對他們來說無疑是一筆不小的開銷。
張師傅對我說,以後等他生活過的好點了,也希望有能力和雷叔一起幫助更多需要幫助的人。自從愛心午餐開始,生活工作在將軍一路附近的殘疾人都知道了這裏有家愛心飯店,裏面有個“活菩薩”老闆。
八月的武漢,炙熱難耐。樸素勤儉的雷叔,把這樣一份三菜一湯裝點成盒,無償獻給了這些“殘障人士”。
“殘障羣體”在報道的視角下,極端悲慘和極端聖潔成了鮮明兩派,這是任何媒體都無法全方位的報道與敘述他們原本立體式的人格形象。
或多或少,他們都會帶有自我防禦的盔甲。這不歸咎於他們,是環境造就他們的條件本能,我們需要做的是儘可能的閉嘴與尊重。
在我們即將結束採訪之際,門外仍有不少殘障人等候領取午餐。他們或許此生終將面臨新老交替的各式問題,但他們依舊選擇正視自己,先把肚子填飽,再面對接下來的生活挑戰。
他們徘徊在將軍一路,有的選擇接受饋贈,此後常懷感恩;有的選擇默默幫助他人,奉獻着剩下的餘生。
//
文=Leo
圖=網絡/雷叔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