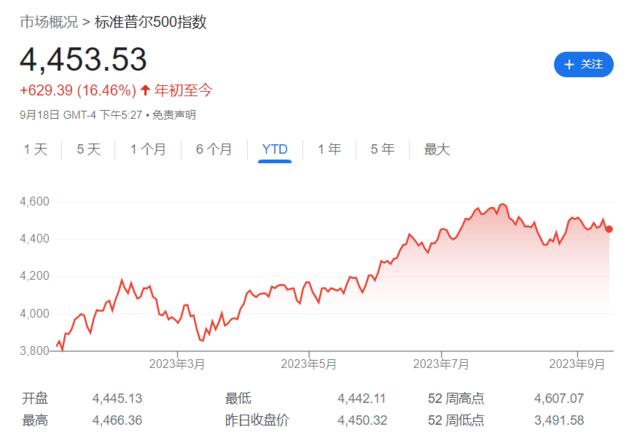古代志怪故事两则(取气袋,见鬼)
摘要:白日见鬼,一般人还真没这个本事,所以,任生究竟能不能看见鬼,谁也不知道。城门之下熙熙攘攘,人来人往,没有任生那样的慧眼,谁又知道哪个是人,哪个是鬼呢。
取气袋
唐宣宗元和年间,光宅坊有一户人家,家里有人得了病。
这人病得很重,缠绵病榻很多天,家里人该想的办法都想了,就是不见好转。
一个大活人有出气没进气,眼看着就要不行了。
事到如今,也只好听天由命了。
病人弥留之际,家人为了他死后能够脱离三途六道,直升天堂。特地请来一群僧众,在床前念经、做道场。
妻子儿女环绕在他身边,压抑着嗓子低低的哭泣。
病人就剩下一口气了,却挺了好几天。
这也真是异数,谁都以为他一两日便去了,却还是无知无觉地活着。
一天晚上,众人正在病人的屋子里低声说话,忽然看见一个不速之客从外面走了进来。
这人他们从来也没见过,不是邻居,不是亲戚朋友,也不是家里请来的大夫。就这么直接往屋子里闯,实在是太没规矩了。
家里的男丁上去追赶,那人对他们好像十分忌惮,围着病床跑了几圈之后,慌不择路,窜到厨房里,四顾之后,一个鹞子翻身,竟然投身于厨房角落的一个大瓮之中。
这人行迹鬼祟,又逃得飞快,着实可疑。
家里人正好看见这人一掠而过的身影,赶到灶间,舀起锅里沸腾的热水,就朝瓮里倒去。
没有听到意料之中的惨叫!
瓮中的水倒满之后,一个怪异的袋子从里面浮了上来。
家里人拿着这个袋子,左看右看,正在狐疑之际,就听见空中有人哀求:
“实不相瞒,这是阴间的取气袋。你家长辈阳寿已尽,阴司命我前来取他的性命,没想到却为众位所阻,求求你们,把取气袋还给我吧!”那人声音非常焦急,又很哀切,看来取气袋对他来说是很重要的东西。
“还给你,我家长辈岂不是死定了!”
“不行不行!”
众人七嘴八舌地道。
争执了半天,见自己的东西无望取回,空中那个声音只得道:
“这样吧,你们把袋子给我,我找别的病人来代替!”
家人听了,心中暗喜,运足力气,把袋子投掷过去。
袋子飘飘悠悠地消失在空中。
回到屋子里,他们惊奇地发现,病人已经睁开了眼睛。
这个取气袋真是个神奇的东西啊,那么,它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呢,且听下回分解。
宣宗元和末年,淮西有位军将,受了上司的派遣到汴州出使。
晚上在驿站休息。夜深了,好几天在路上奔波劳累,他很是疲惫,沾到枕头,便熟睡过去。
半夜时分,忽然觉得胸口沉甸甸的,压得自己喘不过去来。
好像有什么东西压在自己身上似的。
军将从睡梦中惊醒。
他是武人,日日操练,身体也十分健壮。醒来之后,便死死地抱住那压住自己的东西,与其角力。
那东西不是他的对手,踉跄着逃走了。
慌乱之中,手里拿着的革囊叫军将夺了去。
周围一团漆黑,军将站起身来,想点燃灯盏,看看究竟是什么东西夜晚来犯。
正在此时,只听耳边传来一阵哀求之声。那偷袭自己的东西请求军将把革囊还给他。
军将想了想,对他说:
“你告诉我这东西究竟叫什么东西,我就还给你!”
室内沉寂良久,先前那个声音无奈,只得道:
“这是蓄气袋!”
军将听了以后,嘿嘿一笑,猛然暴起,摸起床头的瓦片,朝声音传来的方向砍去。
只听丝丝一阵怪响,再侧耳细听时,屋子里已经恢复了宁静。
军将从怀里掏出火镰,点着了灯盏。
革囊仍在,看上去能盛装好几升米,是绛色的。细看起来又不大象皮革,丝丝缕缕的,有藕丝一般的东西连缀其间……
第二天,军将把这个袋子拿到太阳底下,看看会有什么反应。他发现,在日光之下,那袋子竟然没有影子。
故事讲完了。
蓄气袋,是取生人活气的。气息尽,人便亡。
前后两个取人性命的鬼卒,是同一个吗?笨得真够可以,两次遭人暗算。
看来阴间也得大力抓抓岗前培训了!
见鬼
吴郡有个姓任的书生,乍看上去,同别的书生没有什么两样,身材瘦削,头戴儒冠,手捧书卷,钻研得极为忘我。
只有一点,他这个书生同别的书生很是不同:任生对同龄人孜孜以求的功名利禄从来就没当做一回事,反而对那些和尚道士擅长的飞符做法,驱鬼役神之类津津乐道。
当然,他钻研的那些书也绝不是什么四书五经,而是巫婆神汉当做宝贝的奇门遁甲之术。
据说任生的道行还挺高,而且,青天白日之下,就能看见鬼!
白日见鬼,一般人还真没这个本事,所以,任生究竟能不能看见鬼,谁也不知道。
任生住在洞庭山深处,那里白云悠悠,峰峦叠嶂,罕有人迹,是个绝佳的隐居之所。
他在那里居住了很多年,谁也不知道他究竟有多少岁了,奇怪的是,进山的人发现,不管什么时候看见他,任生的面貌,总是如同孩童一般,清朗红润,一点都没有改变。
唐敬宗宝历年间,前昆山县尉杨氏有个儿子,侨居在吴郡。杨氏子是个闲不住的人,有一天,他约了几个朋友,一起荡着小船,前往虎丘寺游览。
巧的是,当时任生也在船上。这些人都听说过任生的名头,言谈之间就不免提到了鬼神之事。
杨生道:
“常言道:人鬼殊途。所以,鬼终究是无法看到的。那些号称能够看见鬼的人,不是欺骗自己,就是欺骗别人罢了!”
任生听了这话,也不恼怒,只淡淡道:
“鬼有很多,只是常人无法分辨而已,不过,我却能够做到。”
船上众人的目光都向任生投来,任生的表情仍然如流水一样闲散,他回过头看,看了看岸边。众人的视线被他牵引,也朝岸上看去。
有一个青衣妇人,怀中抱着小孩,正在岸边款款而行。
那女子相貌姣好,神态温柔,正低着头,慈爱地看着怀里的孩子。孩子的头埋在那女子的怀中,一动也不动。
任生指着那个女子说:“这是鬼,她怀里抱着的却不是!”
“那是什么?”
“是婴儿的生魂!”
“大家都是成年人了,不能你说什么我们就信什么吧!你说她是鬼,怎么证明呢?”杨生追问。
“这好办,一会儿我上去同她搭讪,你趁我和那女子说的时机,如此这般……”说着,把嘴凑近杨生的耳边,低低地说了几句话。
杨生狐疑地看了他半晌,最终还是点了点头。
任生整了整衣襟,朗声道:
“夫人看起来有些面熟,您这是往哪儿去啊?”
那女子听到任生的问话,不由自主地停下了脚步。
她刚一回头,就听得耳边一声断喝:
“大胆厉鬼,偷窃生人的孩子意欲何为?”
众人都被这声厉喝吓了一跳,回过头来一看,只见任生双手叉腰,满脸怒气,正在逼问那女子。
那女子显然是叫任生给吓得不轻,脚步踉跄,连连后退,她越退越快,走了有十几步之后,就不见了。
晴天白日的,一个活生生的人就这么凭空消失,不是鬼又是什么!杨生又是惊异,又是赞叹,对任生佩服得五体投地。
这些人在湖上完了一整天,到傍晚时分,才掉头回家。
离城还有几里的时候,忽然看见岸上传来一阵嘈杂的响声。原来是有一户人家正在摆设酒宴,招待客人。空地上有个女巫,身上披挂着奇怪的装束,手中持鼓,正甩着脑袋,疯狂地舞动。一看这架势,大伙儿就明白了,这家正在祭神。
等那女巫满头大汗地停下来以后,杨生与任生不约而同地问她:
“这家为什么要祭神呢?难道是发生了什么事吗?”
女巫擦了擦头上的汗水,道:
“今天这户人家有个孩子突然暴亡,现在又醒过来了,所以家人摆设酒宴,感谢上天的恩赐。”
“要说这孩子也真是福大命大,我现在就让人把他抱出来,给二位看看。”
不一会儿,家中女眷抱着一个小孩,从临时搭建的帐篷里走了出来。
杨生一看,不由得大吃一惊。
眼前那嬉皮嫩肉,呀呀学语的孩子,正是先前河岸上那个青衣妇人怀中抱着的那个。
孩子的生魂为鬼所摄,所以才会暴亡。
而任生无意之中竟然救了那孩子一命。
事到如今,与任生同行的人才完全慑服。众人慨叹道:
“先生果然是有道术的人,我等有眼不识泰山啊!”
“岂敢岂敢。”任生谦逊地道。
众人在城门前面分了手。
城门之下熙熙攘攘,人来人往,没有任生那样的慧眼,谁又知道哪个是人,哪个是鬼呢?
原文:吴郡任生者,善视者,庐於洞庭山。貌常若童儿,吴楚之俗,莫能究其甲子。宝历中,有前昆山尉杨氏子,侨居吴郡。常一日,里中三数辈,相与泛舟,俱游虎丘寺。时任生在舟中,且语及鬼神事。杨生曰:“人鬼殊迹,故鬼卒不可见矣。”任生笑曰:“鬼甚多,人不能识耳,我独识之。”然顾一妇人,衣青衣,拥竖儿,步於岸。生指语曰:“此鬼也。其拥者乃婴儿之(“之”原作“也”,据明抄本改)生魂耳。”杨曰:“然则何以辨其鬼耶?”生曰:“君第观我与语。”即厉声呼曰:“尔鬼也,窃生人之子乎?”其妇人闻而惊慑,遂疾回去,步未十数,遽亡见矣。杨生且叹且异。及晚还,岸傍一家,陈宴席,有女巫,鼓舞於其左,乃醮神也。杨生与任生俱问之,巫曰:“今日里中人有婴儿暴卒,今则寤矣,故设宴以谢。”遂命出婴儿以视,则真妇人所拥者。诸客惊叹之,谢任生曰:“先生真道术者,吾不得而知也。(出《宣室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