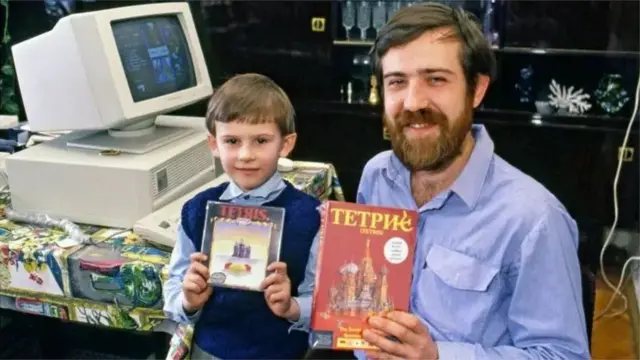全球化、中產夢與地名的空間政治:我們爲什麼在意“洋地名”?
摘要:倫敦政經學院學者David J. Madden在《從地圖中驅離:紐約城的地名學和地方政治》(Pushed Off the Map: Toponymy and the Politics of Place in New York City)一文中指出,地名往往指向的是人羣的歸屬區隔,它們劃分社會界限,創造某種集體政治身份,“通過命名,城市居民、地產行業和各色國家機構根據自己的利益和計劃塑造城市空間,將某一地區的過去和未來進行敘述合法化,並使其他不符合己方要求的敘述版本失去效力。這是因爲,如同改革開放時代引進的衆多舶來品一樣,洋地名象徵着中國人以前不曾有過的、以歐美髮達國家爲藍本的現代生活方式——這是在中國進入經濟大跨步發展的時代初期,充裕的物質生活缺乏本土化的話語表達方式,不得不訴諸於西方文化資源的結果。
撰文 | 林子人
編輯 | 朱潔樹
日前,海南、陝西、河北、廣東、浙江等地開展的清理整治不規範地名工作,因一家被海南省民政廳列入“整治不規範地名清單”的酒店公開抗議而迅速進入公衆視野。根據《瀟湘晨報》6月18日的消息,海南省民政廳發佈的《關於需清理整治不規範地名清單的公示》中涉及的不規範地名共計84個,包括崇洋媚外、刻意誇大、怪異難懂和重名同音四類,其中海南有15家維也納酒店因“崇洋媚外”而位列其中。20日,澎湃新聞注意到浙江部分城市也在開展不規範地名清理整治工作,台州和溫州都有包含“曼哈頓”的地名,前者被改爲“太陽谷小區”,後者被改爲“曼哈屯”。
在一個國家的領土上挪用他國的名稱來創造地名其實並非中國人的首創——很大程度上來說,這是全球人口流動和文化交流的結果。1492年,航海家哥倫布在抵達美洲後第一時間將發現的兩座島嶼命名爲費爾南迪納島和伊莎貝拉島,以向遠航恩主和贊助人、西班牙國王斐迪南及女王伊莎貝拉致敬。在西班牙成長爲一個有能力進行遠航和殖民活動的大國前,伊比利亞半島曾在8世紀到15世紀落入穆斯林的統治範圍,在此期間阿拉伯語深刻影響了西班牙語,西班牙境內原本被穆斯林統治的地區也因而充斥着阿拉伯化的地名,例如阿爾瓦拉辛(阿拉貢地區城市)和安達盧西亞(西班牙最南邊的地區)。
隨着越來越多的舊大陸移民來到美洲,這片土地上亦有越來越多的地點被移民用他們熟悉的稱呼來命名。在美國的各大城市,以某移民羣體的母國命名的地區司空見慣,如“唐人街”“小意大利”“日本城”等等。不過最有代表性,也最讓人驚訝的當屬緬因州:這個位於美國東北角的州有着諸多以海外國家和城市命名的城鎮,那裏有挪威、巴黎、丹麥、羅馬、瑞典、貝爾法斯特,甚至中國。有趣的是,美國作家卡洛琳·丘特(Carolyn Chute)曾寫過一部題爲《緬因州埃及市的豆子》(The Beans of Egypt, Maine)的小說,她特地虛構了“埃及市”這個地方,用來暗示緬因州衆多稀奇古怪的“洋地名”,但小說家自己也沒有想到,緬因州還真的有這麼個地方。
不過當下中國的洋地名和殖民主義或移民沒什麼關係——中國既未曾徹底淪爲過殖民地,也未曾接受過有能力改變當地文化的大量外來移民,新中國成立後,諸通商口岸城市的洋地名也很快被更改了。事實上,中國語言的性質也決定了洋名不可能佔據主流。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裏,中國作爲一個政治、經濟和文化強國在東亞地區具有極強的影響力,中文裏的外來詞數量一直遠遠低於其輸出詞的數量,直至今日,中文都是全球範圍內外來詞含量最少的語言之一。根據德國馬普研究所“全球外來詞數據庫”的數據,在41種主要語言中,中文的外來詞比例是最低的(2%),英語反而是外來詞比例最高的語言之一(42%)。
我們也許需要從另外一個角度來思考當下中國洋地名的成因及其引起的焦慮。洋地名興起的現象可以說是中國市場經濟發展與中產崛起的結果。如同改革開放時代引進的衆多舶來品一樣,洋地名象徵着中國人以前不曾有過的、以歐美髮達國家爲藍本的現代生活方式。這些源自歐美髮達國家的地名被商人利用、包裝爲某種“時髦”“先進”“幸福”的生活範式和文化資本,販賣給追逐與金錢相匹配的地位符號的中產消費者。地名亦是一種空間政治(spatial politics)的表現形式,在不同利益相關方的衝突中形塑着我們對某一具體空間的認知。
格調、檔次與品位:“洋地名”的文化資本
根據日前多個正在進行不規範地名整治工作的城市公示的清單,名稱不規範的地名很大部分屬於樓盤小區、商業廣場等地產項目。也就是說,部分地產開發商刻意在使用“洋地名”向城市(中產)消費者兜售某種理念,在這個過程中,一種新的城市居住和商業空間形式在人們開始享有私有房屋產權和消費自主的時代被創造出來。這個現象背後的重要運作機制,就是人們不斷提高的階級區隔意識。
在《格調》一書中,美國文化批評家保羅·福賽爾(Paul Fussell)指出,區分社會階層的標準不止財富這一項。階層越高的羣體,越傾向於認爲品味、價值觀、生活格調和行爲方式是判斷等級身份不可或缺的標準。某種程度上來說,品味、知識和感知力比金錢更能決定人的社會等級。
福賽爾寫道,對階級區隔非常敏感的美國中產有種濃濃的“古風崇拜”——他們相信,相對於文化淺薄與無歷史積澱的美洲新大陸,英國和歐洲纔是上檔次的、象徵着“老錢”的等級標誌,因此中產喜歡殖民風格或科德角式房屋,認爲打扮成老電影中的“英國紳士”無比體面,熱衷於將孩子送到那些有着哥特式建築風格、洋溢着歷史悠久感的大學。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鑑於英國曾經在19世紀稱霸全球,英國文化風尚被認爲深具內涵和韻味,美國社會因此有種強烈的“英國崇拜”。美國社會學家指出,儘管受訪者總會屢屢聲明他們居住的地區並不存在社會等級差別,但事實恰恰相反。因此,地產開發商爲了吸引中產買家常常刻意採用英式地名:休斯頓的郊區充斥着“令人震驚的英國地名”,比如諾丁漢橡樹莊園、阿富頓橡樹莊園和麥利迪斯莊園。“只要是英國的,就一定有檔次——這種觀念促使一些人更名換姓,只爲聽起來帶有英國味。”福賽爾說。
類似的現象也在中國發生。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人類學教授張鸝在研究中國城市中產房產消費的過程中發現,從21世紀初開始,購房者越來越多地將購房決策和文化品位、居住理念聯繫起來,並以此實踐階級區隔。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開發商窮盡手段提升商品房的交換價值,這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鮮明的文化形象和居住理念的打造上,“今天,賣房子極大地取決於將鮮明的文化概念包裝成產品、將地產價值和生活方式聯繫起來的能力。”
在家鄉昆明,張鸝發現地產推銷最常使用的一個詞是“現代”,很多情況下這個詞等同於“洋氣”,這兩個詞之間的密切關聯暗示着“現代”從根本上來說是一種來自外國(特別是西方)的影響:“在當下,現代生活的願景通過出售號稱採用原汁原味的外國建築樣式的房產實現,它允諾了一種帶有異域風情的、現代風味的光環。”
在張鸝進行田野調查的21世紀頭一個十年裏,有着“現代”意味的建築範式通常來自北美和西歐。張鸝發現,昆明當地的地產商雖然極少具有實力聘請外國建築師來設計出原汁原味的西式建築——事實上很多地產項目至多是在當地人眼裏有西方風味而非具備某種特定的西式風格——但地產商會以取洋地名的方式來創造某種外國氣息,並在廣告宣傳中大量使用白人模特和外國居住環境的圖像來加強“洋氣”的聯想。
除了“創意英國”“挪威森林”“波西米亞花園”“馬可波羅半島”“格林威治”這樣直接挪用外國地名或人名的名稱外,一些地產項目甚至只是在名稱中融入英文來指涉現代、打破常規和國際化,比如“BOBO自由”“GOGO新時代”。她注意到,昆明超過1/3的新建地產項目(特別是高端地產項目)取了一個“洋氣”的名字。
西南地區城市尚且如此,對外開放程度更高的一線城市更不用說。張鸝表示,洋地名在中國城市層出不窮地出現,這一現象在北京和上海這兩座有志於進入全球一流城市序列的城市尤爲突出。“澎湃新聞·市政廳”刊發的《“洋化樓盤”的資本邏輯:高房價和炫耀性消費》一文指出,2000年以來,北京有近3200個新建樓盤,根據名稱和建築風格可辨別出的洋化樓盤有540個,約爲全部新建樓盤的1/6。不少洋化樓盤甚至做到了完全照搬歐美社區的程度,例如京郊有一個以美國懷俄明州傑克遜霍爾社區爲原型的小區,採用美國西部風格設計,安保人員身穿牛仔服,營造原汁原味的美國西部風情。
洋地名或洋化樓盤的大量出現很大程度上源自在中國人認知中,西方與富庶、地位之間的密切關聯。西方——或者更籠統而言外國——生活方式象徵着成功、尊重和較高的社會地位,這或多或少在影響城市中產的購房決策。對於地產開發商來說,採用洋地名或洋化樓盤的策略是爲了迎合消費者的這種潛在心理,向城市新貴們兜售一種優質生活和國際化都市風格的美好願景。正如張鸝所言:
“將西方現代風格移植到中國居住空間,這背後有兩股力量。第一股是商業力量,這主要體現在地產開發商增加利潤的意圖上。第二股力量是將現代美好生活和西方聯繫在一起的流行心態……當這兩股力量合流,就爲挪用西式空間形態和西式生活方式這種做法的興旺提供了理想的土壤。”
中產夢與國家管制:“洋地名”爭議中的空間政治
一方面,開發商通過西式建築設計和洋地名來吸引中產消費者,另一方面,這種做法也引起了民族主義情緒的反彈。在此輪整治不規範地名工作之前,這種衝突就屢屢發生。2005年,人民網“強國論壇”上出現了一篇帖子,作者激烈批評了昆明流行取洋地名的做法,引起了強烈反響。昆明市政府迅速反應,出臺政策禁止當時正在施工的和未來的地產項目取洋地名。
事實上,國家干預洋地名的做法早已有之。根據媒體人李銀的梳理,民政部在1996年頒佈的《地名管理條例實施細則》中明確規定“不以外國人名、地名命名我國地名”。同年11月1日,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也下發了關於規範企業名稱和商標、廣告用字的通知。在那之後,全國各地就陸續有地方在修正地名,新聞報道中能追溯到的最早的案例是在2003年的石家莊。
地產開放商頻頻使用洋地名吸引消費者,政府頻頻開展行動整治這一行爲,這之中反映的衝突告訴我們,地名實際上也是空間政治的一種表現形式——地名不僅僅只是某一業已存在的地理空間的膚淺修飾,而是一項各方利益衝突下爭議不斷的空間實踐。倫敦政經學院學者David J. Madden在《從地圖中驅離:紐約城的地名學和地方政治》(Pushed Off the Map: Toponymy and the Politics of Place in New York City)一文中指出,地名往往指向的是人羣的歸屬區隔,它們劃分社會界限,創造某種集體政治身份,“通過命名,城市居民、地產行業和各色國家機構根據自己的利益和計劃塑造城市空間,將某一地區的過去和未來進行敘述合法化,並使其他不符合己方要求的敘述版本失去效力。”
在意識到城市地名的“政治性”後,我們就能理解洋地名背後折射出的衝突與焦慮究竟源於何處。身爲城市商品化的重要推手,地產資本積極通過命名來打造品牌、營銷城市空間。地名實際上是一種飽含象徵意義的文化資本,它背後關於聲望和階級區隔的暗喻不聲不響地篩選、擊中有經濟實力且對身份地位敏感的潛在消費者,對於後者而言,房產消費絕不僅僅只是爲了有一處能遮風避雨的家,房產連帶的文化資本同樣重要。
我們可以說,洋地名的泛濫和中國人的中產夢有着脫不開的關係,而這個夢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消費的基礎之上。財經作家孫驍驥在《購物兇猛》一書中指出,市場經濟構建出物質充裕、選擇自由的商品社會後,中國人嚐到了甜頭,將國家更美好的未來和個人更高的生活品質聯繫起來,把理想中的國家藍圖想象爲“更多的自由和消費選擇”。商品社會中的商品被賦予越來越多的符號意義,用以證明購買者與他人之間的差異。當經濟快速發展帶來城市新中產的崛起時,商品社會的這一機制就顯得尤爲重要——通過購買商品(及其符號),城市新中產在身份認同缺乏量化指標的混沌中找到了一條確定無疑的路徑,即通過消費獲得身份確認、階級認可和自我價值的實現。
在很長一段時間裏,許多中產消費者熱衷於購買那些有着洋地名及/或外國建築風格的樓盤小區。這是因爲,如同改革開放時代引進的衆多舶來品一樣,洋地名象徵着中國人以前不曾有過的、以歐美髮達國家爲藍本的現代生活方式——這是在中國進入經濟大跨步發展的時代初期,充裕的物質生活缺乏本土化的話語表達方式,不得不訴諸於西方文化資源的結果。這些源自歐美髮達國家的地名被商人利用、包裝爲某種“時髦”“先進”“幸福”的生活範式和文化資本,販賣給追逐與金錢相匹配的地位符號的中產消費者。
對於國家來說,地名同樣具有深意。Madden指出,國家機構通過地名來劃定行政邊界、彰顯政治權威、定義空間問題、合法化政治主體、闡釋領土政策。因此我們可以說,地名的更改實際上也是國家權力的一種表現形式,正如法國社會學家皮埃爾·布爾迪厄所言,爲地方命名是擁有“合法象徵性暴力壟斷”(monopoly of legitimate symbolic violence)的國家機構進行權利聲張的一種形式,命名權之爭實際上就是“社會世界的合法圖景”(the legitimate vision of the social world) 之爭。
國家對洋地名的焦慮,實質上是對附着其上的象徵性符號的焦慮。它打破了以國家爲主體的意義壟斷,將“外國的”定義爲“更好的”“值得追求的”,損害了國家尊嚴。在“洋地名是崇洋媚外”的指控之外,一個更隱祕的緣由或許是這種象徵意義上的空間階級區隔化還涉及到一個根本性的合法性基礎,即社會主義國家允諾的平等。
隨着中國國力的上升,人們對西洋舶來品的無端崇拜或將漸漸消退,取洋地名、採用西方建築風格的地產項目或將從洶湧熱潮退燒爲一個時代特色,但隱藏在消費行爲背後的客觀人性並不會輕易更改。地名的意義或許將隨着時代發展而變化,但它將一直作爲城市空間意義複雜性的有趣註腳,出現在公共討論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