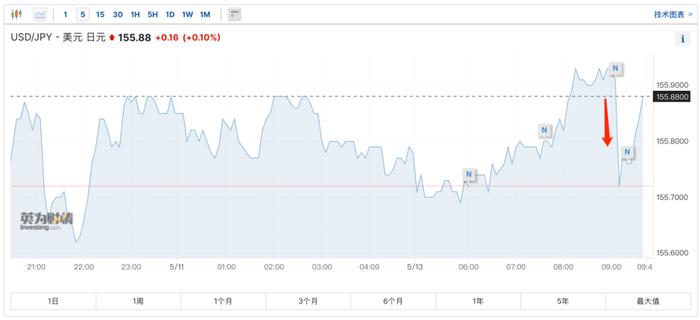「读+访谈」曹文轩:只有快乐,算得上是健康成长吗
摘要:6月16日,在湖北省新华书店·泛海书城举行了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儿童文学作家曹文轩的新书《草鞋湾》读者见面会,这位很受家长、老师、中小学生欢迎,但也有争议的作家接受了读+专访,谈了中小学生语文教育、中国儿童文学现状等问题,也回应了那些批评。记者注意到一个细节,曹文轩引述的一个观点来自写了《洛丽塔》的纳博科夫,他特意隐去纳博科夫的名字,只是说:“这个观点是一个大作家的,他的作品不是写给你们看的。
长江日报记者李煦
6月16日,在湖北省新华书店·泛海书城举行了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儿童文学作家曹文轩的新书《草鞋湾》读者见面会,这位很受家长、老师、中小学生欢迎,但也有争议的作家接受了读+专访,谈了中小学生语文教育、中国儿童文学现状等问题,也回应了那些批评。
荣誉与争议
曹文轩,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学术性著作有《中国八十年代文学现象研究》《第二世界——对文学艺术的哲学解释》《二十世纪末中国文学现象研究》《小说门》等;著有长篇小说《草房子》《青铜葵花》《红瓦》《根鸟》《细米》《山羊不吃天堂草》《火印》《蜻蜓眼》以及“大王书”系列、“我的儿子皮卡”系列、“丁丁当当”系列等,创作并出版图画书五十余种;《草房子》印刷超过500次,印量超过2000万册。《草房子》《青铜葵花》《红瓦》等被译为七十余种文字。
曾获金鸡奖最佳编剧奖、中国电影华表奖、德黑兰国际电影节“金蝴蝶”奖等重要奖项六十余种。2016年获得国际安徒生奖,是中国第一位获此殊荣的作家。
曹文轩荣誉很多,也很受家长、老师、中小学生欢迎,但是围绕他的争议也不少。在网上一搜就能看到诸如《我们只想真诚地谈谈曹文轩这书怎么不好》《为什么我不希望我的孩子读曹文轩?》《曹文轩儿童文学中的“性别观”落后国际社会多少年?》等文章。
“我那时就是个找打的孩子”
“我想问曹教授,你说《草房子》里的桑桑就是您自己,为什么您要把自己写得那么找打?”
这个小男孩的提问让在场几百个孩子都笑了,曹文轩自己也笑了。
这是曹文轩新书读者见面会上发生的一幕。
《草鞋湾》是曹文轩首本侦探小说,以侦探故事的外壳讲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和抉择。在这场见面会上,曹文轩并没有怎么大张旗鼓宣传新书,只说《草鞋湾》源起于毛姆的一部作品,里面有一句话:一位私家侦探出门侦探时总要带上他的小儿子,因为没有人给他带孩子。这句话在曹文轩脑海里存了很多年,然后在今年春节时他构思成熟,用20多天写出了小说。
曹文轩倒是花了不少时间引导孩子们写作文,他为此讲了4个故事,引申出不同的诀窍和技巧。
这几个故事他在不同的地方讲过多次,对于节奏的把控和要点的强调已经非常纯熟;这次他还是讲得不疾不徐,花了不少时间。记者注意到一个细节,曹文轩引述的一个观点来自写了《洛丽塔》的纳博科夫,他特意隐去纳博科夫的名字,只是说:“这个观点是一个大作家的,他的作品不是写给你们看的。”
在后面的互动环节,他回答了六七个问题,泛海书城工作人员说:“他给读者的时间比网红作者要多。”
在互动环节的尾声出现了那个“找打”的问题,曹文轩笑过之后给了回答。他的大致意思有这么几层:“我那时就是个找打的孩子”;当时的观念是“大人打你是为你好”;他没有因为挨打记恨爸爸妈妈,相反地他还想过“如果他们从不打我,我现在会是怎样”;他现在不赞成体罚,但也不赞成“父母一指头都不能弹在孩子身上”。
【访谈】儿童文学和成人文学本质上没有差异,都是文学
鲁迅肯定要读
读+:刚才的见面会上您已经讲了作文的重要性和技巧,也讲了鲁迅对自己一生的影响。据说中学语文学习有“三怕”:一怕文言文,二怕写作文,三怕周树人。您作为语文教材主编之一,怎么看这个说法?
曹文轩:有些说法不一定是太普遍的现象或事实;然后,就算是“怕”,也不等于说“怕”的东西我们就放弃,也不等于说它就不会来。
说到文言文,它对一个人语文知识、能力、素养的培养是绝对不可以省略的。拿文学来说,我们当代文学在很多方面都超过了现代文学,比如主题的开阔、人性的把握、题材的拓展;但是在语言方面,我们没有超过那一代作家。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现代文学作家是被文言养大的,文言给了他们一种语言的气质,他们的“语言质地”比较好,对于文言的凝练、雅致和境界,他们心领神会。
我们打一个比方,百货商店卖床单、被套的那个地方,现在叫“床上用品”,古人称之为“寝具”。现在在台湾地区还有日本,依然沿用“寝具”这个说法。你想,一个总是用“寝具”这样的语词去进行表述和思考的人,和一个只知道“床上用品”的人,他们真的没有什么差别吗?所以我对文言文的态度是很明确的。
现在很多事情似乎都以“喜欢不喜欢”“高兴不高兴”为标准,强调“快乐至上”,这是过于简单、片面了,是有害的。
“快乐”已经成为中国人日常生活中的高频词,甚至成为第一大词。我们整天都在快乐,写作文叫“快乐作文”,学英语叫“快乐英语”,什么前面都有“快乐”这个词。
文学史80%以上的作品是悲剧性的,安徒生最经典的作品都是悲剧性的,《卖火柴的小女孩》一个小女孩衣裳单薄,寒冷的夜晚流浪街头,冻得饿了,饥肠辘辘,只能看着橱窗里头的烤鹅,最后她划亮了一根火柴,用那微弱的灯火去温暖自己寒冷的身体以及更加寒冷的心灵。看那个作品,能看到笑起来吗?如果看安徒生《卖火柴的小女孩》能看得哈哈乐,那一定是狼心狗肺的东西,还是一个人吗?可是《卖火柴的小女孩》难道不需要看吗?所以当我们这样发问的时候事情就很清楚了,孩子是需要悲剧意识的。
有一次我去学校做讲座,有一个家长拿着我写的《青铜葵花》让我给她的孩子签字,我刚要写,她却把我手抓着说:“曹老师,我已经想好了,你按我这句话写——祝你在快乐中健康地成长。”我就停在那个地方,看着她的眼睛对她说:“你以为你们家孩子因为快乐,就算得上是健康地成长吗?”
还有一次我去学校做讲座,我问孩子们:“早上笑,中午还在笑,晚上还在笑,夜里做梦还在笑,这是一个什么孩子?”所有的小孩都说:“傻子。”难道不是吗?你没有悲剧感,不知道痛苦,不知道流泪,不知道感动,不知道悲悯,不知道人来到这个世界上是要吃苦的,是要受难的,你能说你是健康之人吗?所以不要回避整个人生的苦难,要告诉孩子:“你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要吃苦的,不吃苦是不行的。”只有这样,小孩才可能健康成长,当他长大了,在遇到种种的灾难和坎坷时,他才能有坚强的意志。
现在那么多人得忧郁症,难道与这种快乐教育没关系吗?孩子长大以后毫无抵抗力,觉得这个世界是那么难,那么地不可对付,于是他开始走向了一个非常封闭的空间,出现各种各样的心理问题。
说到鲁迅也同样是这个问题。有人总是在怀疑“鲁迅是否还适合今天的小孩看”,可是有没有反思过小孩自己的阅读趣味和阅读姿态?是不是我们的阅读质量出了问题?有没有怀疑过趣味本身?
鲁迅的作品肯定是中小学语文教材的文本来源,最多是篇目做点调整。
中国的苦难和坎坷,向全世界提供了独一无二的故事
读+:前不久您在亚洲文明大会上发言,谈到中国文明对世界的贡献,也谈到自己的创作如何得益于中国文明的滋养。您之前还说过,中国儿童文学的水平,也就是世界儿童文学的水平。那么在您看来,当下的中国儿童文学有没有呈现出与国外不一样的风景?中国儿童文学还可以在哪些方面进一步开掘?
曹文轩:我有两个观点是一贯的。中国儿童文学的最高水平就是世界儿童文学的最高水平;此外不要把世界上所有其他国家的儿童文学加到一起来和中国比,我们可以“单练”。
中国现在是个翻译大国,我们广泛地了解了世界,所有国家最好的儿童文学作品我们都翻译了,几乎没有落下的。也就是说,我们面对的是一幅非常完整的世界儿童文学图景。所以我们有把握说,“我最好的东西不比你差”。此外,把全世界最优秀的东西堆到一起来和中国比,这也是不公平、不科学的。
我们的儿童文学有很多外国不具备的东西。中国经历的苦难和坎坷,向全世界提供了很多独一无二的故事,这些故事不可能发生在伦敦、巴黎。我们当然也可以写小猪小狗小兔子,但是中国的现实生活给中国作家提供了太多写作资源。
中国儿童文学存在的一个问题是“一头沉”,写给大孩子看的这部分比较强大,给幼儿园、小学三四年级以下的“小小孩”写的这部分比较薄弱,包括我自己写的也是偏“大孩子”的。现在我正在“往回撤”,这两年写了50多本图画书。
读+您作品中似乎父亲的形象始终比较强大?
曹文轩:有人对我的作品有一种质疑,认为我没有像写父亲形象那样用力去写母亲,其实我写“奶奶”形象还是比较多、比较好的,《青铜葵花》里的奶奶,像一座山一样支撑起一个家族。还有人说我总是写“温柔的小女孩”,我承认这是事实,但我不可能赞同“女权分子”那种批评。
作家可以有自己偏爱的人物形象,沈从文写的三三、翠翠不都是那个形象吗?这是由作家的美学风格决定的,朱光潜先生讲过,西方美学追求“崇高之美”,中国美学追求“秀美”。这种美学风格通过传统文化融化在我们的血液里,那么一出手写女性形象时,就很容易往“秀美”靠拢,这不能说是男权主义作祟,充其量说传统美学在“作怪”。
所以,有些批评,是为了满足其理论的宣泄,而要求作家牺牲其创作事实,这是不对的。至于有人拿我的长篇小说《天瓢》做文章,说儿童文学里面有色情,这是胡说八道了。我不只是一个儿童文学作家,我写过很多给成年人看的作品,《天瓢》《红瓦》就是给成人看的,当年,《红瓦》离茅盾文学奖只差一票。如果我得了那个奖,今天我们坐在这儿可能谈的就不是儿童文学话题了。
儿童不能只读儿童文学,应该读一切可以读的文字
读+:说到成人,您曾经提到正在编一套给孩子们看的《成人童话》,编这套书的起因是什么?过程中有没有什么感受?
曹文轩:有一些成人文学,它也可以变成孩子的读物。比如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土耳其作家帕慕克、阿根廷的博尔赫斯,他们的很多作品就可以给孩子看。我发现中国孩子很少接触这些作品,所以我最近正在编《成人童话》,把成人作家中适合儿童阅读的作品单独拿出来结集。《成人童话》既是成人看的,也可以给孩子看。
儿童不能只读儿童文学,儿童应该读一切儿童可以读的文字,而且也不光是文学,历史、地理、政治、伦理等方面的书都可以读。
此外,儿童文学和成人文学本质上没有差异,都是文学,它们所遵循的规律是一致的。它们的界限主要是表现在主题、题材上,一些东西你可以向成人展开,但是不能向小孩展开;另外还有一个深浅度的问题,你不能在儿童文学作品里用那些特别深奥的词。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的界限主要是在这些方面。
读+:您提出要写“新小说”,到目前为止已经出版了好几部,这是否可以视为您在创作上的新尝试,是否出现了某些规律性的东西?
曹文轩:所谓“新小说”,主要指的是我要“走出油麻地”。从《草房子》开始,我的不少作品故事基本上都发生在一个叫油麻地的地方,一块如同福克纳所说的‘邮票大一点’的土地。我关于人生、人性、社会的思考和美学趣味,都落实在这个地方。可是,我早就离开那块土地了,我的生活领域大大扩张,我在油麻地以外生活的时间长度已经几倍于油麻地,我有了不同的生活与人生,有了新的生命经验,它们在价值上丝毫也不低于油麻地,那么我可以不再一味留恋、流连于油麻地了,可以使用我这部分写作资源了。写“新小说”,我的感觉十分自然,因为这也是我自己的生活。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的新小说也可以看成我的“出油麻地记”,包括最新的这本《草鞋湾》。旧上海确实有条马路叫草鞋湾路,现在这个路名还在,在上海的南市。为了写好《草鞋湾》,找那种旧上海的感觉,我还去找了程小青的《霍桑探案集》来看,《霍桑探案集》的故事不亚于福尔摩斯探案集,文笔相当好,观念很透彻,在今天看来也不落伍。
侦探题材我可能会再写,《我的儿子皮卡》系列,就会有这样一集,讲皮卡的学校里丢了一幅名画,皮卡和他哥哥很搞笑地要去破案。
当然我也可能还会抽身回头,再去写油麻地。
近年来很多作家进入大学,这是有传统的
读+:您和其他作家的一大不同是您的学术背景和理论基础,而且在方向上不乏“跨界”,比如电影和当代文学;“作家学者化”曾经是热议的话题,今天,您又是怎样看待这种说法?
曹文轩:“作家学者化”这个方向是没错的,当然不是要求所有作家都这样,但是国外其实就是这样的,包括萨特、加缪、纳博科夫,都是作家兼学者,都在大学工作。当代文学的一个问题,可以追溯到上世纪50年代,就是片面强调“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把生活等同于生活经验,忽视了作家的知识背景。其实知识、思想比经验、生活更重要,所以很多作家花了时间去“深入生活”,但是没写出什么来。
近年来很多作家进入大学,这是有传统的,鲁迅、沈从文、朱自清、闻一多都是大学老师。这个传统曾经中断,现在又得到恢复,我们开始重视这个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文学的未来一定是比较理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