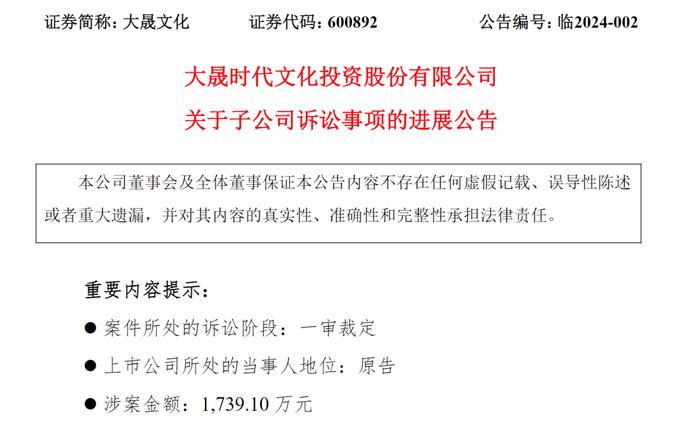寂寞的铁琴铜剑楼——记藏书家瞿凤起先生的晚年
摘要:月白风清之夜,挥手抚弦,一曲高山流水,那铁琴可是声闻三十里呵。但他没多说,移步到书桌前坐下,提笔给我写了一封介绍函,跟着说:“凤起先生对牧斋的材料很熟悉,你去看他,对你研究虞山钱家是有帮助的。
瞿凤起(1907-1987),现代藏书家、古典目录学家。 (资料图/图)
(本文首发于2019年6月27日《南方周末》)
凤起先生亡故后,我去过一次北京图书馆。在一间展览室中,我看到老先生他家那张铁琴。琴没上弦,静静地躺在一个玻璃匣子里。老先生那宏亮的声音:“虞山之巅,……月白风清之夜……一曲高山流水……声闻三十里呵……相见太晚了呵……”却仍在我的耳边萦回,萦回……
瞿凤起先生(1907-1987)逝世已有三十多年了。他是常熟藏书家瞿镛的后人。瞿家的铁琴铜剑楼,和聊城杨氏海源阁、归安陆氏皕宋楼、杭州丁氏八千卷楼,合称清代四大藏书楼。瞿氏的藏书,历一百五六十年然后开始失散,私家收藏,经营时间之长,仅次于范氏天一阁。从瞿家祖上聚书,到凤起先生为止,算起来,刚好是五代。凤起先生无子嗣,铁琴铜剑楼恐怕就从此随凤起先生的亡故而变成历史的陈迹了吧。
1985年夏天,我和内人带着小儿到沪上查阅上海图书馆藏的清初诗文集。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凤起先生。往后两百多个日子里,每隔一星期便去看他。那时,凤起先生孤身住在闹市中一间简陋的斗室里;老伴已于前数年逝世,日常生活靠一个五十多岁、目不识丁的女佣人来打点。又因为两腿在丙午乱中受伤,不良于行,已有十多年没有出门了。但每天仍勉力靠双手将身体从床上挪到书桌旁的藤椅上,坚持一丝不苟地读书、作文。他不理会外边的世界,外边的世界也不来打扰他。
和凤起先生的交往中,我除了体验到一般老人的孤单和寂寞之外,还亲眼看到一个旧时代的读书人,如何在一个急剧改变的社会中顽强地坚持手不释卷的生活;我看到一个年近八旬的老人,如何在身心都背负着生活给他的累累伤痕时,仍孜孜不倦地为传统文化留下火种。
这篇短文,一方面要追述我和凤起先生之间一段不比寻常的友谊,一方面要把他那严肃认真的治学态度,和谆谆勉诱后学的精神记录下来,作为对凤起先生的怀念。
〖一〗
1985年在沪上期间,常常在周末和妻儿到苏州短住。内人的娘家在苏州,而我则顺道去看在那里教书的钱仲联先生。钱先生和我以前通过信,也见过面,我曾多次向他请教过有关明清之际文学上的问题。那时,我正在整理钱遵王的诗集,也开始对清初人对钱牧斋评价的转变这一问题发生兴趣。钱先生原籍浙江吴兴,却从小在常熟的翁家长大,对虞山的掌故熟而能详。在一次闲谈中,又知道钱先生在抗日战争初期随无锡国专迁到广西北流任教,我的父亲曾在那里跟他念过书。论起行辈来,钱先生应是我的“祖师爷”了。
大约是夏末秋初,钱先生向我提及瞿氏铁琴铜剑楼藏书流散的往事。并说起瞿家的后人凤起先生正好住在上海,敦促我找时间去看看他。
关于铁琴铜剑楼,以前在叶昌炽的《藏书纪事诗》中看过一些有关的材料,但印象却已模糊。瞿凤起的名字倒并不陌生。廿多年前曾购得他所编的《钱遵王藏书目录汇编》。但自己对目录版本之学,本无慧根;凤起先生的书,虽也跟着我飘洋过海,但却从未细读过。因此,虽然自己立意要整理钱遵王的诗集,却没有想起凤起先生这本书来。
钱先生似乎也看出我对他这一建议反应“冷淡”。但他没多说,移步到书桌前坐下,提笔给我写了一封介绍函,跟着说:“凤起先生对牧斋的材料很熟悉,你去看他,对你研究虞山钱家是有帮助的。”接着又说:“凤起先生两腿不良于行,他是从不出门的。你什么时候去,他都会在家。只是他的常熟话不易懂。可得带个翻译去。”
〖二〗
凤起先生住在北京西路1290号。我和内人按址找去,看见一幢古旧的西式楼房,想是以前租界时代遗留下的物业。房子的大门敞开着,里面却阴暗得很,甬道两旁摆满了杂物,楼梯的边上有人在生火烧饭。内人轻声对我说:“这四层楼的房子,可至少住有十多户人家呢。”
内人用上海话和烧饭人说了一阵话后,拉着我的手便往楼上走。那时该是下午四五点钟,屋外阳光普照,而我们却在楼梯上摸索前行,举步维艰。我把抽烟用的火机打亮,这才安心地一步步沿梯而上。
凤起先生住在三楼通往四楼间的一个亭子间。敲门进去,老人正在伏案写字。房间大约是十英尺见方,是卧室、书房,也是吃饭和接待客人的地方。进门右边有一张木板床,床头恰可放下一架书。床边摆着一张方桌、一张藤椅,对着两扇开着的窗,窗外是小巷,桌子左旁有三四张旧红木凳子,上面堆满了书籍。老先生的女佣人张罗了好一阵子,才找出两张椅子来让我和内人坐下。
呷了一口茶,再细看房内的摆设:桌上有笔墨纸砚,有热水瓶、茶叶罐,还有几只青色的小苹果。墙上挂着一张年迈妇人的照片,想是老先生死去的妻子。房的左边另有一道门,通往另外一间面积更小的房间,里面有几个木箱子、一张床,大概是女佣睡觉的地方吧。也许是因为房间位于两层楼之间,天花板很低,使人有说不出的局促之感。
内人用上海话向老先生说明来意。老先生细细地听,偶然向我看一眼,脸上却木无表情。
内人把话说过了,老先生朝她说:“我和钱老不见面已二十多年了。他的身体应该比我强吧?”语气有感叹,也有点自怜。却不是容易接口的话。我和内人相望了一眼,没有说话,房内的气氛便更局促了。最后还是我先再开口的,我向老先生请教有关钱遵王的诗集,并向他打听常熟图书馆所藏的《遵王诗辑》。
老先生似乎没有听懂我的话。内人只好用上海话再说一遍。
好一阵子,老先生才对内人说:“请转告谢先生,我解放后没去过常熟。那边的情况我不熟悉。我以前编过一部《钱遵王藏书目录汇编》,他的诗我没研究过。”
我向内人看了一眼,示意她我听懂了他的话。这时,我发现门外站着一个中年男子,朝房里看。房里的人也不再说话了。
我站起来告辞。把带来的一篇刚发表的有关遵王的短文送到他手里,说了些请指正的客气话,准备离去。
这回,老先生却像听懂了我的话。他说:“请再来。”但表情却仍然是木然的。内人在旁笑着对他说:“他下星期便再来看你老人家。”
回程上,心里很不是味儿。怎么老是一副拒人千里的面孔?而且老是一问三不知?我于是开始怀疑起钱老先生和他的交情来。但内人不同意我的推测。她的看法有二:一是老先生的记忆力也许是衰退了。二是我究竟是从外边回来的,只凭一封私人介绍信便去看他,这是不符合“内外有别”的原则的。内人又说,谁知道那个突然在门外出现的中年人是何方神圣?看来老先生对他是颇有顾忌的。
〖三〗
大约过了两个星期,我终于鼓起勇气再去看凤起先生。老实说,我对常熟图书馆藏的那部《遵王诗辑》仍然没有死心。而且,还决定独自去。心想:老先生的家乡话我是可以对付得
来的。要是真听不懂,以笔代舌也可解决。
老先生的房门是敞开着的。像上回一样,他正在伏案工作。
“是谢老吗?请进来!”
我比老先生小三十多岁,他怎么竟称我为“老”?但声音却是温和的。
“不是约好一个星期便来的吗?这好像已经有十几天了。你那位翻译呢?”
我连忙解释那位“翻译”是我的内人,并打诳说她有事,不能同来。
老先生呵呵大笑起来:“原来是尊夫人。我以前听说回来的人都带着外办指派的翻译一同出入的。我弄错了。”老先生把我上回送给他的文章找出,指给我看他在文字上改动了的地方。然后说他大体上赞成我对遵王诗的看法,但关于遵王在明朝取得科名、入清后不仕、应视为遗民一点,老先生的态度是有所保留的:“我记得在一本清初修的《常熟志》里,遵王的科名是在清朝取得的。手头无书,待我以后替你再查。”
老先生的记忆力并没有衰退。内人的第一个推测是不确的。
从遵王自然便谈到他的族曾祖牧斋。老先生把一篇他发表在《中华文史论丛》关于现存牧斋文集外佚文的文章送给我。文章的首页已题了我的名字,可见他是等着我再来的。
“关于牧斋的诗,钱先生比我内行多了。他整理过《初学》《有学》两集,我只提供了材料。他才是专家。”老先生的语气是诚恳的。他对钱老先生究竟是极佩服的。我自己先前的怀疑,也自是不必要的了。
那天我们谈得很投机,偶然有言语不通的地方,便用笔谈。第一回出现过的中年人也来过一两次,每次站在门外两三分钟。他一出现,老先生便面呈不悦之色,并且示意我不要开口。
直到半年之后,我才从别人的口中知道这位中年人原来是凤起先生的一位远亲,凭了凤起先生的关系,住进了这幢房子,却把原来分派给凤起先生在二楼的住房给占用了,让老人住到亭子间里去。每次有人来看凤起先生,这个中年人都会出现,一来看看客人提了些什么礼物来,一来看看凤起先生是否把所藏的书物赠给来客。
〖四〗
铁琴铜剑楼极盛之时,藏书超过十万卷。瞿家历代对书籍,都抱着书贵流通、“化身千百”的态度,不像有些藏家不轻以书示人。1919年后十数年间,上海商务印书馆筹印《四部丛刊》,铁琴铜剑楼的主人便慨出家藏,玉成其事。这件事的先后在凤起先生所撰的《先父瞿良士先生事略》中有详细的记录:
己未(1919)之秋,上海商务印书馆同仁,以神州多故,国学寖微,创议影印古籍,欲网罗巨帙,以成学海之巨观,以便学者。董其事者海盐张菊生、无锡孙星如两先生由沪假道昆山,驾扁舟至罟里见访,道使命,商请发棠,共襄盛举。先父素抱书贵流通,能化身千百,得以家弦户诵,善莫大焉,私志不谋而合,遂被推为发起人,相计就地取材,豫约次年派员来吾家摄影,借以付印。越三载,至壬戌(1922)告成。颜曰《四部丛刊》,所收凡三百二十三种,出之吾家者二十五种,其数为采自私家所藏者之冠。
甲子(1924),齐卢构衅,闾阎杌陧,吾家移书沪渎,商务馆以世多故,古籍销亡,国学起衰,相需尤亟,以《初编》为未足,故有《续编》之议。先父继承旧志,尽出家藏,请选所需,俾成美备。期年告成,全编凡七十五种,出吾家所藏者逾半,达四十种。
次年,又赓续《三编》之辑。共七十种,吾家占十六种。
瞿家对私人“欲假善本影印或复刻,亦有求必应。而于乞求传录者,每为之代觅写官,付之精缮。数十年中,未尝间断,累计在千卷以外”。可见铁琴铜剑楼的藏书,在近代书籍文献的流通上,曾经做出过多么大的贡献。
1949年后,瞿家的藏书全部归北京图书馆。
〖五〗
从认识凤起先生时,他的亭子间里仍堆着一包包用旧报纸包好的书。桌上、杌上、床头、床底下都有,而且堆得也颇整齐。包外没有标记,别人是不知道他藏有些什么书的。我在想:这些也许就是铁琴铜剑楼的劫余之物了吧。但究竟有多少,是些什么书?我始终没问过他。
从1985年秋到翌年7月,我几乎每周必在那个亭子间里坐上个把小时,陪他老人家喝茶、聊天。
每当我和他谈到一些学术上的问题,他总约我下次来看书。如我偶然因故没去,老先生便会寄一封类似这样的短柬来催促:
别又数日为念。累室粉刷,业已竣工。
亟将约看之书,分别检出,乞安排时间,别前得以过目,想必乐从。恭候驾临,余容面谈不赘。敬请暑绥。弟瞿凤起。
那八九月里,我在老先生那里浏览过很多书籍,可惜当时没有详细记录下来,实在是一件愚蠢至极而又永不能补偿的憾事。在看过的书中,印象较深的是一批有关柳如是的材料,因为凤起先生好几次提及陈寅恪先生晚年著书岭南,无机缘读到他所藏有关钱柳的一些资料,言下不胜唏嘘。
除此之外,令我难忘的是一册极珍贵的抄本。
记得那是因为一次老先生小恙初愈,和我谈起养生,又谈到食疗,便从书架上取出一本用黄绫包好的册子,是他以前手抄的一种宋人著述,书名是《养老奉亲食治方》。抄本后有他亲笔写的跋文三篇。跋文道出此书的价值和流传经过;字里行间,也流露出他对书籍的那份狂热:
此册从杨毓斯表弟藏本传录。其原出宋本,半叶九行,行十八字,双鱼尾。避讳至慎。字为孝宗时所刻,但无年岁。当在隆兴至淳熙间。据毓斯云,原本为我家旧物,渠从伟堂伯处借抄。伟堂为我姑丈。此书或以药食相合,已非纯粹医家之属,故不载我家书目,为祖辈所投赠。姑丈无后,以毓斯之胞兄应潮二表兄为嗣。兵燹之后,城西程家巷杨氏旧宅,大部被毁。宋刊原本《养老奉亲食治方》当亦化为灰烬。此书未见别家著录,人间已无第二本。亟从其传录一册,并记其原委如右。
此册传录,尚系若干年前事。毓斯亦早退休,居苏城已十余年。追忆所及,再记于后。乙丑小寒,瞿凤起识。时年七十有八。
册中书眉文字,疑为后人所加,非原书所有。册尾行在云云,当为杭州所刊行。橘园亭郭十郎书铺掌故,容俟续考。是日严寒,北窗冰冻,至午后始解。
那段日子里,他一边替黄虞稷的《千顷堂书目》作校补,一边整理钱遵王的《读书敏求记》,都是工程浩大,而又必须是心细如发的人才能胜任的研究项目。除此之外,他还抽空写些短文。据我记忆所及,我和他交往的八九个月中,他至少完成了《重校本〈万卷堂书目〉跋》《虞山毛氏汲古阁图题咏》,和一篇讨论两宋版本的文章。
〖六〗
老先生的亭子间里还有不少他戏称为“小玩”,实际上世不经见的东西。他珍爱这些东西,也如同他珍爱书籍一样,却也常常表现出一种令人惊讶的豪情。记得1986年农历春节,我和内人带着两岁的小儿去给他拜年,事前是约好的。坐下不久,凤起先生便指着桌上说:“今天为你们全家都准备点小礼物。就照洋人的规矩吧,可以在我的面前把礼物拆开。”送给小儿的是一件白玉挂件,送给我的是一叠宋纸。“我们上星期不正好谈过宋纸吗?”送给内人的,是一方颇有来头的墨。墨上刻有几行字:
古有九子之墨祝婚者多子善祷之像也。词曰:九子之墨,藏于松烟,其性长生,子孙无边。
这方墨便叫作“九子之墨”。老先生把《文房四谱》一书打开,翻到卷五“墨叙事”一节,墨上刻的几行字,便正印在书上。
看过礼物后,内人和我相看了几眼,心里感激老先生这份盛情,但两人都一时不知说些什么。还是他先来打开僵局:“我年轻时是念会计的,也学过点洋文。原本想出洋留学的,所以也知道一些洋规矩。后来家父劝我守着家里的藏书,才取消了出国的念头。要是当年出去了,现在便不也像正光那样是个归国学人了吗?”说罢哈哈一笑。我却更不好说话了。
我那时正从师习古琴,他知道后,便替我找出好几册手抄的琴谱,为我详道虞山琴派的源流,并敦促我到常熟去找翁家的后人痩苍先生习虞山琴法。他说他的高祖荫棠先生当时因为家里藏有一张铁琴和一把铜剑,才把藏书楼这样命名的。铜剑早已流失了;铁琴则于1949年后上缴国家,现仍存在北京图书馆。“抗战以前,虞山琴社的一些琴人曾携我家的铁琴到虞山之巅开琴会。月白风清之夜,挥手抚弦,一曲高山流水,那铁琴可是声闻三十里呵!谢老,咱俩可惜是相见太晚了。”
〖七〗
1986年春末,我去了一次常熟在那里,和翁瘦苍老先生弹了半天琴、踏勘了几处钱柳遗迹、参观了曾国藩幕友赵烈文的一处庭园。然后试图到图书馆看那本《遵王诗辑》,但在门口便被挡了下来,原来那里是不对外开放的。那时,常熟县政府拨了巨款,正在重修瞿家原有的铁琴铜剑楼,作为对外开放的一个观光点。朋友怂恿我到罟里去看看。起先有点心动,但想起以前在其他地方看过的一些重修过的古迹,又想起凤起先生住的那个亭子间,我还是决定不去。
回上海后,我告诉老先生重修铁琴铜剑楼的事。他淡然,没说什么。我也就不提在常熟图书馆被挡驾的事。我们谈了一些有关钱柳遗迹的事之后,他从一个小盒子里检出了两粒红豆:“这是常熟产的,和钱柳他们当年所咏的红豆,同一来源。寅恪先生在《柳如是别传》末章所说的红豆,倒是五岭以南之物呵。” 说罢又是哈哈一笑。那爽朗的笑声,把我心里那股从常熟带回的阴霾气,一扫而空。
不久之后,我结束了在上海的研究工作。临行前,他来过一封短柬:
上次匆匆话别。记得说起周四过我,知诸事亟待小结,无暇可抽,亦意中事。但小别须五月,总望别前再得多谈一两次,并希将照相机带来,再为我多摄一次。劳动大姐(注:指女佣)亦有盼望。辱承垂注,特此奉恳。承示近著,当细细阅读。又承厚赠邮花多枚,谢谢。专此奉达,敬请撰安。教弟瞿凤起上。
我连忙赶去。
那天,老先生像是料到我要来似的:水果、蛋糕、清茶和香烟罐都让佣人摆好了。像往常一样,书桌上、短杌上,都摆满了用旧报纸包好的书,等着我浏览。
那天他给我看了些什么书,大都记不清楚了,只记得其中有一册《瞿氏四代忠贤遗像》,是1920年无锡孙毓修在上海刊印的。《忠贤遗像》中的第三像,便是那位明末殉难于桂林的瞿式耜。原来铁琴铜剑楼的主人,竟是这位明代忠臣的后裔。这一点是我以前不知道的。
书看过后,老先生照例问我要不要借去复印一份。我说不久便要离去了。待来年一月见面时再说吧。
一提起离别,老先生似乎有点黯然。彼此沉默了一阵。
他问:“回去后,要做的事很多吧?”
我笑笑,告诉他回去后便得准备申请升等的事了。我那样说,无非想让他高兴一下,以便把离别的话题扯开,老先生沉吟不语。好一会儿,才正色说:“在外边升等,著作一定很重要吧!我最近在写一篇有关版本的文章。写成后,你来把它翻成英文。这样,你可多一种著作,也可算是咱俩友谊的纪念。你看呢?”我笑而不答。心里在想:要翻译他老人家的文章,无论是就版本学的修养,或是翻译的造诣,我都万万不能胜任。再说,即使我费了力气把文章译成英文,现存的外国汉学家中,又有几人对版本学有兴趣呢?
但我没有告诉老先生这些话,生怕令他沮气。只说希望他及早把文章完成,让我来时好好拜读。
〖八〗
1987年1月,我因公去上海,得以和凤起先生再见一面。那时,老先生好像仍精壮如前,只是他的哮喘有点令人担心,不意两个月后,他便因哮喘发作而逝世了。
凤起先生亡故后,我去过一次北京图书馆。在一间展览室中,我看到老先生他家那张铁琴。琴没上弦,静静地躺在一个玻璃匣子里。老先生那宏亮的声音:“虞山之巅,……月白风清之夜……一曲高山流水……声闻三十里呵……相见太晚了呵……”却仍在我的耳边萦回,萦回……
谢正光 美国格林奈尔学院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