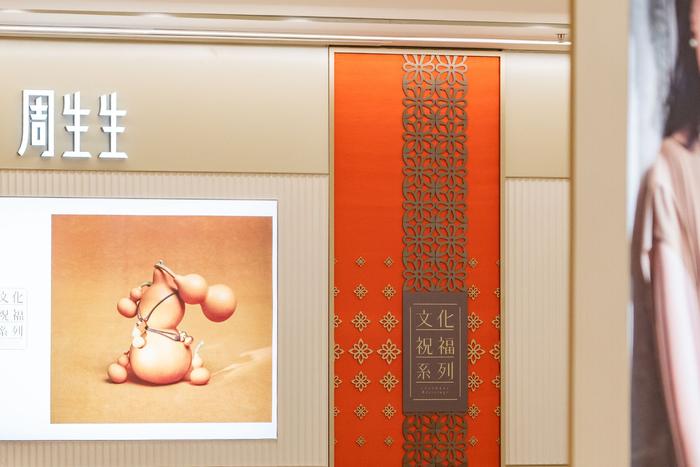王家衛:香港的詩意 失意 追憶
摘要:和香港一樣,王家衛的電影也是在一朝一夕之上建立起來的,流亡是易逝的,懸崖邊建起的城市也是易逝的,它的身份,甚至在CHINA這個隨時可能將它建立起的一切頃然吞噬的龐然大物面前,存在也是易逝的。這其間迸發出的能量如今被寫進了王家衛的電影,對於所有在那個年代的香港生活過的、有幸見證這一美好時刻的人來說,它都是熾熱、難忘的。
原標題:阿薩亞斯評王家衛:香港的詩意、失意與追憶
2017年10月在電影誕生地法國里昂,一年一度盧米埃爾大獎頒發給了中國香港導演王家衛,他也成爲了獲得此殊榮第一個亞洲電影人。盧米埃爾大獎是由現在戛納藝術總監福茂創立,每年十月依託法國里昂盧米埃爾電影節表彰一位全世界最傑出的電影人,試圖打造電影界的諾貝爾獎。這項大獎從2009年開始頒發,獲獎者均爲在世公認的頂級電影人,目前獲獎九人分別爲:克林特·伊斯特伍德、米爾斯·福爾曼、傑拉德·德帕爾迪約、肯·洛奇、昆汀·塔倫蒂諾、佩德羅·阿莫多瓦、馬丁·斯科塞斯、凱瑟琳·德納芙、王家衛。
數位王家衛在世界各地老友都來到里昂與王家衛團聚,見證他的獲獎。其中,法國著名導演、批評家奧利維耶·阿薩亞斯也宣讀了他爲王家衛獲獎專門撰寫的文章《回憶之憶》(Le Souvenir du Souvenir)。早年,當阿薩亞斯還是《電影手冊》影評人時,因發現了臺灣新電影,他與華語電影人結緣,並努力將侯孝賢、楊德昌推向了歐洲,乃至全世界。而在世紀之交,他與張曼玉那段廣爲人知的婚姻,則讓他進一步深入了香港電影工業,也與王家衛結下了深厚的友誼。
很長一段時間裏,香港(HK)都很少出現在香港電影中。大多數導演選擇棚內拍攝,因而忽略了自己生活的城市。那時候的香港電影沉醉於神話傳說和虛構的武俠世界,也即“江湖”和“武林”,直到李小龍的出現,電影纔開始轉而關注我們當下生活的城市,但也總帶着一絲唯有通過暴力方可立足的叢林現實主義的意味。
然而HK真正迷人之處,也是令初來乍到的我最受感染的地方(1984年,彼時我還是一名年輕記者),似乎並未被展示出來,包括城市的緊張感,其強烈的對比、令人迷醉的魅力,還有種種謎團。它們其實就蝸居在城市最不起眼的角落——灣仔的酒吧,或尖沙咀人滿爲患的樓房,儘管那些在緊急局勢下倉促完工且歷經四十載的房子已經老舊不堪,甚至連牆皮都脫落了。
王家衛的靈感來自於城市的詩意,小巷、深夜、霓虹燈、街邊的餐館、雙層公交和迷宮般的後院,構成了這座城市獨特的美併爲導演所用。這座城市幾乎是一朝一夕建立起來的,在四五十年代,爲了接收從日軍侵佔的上海逃難過來或是後來CHINA內戰時期的移民而建。
儘管如此,HK卻開創了自己獨特的文化。它首先是中國內地與現代西方交流必經的窗口,同時也有着無可比擬的燦爛建築景觀。香港濱海花園的景色令人難忘,太平洋的風翻湧起的雲層讓天空變幻莫測,一棟棟摩天大樓在天空的映襯下變得清晰。
島嶼面朝海灣,日光下,海水每時每刻變換着色彩,而當夜晚降臨,它便映出島上的景色,像一塊色彩奪目的調色板,被往來的天星小輪刻下道道紋路。此時,城市在斑斕的閃光和霓虹燈點綴下,彷彿自己也成了海面的延伸。
和香港一樣,王家衛的電影也是在一朝一夕之上建立起來的,流亡是易逝的,懸崖邊建起的城市也是易逝的,它的身份,甚至在CHINA這個隨時可能將它建立起的一切頃然吞噬的龐然大物面前,存在也是易逝的。王家衛是這個轉瞬即逝的世界裏手握繮繩的人,因爲他知道電影有一種凍結時間的魔力,它能證明其他藝術抓不住的東西真實存在過。
要怎麼再現出那個年代的脆弱呢?香港未來會發生什麼未可知,CHINA是否會報復這些分LIE分子,這些離開大陸的移民,同樣未知——他們本身也是political移民,背棄了大陸並走上了一條混合了西方制度的道路,卻又不得不重新面對中國和它的二十一世紀。
沒有什麼是牢固的,時間亦如此。飛逝的時間催促着人們必須抓緊所剩無幾的時日把一切該講的講出來,做一切該做的,發掘一切假設;這其間迸發出的能量如今被寫進了王家衛的電影,對於所有在那個年代的香港生活過的、有幸見證這一美好時刻的人來說,它都是熾熱、難忘的。
把王家衛簡單歸爲是1997年前那個時代的反映是不公的,因爲構成他的首先是流亡的傷感,對離開、消失的上海的傷感。三十年代的上海是“另一個”中國的首都,它朝向未來,星光璀璨,燈酒繁華,還有奪目的外灘,這是日本入侵前和內戰爆發前的CHINA,它可以媲美歐洲,和美洲抗衡,它光芒四射,而且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是無憂無慮的。這樣的一個上海形象似乎成了香港的心結,也在王家衛塑造的城市中每個隱蔽的角落得到體現。這是對上海的回憶,是一些人對他們從未經歷過的歲月的傷感,對那個已經被吞沒的世界的追念。
1997年到來之前,這種回憶自身也快被吞沒了,只剩下曾經足跡的足跡,和對回憶的回憶。“你哭的時候自然會哭,那時候時間會過得很快,就如每一個時候。”詩人阿波利奈爾這樣寫到。王家衛則是這樣一位回憶記憶的導演,正如帕特里克·莫迪亞諾(Patrick Modiano)是一位回憶記憶的小說家。在我看來,這兩個藝術家之間似乎有某種既神祕又顯然的關聯,雖然我們今天的盧米埃爾電影節並不是要爲他頒發諾貝爾獎。(譯註:帕特里克·莫迪亞諾於2014年獲諾貝爾文學獎)
可能也是出於這個原因,在金融危機之後,渡過難關之後,人們發現世界並未崩塌之後,王家衛沒有投入到當下,而是選擇展望一個設定在2046年的將來,一個由HK特殊身份——CHINA賦予其的一國兩制——決定的期限。
彷彿期限向後順延,倒計時重新開始一般地,世界末日被推遲了,但卻沒有被撤除。又或者,我們可以說,並非CHINA吞掉了HK,而是在香港、臺北和新加坡發明的“二十一世紀CHINA”這樣一種意識吞掉了CHINA,無論它是好是壞。
《2046》
王家衛作品中的詩意、對不可見不可知的追尋,在一般電影中很難得到如此真實、有深度地體現。因爲這很難。因爲這是一扇永遠難以開啓的門。同樣也因爲電影的手法、敘述話語、敘事、時長限制、經濟上的要求不允許、乃至禁止這麼做。
但有時候,一些導演會打破這些規定,認爲這些遊戲規則不適合他們,與我們的期許背道而馳,然後創造出展現自己藝術和獨特天分的電影手法。王家衛就屬於這一類稀有的導演。他將劇本、編劇理論、計劃、預算限制、技術、傳統、規則,所有這一切付之一炬,在他看來,必須擺脫這些才能發明方法,才能創造出將靈感發揮至極的必要算法。
王家衛在片場
拍攝一部電影,王家衛往往會花上好幾年的時間,拍攝的片段會在剪輯室被重新組織,各片段之間由畫外音銜接。剪輯所遵從的邏輯有別於其他任何導演。
詩意的密度和厚重感
然而,不把王家衛視爲現代電影形式上的開創者也是不準確的。但形式上的開創性指的是他追尋的道路將我們帶到全新的疆域,他革新了香港電影、中國電影的創作模式,並極大充實了一般現代電影的體系。
集體作品,所有的電影作品都是集體作品,但是王家衛的作品體現出不止一般的集體性,而他的合作者也不只是一般的合作者。他的製片人彭綺華幫助他成立了澤東電影,也因此讓他如此獨特、個人化的方式得以實現。當然,還有張叔平,他是王家衛電影的剪輯師,但更是雕塑師,從這個意義上講,他是王家衛真正的編劇,除此之外,他也負責服裝、佈景,是他讓集體記憶中的鬼魂得以重生。
還有他初期電影的攝影師杜可風(Christopher Doyle),我認識他比他認識王家衛還久,我們1984年在臺北相識,那會他剛剛結束他的第一部電影,那是我離世的朋友、另一位中國現代電影巨匠楊德昌的作品《海灘的一天》。
我還記得我是如何被王家衛和杜可風使用攝影機的方法驚愕並深深啓發,他們把一個鏡頭在拍攝時中斷,他們將畫面加速、減速、中止,就像音速青年的瑟斯頓·摩爾虐待他的吉他一樣虐待它,畫面變得抽象,攝影機在畫面上留下劇烈的筆觸。他們發明了一種電影中的朋克搖滾,無所謂真,一切都被允許,就這樣點燃了那些歲月。
張曼玉在《花樣年華》
如果真的說要回望歷史的話,那就是後來的一些軼事了,當然,對我來說是很重要的,可以說是王家衛改變了我的人生。《阿飛正傳》和《東邪西毒》裏讓我着迷的女演員張曼玉(Maggie Cheung)因爲後一部片子參加威尼斯電影節,而剛好我也在。我對她心動到乃至爲她寫了一部電影——《迷離劫》,和她一起生活,和她結婚,然後爲她寫了第二部電影,《清潔》。
那幾年我在HK待的時間很多,在一個屬於王家衛的世界裏,那會兒我們常常見面,這種親密,這種友情,是那個時期最寶貴的回憶。直到今天,我都爲自己能因合適的時機參與投入到王家衛最美的電影之一——《花樣年華》的拍攝感到高興。
另一件軼聞,大約是在1997或1998年,也挺久遠了。我最開始和一位製片人Éric Heumann做一個項目,因爲各種不幸的原因沒有成功,但最後我們也沒有彼此怨恨,甚至一直保持着聯繫。總之,Éric給我打電話,想讓我幫他和一位他很欣賞的侯孝賢導演牽線,並拍一部片子,他剛剛賣出他在一家公司的份額,手裏有充足的本錢。
那時恰逢韓國經濟危機,王家衛下一部,剛好也是張曼玉擔任女主角的電影的韓國合夥人突然不見蹤影。項目能否實行都成了問題。王家衛路過巴黎時告知了她這一壞消息,張曼玉顯然是非常失望。晚飯過後,我們一起在家喝了一杯,我記得我當時問他,這是錢的問題嗎?或者還有別的,更復雜的原因?不,沒有別的,就是融資的問題。我於是告訴他,《春光乍泄》之後,他根本不愁找不到法國合夥人。是嗎?那找誰呢?他不太想挨個問製片人,這實在不是他的性格。但如果我認識一個靠譜的製片人,他可以明天出發之前和他見一面。
我給Éric Heumann打了電話,他看過幾部王家衛的電影,但這次突然的見面,還是需要重新梳理一下記憶的。我們第二天約在一家酒店的酒吧裏,說實話,談話並不是非常熱烈。最後Éric才問到關鍵:“What’s the story (故事是講什麼的)?”王家衛猶豫了很久答道:“It’s a love story about food (這是個有關食物的愛情故事).”Éric馬上說:“I like it. I’ll produce it(我喜歡,我要做這個片子).”然後最不可思議的是,他還真的投了!這也成了王家衛電影拍攝衆多奇聞中的一件。
拍攝過程持續了兩年,在這期間,我自己也拍了一部歷史題材、長達三小時的電影《情感的宿命》,我們倆也都參加了2000年戛納電影節的競賽。這一屆,機緣巧合,帕特里克·莫迪亞諾是評審團之一而梁朝偉榮獲了最佳男演員獎。四年之後,張曼玉則因爲我的電影《清潔》獲最佳女演員……
如今,香港電影產業的核心已經轉移到了中國內地,在那裏,本土大片也得到發展。中國有着和好萊塢工業競爭的野心,也比任何時候更死守其窒息現代形態並嚴重遏制中國在現代電影發展中地位的審CHA制度。
香港並沒有等2046,也沒有任何倒計時存在,結合就將這麼進行下去,且似乎比我們預期得更早。然而我們可以說香港電影保留了——儘管並不非常顯著——它獨有的聲音以及決定香港電影的Freedom空間。但王家衛始終是其中一員嗎?難道不更應該說,他已經成爲一名座標香港、與時代電影對話、脫離了對他創作動機起決定作用的城市身份和文化身份問題的國際導演嗎?簡而言之,王家衛創造的風格如此有機地和他特定的文化土壤聯繫在一起,能夠在世界範圍內被接受嗎?是的,當然,比如《春光乍泄》便是一部出於1997年之前的緊張感以及思考在別處感受香港的可能——比如其對蹠點上而寫作的電影。
而《藍莓之夜》和《一代宗師》這兩部電影則讓我感覺這個問題是開放的,它將繼續質問王家衛的電影,而王家衛的電影也將反之繼續挑戰它,我們要知道,他除了解決問題沒有別的出路,而這就是他今後電影的核心所在,這也是今天許多其他大導演面對的問題。
(圖片來源於深焦DeepFocus及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