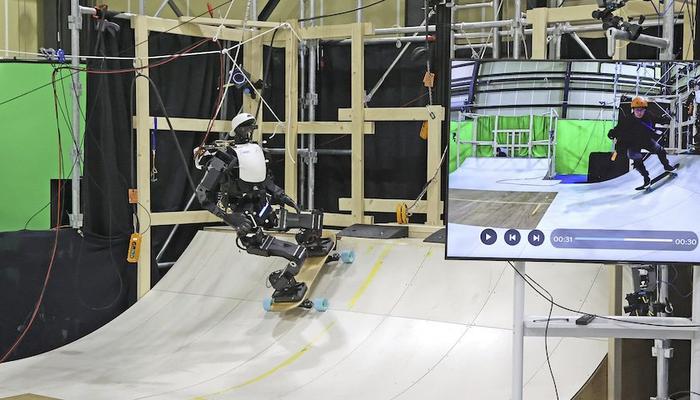這所只存在了八年的大學,值得我們一唱再唱
摘要:西南聯大成立不久,南開校長張伯苓對蔣夢麟說:。爲日本人做丁點之事都是陳寅恪不能想象的,他決定立馬祕密離開北平,只爲延續中華文脈,他說:。
這些天,高考學子們最大的難題之一是選擇學校吧?
我不知道,如果這所學校還在,它是否仍是人們心中的最佳選擇。
如果是,我不知道,那是它的榮耀,還是悲哀?
它的名字叫做:西南聯大。
1937年9月10日,國民教育部發出第16696號令,組成長沙臨時大學。
1938年4月,學校到達昆明,改稱“國立西南聯合大學”。
1946年7月31日西南聯大停辦,共存在了8年零11個月。
在此期間,它培育了2位諾貝爾獎獲得者、8位“兩彈一星功勳獎章”獲得者、171位兩院院士,此外,還有很多我們熟悉的各界泰斗,諸如汪曾祺、殷海光、許淵衝、何炳棣……
有人說:這所學校猶如中國教育史上難以逾越的珠穆朗瑪峯。
不,這所學校,值得我們一唱再唱,絕不僅是因爲這些數字和名字。
01.
星斗其文,赤子其心——沈從文
那一天,那些天。
1937年7月14日,清華園遭日機轟炸。
吳宓教授擁被坐在牀上,四周的牆壁被轟炸震動而脫落。面對國難,吳宓痛悔自己因沉浸個人世界而造成的虛弱與虛度,他強烈自責:
生復何用?生復何用?
日記中,他寫下了:
聞報,知戰局危迫,大禍將臨…...今後或自殺,或爲僧,或抗節,或就義。
這位哈佛大學的高材生其實也有另一條路可走,那就是到沒有戰火的西方去。
然而於他,這樣的道路是不存在的。
1937年7月29日,日本軍隊的皮靴踏響金水橋,開進了靜默的故宮,北平淪陷,中國軍隊被迫撤出了故都,那些手無寸鐵的人,還在。
清明月色下,吳有訓與馮友蘭沿着清華校牆,一同巡夜,斯文如水的他們想以這樣的方式守護鐵蹄下的校園。
在一片狼藉又靜得可怕的校園裏,馮友蘭泫然欲泣,吟道:
“如此星辰非昨夜,爲誰風露立中宵?”
年輕時的陳寅恪
彼時,陳寅恪的悲痛比他的同仁們更爲深切,他年逾古稀的父親,著名愛國詞人陳三立,在日軍佔領北平後,就拒絕進藥進食,爲國盡節而死。
父親的喪事尚在辦理之時,陳寅恪就接到了日本人送來的邀請函,要他到日本使館赴宴。
爲日本人做丁點之事都是陳寅恪不能想象的,他決定立馬祕密離開北平,只爲延續中華文脈,他說:
救國經世,尤必以精神之學問爲根基。
北大當時由鄭天挺教授主持工作,在日軍進城之後,他不顧夫人新喪的悲痛和子女年幼的拖累,在嚴峻紛亂的局勢中,全部身心用於保護校產和組織衆多師生安全轉移。
然而,他再怎樣傾心竭力,亦無法讓這所一向傲然的莊嚴學府免遭踐踏。
日本憲兵搜查北大辦公室,發現抗日宣傳品,藉此進駐北大紅樓。
維持會查封了北大二院,北大變成了日寇關押拷打愛國學生的地獄。
南開的境況還要慘烈。
南開有一口大鐘,原爲李鴻章祝壽所鑄,和平之時,每年鐘響之數,即爲南開畢業人數。東北淪喪之後,大鐘就以九一八爲鳴響之數,聲聲震耳,警示國人,也令日軍不安。
南開校鍾
日軍對南開仇恨已久。
7月79日,南開大學突遭日軍兵營炮擊,頓時樓塌屋倒,幾十萬冊珍貴圖書和資料化作菸灰。轟炸之後,日軍又在校園四處縱火焚燒。
在日軍毀校的日子裏,大鐘不知去向,有說已被熔鑄,有說被日軍砸成碎塊,運往日本。
校長張伯苓聽聞苦心瀝血經營的校園已成爲一片廢墟,悲愴不能自已,當場昏厥。
甦醒之後,他對《中央日報》記者說:
敵人此次轟炸南開,被毀者南開之物質,而南開之精神,將因此挫折而愈奮勵。
這簡短慨然的言辭,是他那一代知識分子的普遍信念。更是從歷史深處傳來的堅韌吟唱:弦誦不絕。
歷千萬劫仍弦誦不絕。
02.
千秋恥,終當雪,中興業,須人傑。——西南聯大校歌
西南聯大能有如此高度,離不開三位校長公而忘私的精誠合作。
從左至右:張伯苓、梅貽琦、蔣夢麟
北大前校長蔣夢麟回憶說:
“在戰亂中的年代,與兩所不同校風的大學及性情各異的教授合作,無異難上加難。”
但三位校長以無比高潔的品格,攻克了這個異常困難的考題。
西南聯大成立不久,南開校長張伯苓對蔣夢麟說:
"我的表,你帶(戴)着。"
這是天津俗語"你做我的代表"的意思。
但蔣夢麟轉過頭對清華校長梅貽琦說:
"三人中,你最年輕,聯大校務還請月涵先生多負責。"
此後,張伯苓去重慶開辦了南開中學。蔣夢麟長期在重慶任職,只有梅貽琦長期留於昆明,主導校務。
謙讓亦或承負,他們都只是爲了一個目的:延續中國教育的命脈。
那是他們很早就在心底萌芽,終其一生都爲之奮爭的夢。
「張伯苓」
1895年,中國在甲午之戰中慘敗。
威海衛交接那一天,以北洋水師學堂“最優等第一”的成績畢業的張伯苓,站在傷痕累累的“通濟艦”上,眼睜睜地看着戰衣不整、精神萎靡的清兵慢吞吞走出來,將黃龍旗降下;
隔一日,又看着步伐整齊、神采奕奕的英軍列隊而出,米字旗高高飄揚在我山海之上。
這羞辱讓他沒齒難忘,他在晚年回憶當時:悲憤填胸,深受刺激,念國家積弱至此,苟不自強,奚以圖存?而自強之道端在教育。
1904年10月,在他努力多年之後,南開中學初創,開學之際,張伯苓莊嚴承諾:
寧以身殉,不爲利誘,終身從事教育,不爲官。
他以一生踐行了此言。
他的付出無須贅言,因爲沒有什麼比他培養出了怎樣的學生更能證明一切:
在他經年累月“不敢作片刻停”的苦心經營下,彼時的南開成爲中國最傑出的一所私立大學,守護和滋養那麼多生動的青翠的生命:
周恩來、梅貽琦、曹禺、老舍、吳大猷、范文瀾、熊十力、陳省身、郭永懷、黃仁宇…..。
然而,1937年7月29日的那場劫難,使張伯苓數十年的心血日夜之間幾乎被夷爲平地。
時值暑假,負責留守學校的教務長拿着所有房間的鑰匙,南下找到正在廬山開會的張伯苓:
“所有的鑰匙都在這兒,但是我們的學校沒了。”
沒了的不只是他視若生命的校園。
9月份,他接到蔣介石親擬的電報:
“四子錫祜所在空軍,在江西奉命赴前線,中途失事,機毀人亡。”
他看着電報,臉漲得發紫,只是沒有流淚,沉默半晌後,對三兒子張錫祚說:
“我早就把他許給國家了,今日的事,早在意中,可惜他未能給國家立大功,這是遺憾。”
他更是把自己許給了國家。一直,一生。
「梅貽琦」
梅貽琦一生服務清華長達47年,擔任校長31年,他被稱爲:
“永遠的校長”。
但這絕不僅是因爲時間之長。
1931年梅貽琦回國在清華任職校長後,在給師生們的第一課上,他這樣說:
“我希望清華今後仍然保持它的特殊地位,不使墮落。
我希望清華在學術方面應該向高深專精的方面去做。
辦學校,特別是辦大學,應有兩種目的:一是研究學術,二是造就人才。”
也就是在這次演說中,他提出了那句你我共知共嚮往的教育箴言:
“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
這是滾熱的燙手的雄心,這是栽種,這也是育土。
西南聯大能夠創造中國教育史上用讓人景仰的奇蹟,始終秉承這一理念的梅貽琦居功奇偉。
對這段歷史,梅貽琦曾這樣說:
“在這風雨飄搖之秋,清華正好像一條船,漂流在驚濤駭浪之中,有人正趕上負駕它的責任。
此人必不應退卻,必不應畏縮,只有鼓起勇氣,堅忍前進。
雖然此時使人有長夜漫漫之感,但吾們相信,不久就要天明風定。
到那時我們把這條船好好開回清華園,到那時他才能向清華的同仁校友敢說一句‘幸告無罪’。”
幸告無罪,是多麼謙遜至極的幾個字。
梅貽琦對日寇入侵有着清醒的自覺和超前的防範措施,早自1935年始,他就把清華物資進行轉移,把一部分設備、圖書運到武漢,這批物資後來成爲西南聯大的主要家當。
在他主持聯大校務其間,他不偏不倚,堅持一碗水端平。他還把工學院清華服務社經營所得作爲額外的月薪,發給三校教員。
這種民主通達,公正無私的大家風度,從一開始就贏得了普遍的尊敬和信服,因此三校雖有競爭,但卻奇妙地融合。
有人曾精闢地說:
“關鍵在於梅校長的‘大’,他心中只有聯大,沒有清華了”。
他心裏沒有清華,更沒有他自己。
抗戰8年,物質極度匱乏。爲了籌措資金,協調各種關係,他每年必須在烽火綿延中奔走重慶幾次。
他每天步行上班,把分給他個人的汽車讓給聯大。
有一次他到成都出差,放棄搭乘飛機的便利,不辭辛勞地坐長途郵車,只爲給聯大省下200美元。
他和妻子、四個孩子住在西倉坡一幢簡陋的房子裏,白飯拌辣椒就是主食,但是當教育部捐了一筆錢給聯大學生時,他卻不允許發給同在聯大唸書的四個孩子一分錢。
1962年,梅貽琦病逝。
他死後,留下一個緊鎖的皮箱,人們打開,是一筆清清爽爽的清華庚款賬目。
他那麼窮,只留下了這麼一筆賬單,和一個清華。
「蔣夢麟」
1907年,出生在浙江餘姚一個小村莊的蔣夢麟第一次去日本,在上野公園的展覽會上,他對日本工業的發展深感震驚,但最讓他觸動的還是一個戰績博物館。
在這裏,他看到了甲午戰爭中俘獲的中國軍旗、軍服和武器,感到慚愧得無地自容。
夜間整個公園被幾萬盞點電燈照耀得如同白晝。
興高采烈的日本人提着燈籠在公園裏遊行,高呼萬歲。
他孤零零站在一個假山頂上,望着遊行的隊伍,觸景生情,不禁泫然涕下。
那時他立誓要實業救國。
1908年的夏天,蔣夢麟參加了浙江省官費留美考試,獲得錄取,前往美國加州大學農學院深造。
改變他命運抉擇的是1909年的一個清晨,那天他正預備到農場看擠牛奶,路上碰到一羣朝氣蓬勃的小孩子去上學,他追思中國曆代興衰的前因後果,忽然想到,我在這裏研究如何培育動物和植物,爲什麼不研究研究如何培育人才呢?
之後他毅然轉到社會科學院,選教育爲主科。
於是,中國多了一位傑出的校長。
1930年12月,蔣夢麟在創辦浙江大學,擔任南京國民政府首任教育部長之後,正式出任北京大學校長。
1935年日本策動“華北五省自治”,北大教授發表宣言,聲明誓死反對。
一個日本憲兵到北大找到他,“請”他到日本在東交民巷的兵營,天黑以前,他隻身前往。
日本大佐脅迫他讓北大放棄抗日宣傳,並提出要把他送到大連。
他斷然拒絕。
拒絕的結果是,如上所言,日本兵對北大校園的百般蹂躪。
在北大被佔領後,蔣夢麟回家鄉告別老父,他不知何日再能見到老人家,只是在臨別和父親鄭重說:
“中國將在火光血海中獲得新生。”
老父聞之目光炯炯。
蔣父在送走了兒子後,退避深山,茲後,在對兒子和勝利的盼望中辭世。
這是那一代學人父子共同的,無可迴避的命運。
03.
違千夫之諾諾,作一士之諤諤。——馮友蘭
西南聯大是中國的羣星閃耀之地。
聞一多、朱自清、吳宓、鄭振鐸、金嶽霖、吳大猷、吳有訓、曾昭掄、葉企孫、趙忠堯、周培源、華羅庚等等都曾在這裏留下身影足跡。
他們中任何一個人都足以彪炳千秋,篇幅所限,我們不能一一細敘,僅在此重溫兩名教授些許事蹟,我想在他們,亦能充分體現聯大之獨特之精神。
他們,一位以才學以狂傲頗負盛名,但最終被聯大開除;
另一位,則被稱爲:教授中的教授。
「劉文典」
西南聯大的《文選》課上,名教授劉文典如常走進教室,剛剛開課半小時,他突然就福至心靈一樣,神祕兮兮地告訴學生,提前下課,改在下星期三晚七點半再上。
一臉懵逼的年輕人圍坐在青草地上,如水月光安靜地灑在他們身上,等劉文典打開書,一字一句開始讀《月賦》,學子們才恍然明白劉文典的用意,這一天是農曆五月十五。
講課乘興而至,別開生面,是劉文典的拿手菜。
但最爲世人所知的,是他的狂傲,不一般的傲。
1928年,劉文典在安徽大學主持校務,剛掌握大權不久的蔣介石多次想去安徽大學視察,但領導的厚愛非但沒讓劉文典倍感榮光,他還多次硬生生地拒絕。
蔣介石覺得面子無光,繼續堅持,最後終於出現在安徽大學校園裏。
可是安徽大學還是給了他個沒面子,校園裏冷冷清清,壓根沒有那種隆重熱烈,夾道歡呼的場景。
這是因爲劉文典事先已放言:“大學不是衙門”。
學校掌門人都如此牛掰,學生們自然也樂得跟着傲嬌一把。
後來安徽大學學生鬧學潮,蔣介石問責劉文典。
對話中,劉文典對蔣介石只稱“先生”,而不肯稱“主席”,蔣很是惱火,衝突激烈時,劉文典甚至指着蔣介石罵:“你就是軍閥”。
他不僅傲,也決絕。
“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對中國步步緊逼,劉文典認爲必須對日本有深刻認知,方能給予它致命打擊。
他爲此夜以繼日地翻譯日本相關資料,有時甚至通宵達旦,以至第二天上課時嗓子都啞得幾乎說不出話來。
但他的親弟弟劉蘊六不同,七七事變後劉蘊六在冀東日僞政府謀到一個肥缺,喫飯時還向劉文典炫耀。
劉文典當即大怒,摔掉筷子說:“我有病,不與管廷同餐”;
又鄭重說:“新貴往來雜杳無不利於著書,管廷自今日始另擇新居”,毅然將與他相依爲命多年的弟弟逐出家門。
他也有自己的深情和謙恭。
1938年5月22日,劉文典到達蒙自——西南聯大文學院所在地。
他一路顛沛流離,早已衣衫襤褸,拄着棍子,如流浪乞丐一般,可當他抬眼看到風中飄揚的國旗,立馬肅立,整理衣衫,向國旗鄭重三鞠躬。
等他禮畢抬頭,已滿臉是淚。
西南聯大常常遭日寇炮轟,在一次襲擊中,師生們都急忙四處躲避,劉文典跑到半途,路遇沈從文,他竟然對沈從文說:
“你跑什麼?我跑,是因爲我炸死了,就不再有人能講《莊子》了。”
劉文典這番話固然傲慢無禮,但是亦有他的底氣在,彼時,乃至今日,在國學造詣上能和他比肩的的確無幾。
但是,最終,他卻被是唯一一位被聯大開除的教授。
1931年,劉文典長子去世後,染上鴉片煙癮,但囊中羞澀,1943年曾在雲南磨黑逗留過數月,給當地大鹽商張孟希講學,寫墓誌銘。張孟希則供應他充裕衣食以及上好煙土。
西南聯大得悉此事後,覺得劉文典此行實在有損師德,最終將他解聘。
此後,一代國學大師離開了中原的文化中心地帶,蟄居雲南,人物風采亦自此悄然中滅。
也曾有人覺得劉文典被解聘着實可惜,但西南聯大不顧劉文典的學識名望,依然做出此舉,也着實昭顯了一座名校應有的清潔和尊嚴,和它不爲任何人動搖的原則。
在那次跑空襲中,劉文典在對沈從文嘲諷的同時,卻又要竭力保護另一個人:陳寅恪。
陳寅恪眼睛不好,劉文典生怕他有所閃失,他一邊攙扶着陳寅恪跑,一邊高喊:
“保護國粹要緊,保護國粹要緊”。
劉文典恃才傲物,能入他法眼的沒幾個人,但他在陳寅恪面前,總如小迷弟一般。
他曾認真地說,對陳先生人格學問,不是萬分敬佩,是十二萬分地敬佩。
的確,陳寅恪先生,他值得,十二萬分的敬佩。
「陳寅恪」
1939年,陳寅恪從香港輾轉到達昆明,雙眼已幾近失明的他又出現在講堂上。
他先在黑板上寫好重點,然後坐在椅子上,閉着眼睛開始講。有時他也讓學生讀文章,他們讀錯一個字都逃不過他的耳朵,那些典籍就像長在他心上。
學生們卻不驚訝,他們早已聞得他大名。
1926年,36歲的陳寅恪成爲清華國學研究院的導師,彼時的他一無學位二無著作,但很快人人都驚歎他的博學和識見,人們叫他:教授中的教授。
他當之無愧。
陳寅恪學貫中西,通曉十四國語言,包括全世界都沒幾個人精通的巴利文,突厥文,梵文,以及匈牙利的馬紮兒文。
他上課,一開始慕名而來的人非常多,後來因爲聽不懂,人越來越少,但即使只有一個人聽課,他都一樣的認真,一樣的熱忱。
有人說“他對教書這件事有宗教般的虔誠和儀式感”。
可這背後是他每天都在昏暗的燈光下伏案到深夜,即使在他右眼視網膜脫落致盲,左眼也只剩微弱視力的情況下,他也沒有一天不在堅持備課和寫作。
他的眼病真的是累出來的。
也不只是累。
牛津大學曾屢次邀請他做漢學教授,陳寅恪屢次拒絕。他不去,牛津大學就虛位以待。
1939年,陳寅恪考慮到可到英國醫治眼疾,才準備接受這一教職。但這時,歐洲戰火亦起,在他行至香港後不久,此地就落於日本人之手。
流落在香港的日子過得非常清苦,他的一個朋友說,有一次去看陳寅恪,才知道他已經捱餓兩三天了。
其實也可以不那麼苦,日本佔領軍司令常派憲兵往他家裏送食物,可憲兵往屋裏搬,陳寅恪和妻子就往外拖。
這樣做的結果是他的身體每況愈下,鄧廣銘有次去看他,他躺在牀上呻吟,說我堅持不住了。可又說,我不能死,寫不完這書稿,我不能死。
1944年12月12日,陳寅恪心心念唸的書稿《元白詩箋證稿》也終於完成,可也就在這一天,他發現自己徹底失明瞭。這時他想到的第一件事,是讓大女兒流求通知學生,今天上不了課了。
女作家張曼菱曾這樣寫到:“當蒙自南湖的荷花綻放,孤身的患着眼疾的陳寅恪就住在湖畔樓上。……
我常常琢磨他那種‘天下無路’的感覺,感到一種寒夜的淒涼,和蒲草磐石的堅韌。無路也是路。”
無路也是路。
即使在二十多年後的大風暴中,他飽受凌辱摧殘,即使他癱瘓在牀了,即使他只能沉默,這位扶杖的眼盲學者的身影,亦有一種神聖的、必須敬畏的力量。
正如張曼菱所言:他是西南聯大一個靈魂型的人物。
有他在,就有一份家國的分量,一份歷史的分量。
有他在,就無路也是路。
04.
“便一成三戶,壯懷難折。多難殷憂新國運,動心忍性希前哲。待驅除仇寇,復神京,還燕碣。”——西南聯大校歌
我們景仰西南聯大,因爲它難以逾越的成就,亦是因爲這樣的成就,湧現於我們難以想象的艱難境況中。
今日雲南師大的校園,保留着一間陳舊的聯大教室,低矮泥黃的土牆,鐵皮的屋頂。
下雨時,雨聲叮叮噹噹敲在屋頂上,讓人無法講課,一位老師曾在黑板上無奈寫下:
“現在停課賞雨”。
電影《無問西東》中“停課賞雨”場景
這樣最簡陋不過的大學校舍,卻是出自大家之手。
初到昆時明,聯大隻能靠租借民房。
梅貽琦請梁思成、林徽因夫婦設計校舍,但在此後兩個月的時間裏,梅校長卻又一遍遍否定了他們的心血之作。
在改到第五遍時,梁思成忍無可忍:
“改!改!改!還要我怎麼改?!茅草房?不是每一個農民都會蓋嗎,要我梁思成幹什麼?!”
梅貽琦其實比梁思成更無奈,但他只能懇切地對這位著名建築學家說:
“大家都在共赴國難,思成,以你的大度,最後諒解我們一次,行嗎?”
半年之後,一座座茅草房坐落在了西南聯大的校園。
有個廣爲人知的故事:教授們走在路上,遇到乞丐,只要說:“我是教授。”
乞丐聞聲便走,連他們也知道,教授們窮得叮噹響。
這絕非誇張。
爲了生存,教授們不得不各展其能,賣衣、賣印、賣字賣畫,聞一多日夜治印,手上全是老繭傷痕。
聞一多治印
爲了生存。吳有訓太太熬夜刺繡,物理教授趙忠堯在汽油桶裏自己燒製肥皂。
即使是校長梅貽琦的日子也非常艱難,他的夫人韓詠華曾回憶,有一次家裏沒錢招待客人,她只得趕緊跑到街上,鋪上油布擺地攤,把孩子不穿的衣服賣掉。
梅夫人還和潘光旦、袁復禮兩教授的夫人一道做糕點賣,取名“定勝糕”。
但最讓人唏噓感動的並不是他們的艱辛,而是,當教育部聞知他們的困境後,勉力拿出一筆錢要補助教師們。
西南聯大爲此專門召開會議,最終的決定是:所有的教師聯名拒絕救濟。
這一次,他們的話沒那麼有文采,只是簡單說:
“在全民族都爲抗戰付出了巨大犧牲的情況下,在大後方還有許多的人民生活比我們還要艱難;
面對中國的百姓,我們還有什麼理由接受政府的補助呢?還是讓這些補助用於抗戰吧。”
05.
自由的大地是該用,血來灌溉的。——繆弘
在今日雲南師大的校園內有座“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紀念碑”的背面,鐫刻着1946年5月4日立碑時所能收集到的832位從軍學生不完整名單。
由於當時條件所限,長沙臨時大學時期295人從軍學子絕大多數未列入。
兩者相加共有1100多人,從軍人數比例高達14%。
這裏面有“世界光導纖維之父”的黃宏嘉,有著名翻譯家許淵衝…..
是的,還有寫下著名詩篇《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的穆旦。
穆旦
1942年2月,身爲西南聯大外文系青年教師的穆旦參加了中國遠征軍,任司令部(杜聿明將軍)隨軍翻譯。
4月底至5月,力戰不敵的遠征軍陸續退卻,一部分退往滇西與日軍隔怒汀對峙,一部分撤往印度。
在日本人的窮追中,23歲的穆旦和他的戰友們穿越了野人山。
杜聿明在回憶錄中說:
“原始森林內潮溼特甚,螞蟥、大得可怕的蚊蟲以及幹奇百怪的小巴蟲到處皆是,螞蟥叮咬.破傷風病隨之而來,瘧疾、迴歸熱及其他傳染病也大爲流行”。
一個發高燒的人一經昏迷不醒,加上螞蟥吸血,螞蟻啃齧,大雨侵蝕沖洗,數小時內即變爲白骨。
官兵死傷累累,前後相繼,沿途白骨遍野,令人觸目驚心。
但文字還是很難形容出這座莽莽叢林的全部恐怖,在過野人山時穆旦的馬倒了地,傳令兵死了。
他的腿腫了,還得了致命性的痢疾,有一次斷糧達八天之久,他還是活過來了,
那段讓人發瘋的經歷,穆旦幾乎從不願提起,王佐良說:
“只有一次,被朋友們逼得沒有辦法了,他才說了一點。
而就是那次.他也只說到他對於大地的懼怕,原始的雨,森林裏奇異的,看了使人害病的草木怒長,而在繁茂的綠葉之間卻是那些走在他前面的人的腐爛的屍身,也許就是他的朋友們。”
“不知多少天。他給死去戰友的直瞪的眼睛追趕着。”
吳宓在日記中寫到:“錚述從軍的見聞經歷之詳情驚心動魄,可泣可歌。不及論述……”
可泣可歌的人和事,那麼多。
1942年,吳宓教授在日記中還寫到:
“黃維隨軍退歸。六月十五日,在車裏渡瀾滄江,……維與馬俱墮水中。及馬救出,而維已被急流裹去,渺無形跡矣!聞耗,深爲傷痛。”
黃維是吳宓一向極喜愛的學生,1941年應徵時他是外文系四年級的學生,也是聯大學生社團“石社”的核心人物。
他本可以去條件較好的“飛虎隊”,但他放棄了,選擇了兇險未知的緬甸遠征。
繆弘,1943年入學。在聯大五次輸血後,他寫過一首詩:
沒有足夠的糧食,且拿我們的鮮血去;沒有熱情的安慰,且拿我們的熱血去;熱血,是我們一的剩餘。…….自由的大地是該用血來灌溉的。/你,我,/誰都不勞忘記。
1944年他隨美軍和中國鴻翔部隊空降到敵後作戰,反攻桂林時,他奮勇衝鋒直至犧牲,那一年,他還不滿19歲。
這些全國最優秀的學子,都以自己的熱血、澆灌了這片苦難破碎的土地。
靜靜的,在那被遺忘的山坡上, 還下着密雨,還吹着細風, 沒有人知道歷史曾在此走過, 留下了英靈化入樹幹而滋生。
他們,已靜默無聲,與這蔥蘢草木同呼同吸,我們亦該勿失勿忘。
06.
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曆千萬祀,與天壤而同火,共三光而永光。 ——陳寅恪
今日,我們爲什麼要對西南聯大屢屢回望?
不,不只是景仰並要銘記它的榮耀和苦難,更絕非是懷戀亦或謳歌那個時代。
我們深知,那是一個埋藏巨大悲傷的時代,風雨如晦,山河破碎,那個時代的學子們,在戰亂紛爭在顛沛流離中,常常連一張安靜的書桌都放不下。
是因爲,正是在這樣的動盪苦痛中,凸顯的那些先生們、學子們的意義和價值。
他們心境澄澈,堅守了這個民族的文化與風骨。
他們的精神,他們的理想和人格,更猶如燈塔,燃亮了破碎山河,和這個民族蒼涼又年輕的心靈。
不,也不僅僅是這些,還有那些實實在在的。
比如,李四光的女婿鄒承魯院士說:
“西南聯大的傳統就是:
越是普通的課,越是有名的大師教。
系主任就教普通化學。我上普通物理課,是吳有訓教;微積分課,是楊武之教。”
比如,汪曾祺回憶:
“聯大教授講課從來無人干涉,想講什麼就講什麼,想怎麼講就怎麼講。”
聞一多
金嶽霖
比如,當代作家,寫下《西南聯大行思錄》的張曼菱說:
“由於師資充裕,常常幾位教授同時開講一門課程,如一年級國文課,全校共同必修。
講課的教師中有李廣田、沈從文、餘冠英等十來位教師,講授各有特色,風格觀點紛呈,師承流派各異。”
比如,著名物理學家李政道曾對張曼菱說過:西南聯大的學生,不是一個模子出來。
也許一切都不必過多述說,你和我,多少還是承認:
它是昔日教育之榮光,亦爲當今中國教育立鏡。
無論何夕何年,都值得我們一唱再唱。
✒️
作者:樊曉敏
圖片: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