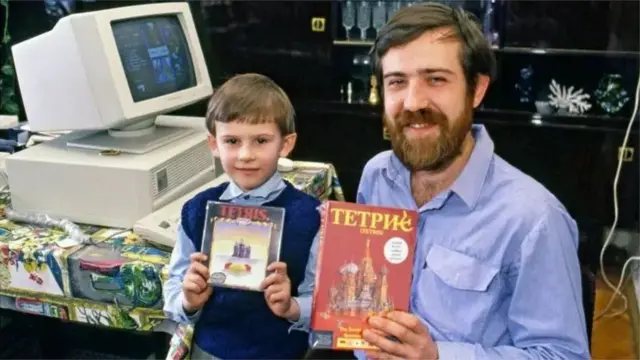富金山戰役背景下,祖父母的民國二十七年:父親差點死在了廟裏
(一)
四十一年前那個冷得連狗都不敢出門的冬天,已經雙目失明的七十八歲祖父告訴我:你老叔(我們兄妹稱父親爲老叔)民國二十七年差點死在了廟裏……
突兀的聲音像門口池塘的冰突然裂開一樣,讓我再一次毫無徵兆地跌進了冰窟裏。彼時,因爲“滑冰”,我穿着破狗套子(棉衣,無袖),意外地扎進了裂開的冰面內。幸虧被恰好路過的母親從水裏拎出來,扒掉衣服,痛毆一頓後,命令我裹一牀破被子——那會可沒有多餘的棉衣——坐在火塘邊一邊烤火取暖,一邊烘烤衣服。
火塘裏,一塊乾枯的大樹根子默默燃燒,慢條斯理地冒着青煙。
什麼時候?我吸了吸鼻涕,盯着祖父那雙火塘裏留存的細灰一樣顏色的眼珠子,驚愕地張大了嘴巴。
民國二十七年。瀰漫的青煙裏,祖父爛桃子紅的眼皮子連眨了幾下。
民國二十七年是哪一年?我裹緊被子,往祖父那邊湊了湊,生怕漏掉一個字。
呃……這個……祖父一時語塞。
好一會,祖父解釋說:民國二十七年就是民國有二十七年了,離現在四十整年。
對於祖父的解釋,我並不滿意。多年後想想,讓一個不識字的垂暮老人解釋清楚民國多少年是多少年,確實荒唐可笑。
再問,祖父雷似的呼嚕聲響了起來。一縷又一縷的青煙被吹得一個趔趄接一個趔趄,斜斜歪歪地奔着裂開嘴的牆縫,閃身鑽出去,消失在屋外凜冽的寒風裏。
幾天後,我又裹着被子坐在火塘邊的祖父的面前。這一次,更慘,大便時,腳一滑,仰面跌進了茅坑裏。
我聽到你哭了,又捱打了。洋蛋(方言,調皮,頑劣之意)了吧?祖父長嘆一聲,身子前傾,樹皮一樣粗糙的雙手攤開,伸在火籠上方,時不時搓幾下,細灰一樣顏色的眼珠子盯着我坐的方向。他的手摸索着探過來,試圖找到我的頭,安慰一下,我偏了偏頭,躲開了。
爺爺,你上次說民國二十七年俺老叔差點死掉是怎麼回事啊?你要告訴我,我的頭就讓你摸。我和爺爺講條件。
好,我給你講。祖父咧嘴,掉光了牙齒的嘴像個黑乎乎的洞。
我抓過祖父的手,放到自己頭上。祖父摸了頭,摸了臉,又摸了耳朵。然後又長嘆一聲:民國二十七年我和你奶奶把你老叔放進廟裏,後來和尚死了,你老叔差點也死了……
怎麼回事?那時俺老叔多大?我截斷祖父囉裏囉嗦的敘述,急不可耐地想滿足好奇心。
一百零五天還是一百零六天?祖父費力地抬起頭,眼珠子空洞地對着他看不見的黑黢黢的房頂。我順眼望去,燻黑的椽梁在青煙裏隱約泛着油膩膩的白光。
唉,老了,記不清楚了。反正是跑老日的時候,把你老叔放在廟裏頭,我挑着你大伯,帶着你奶,往山裏跑……
祖父的聲音含糊而微弱。
和孫子講這些幹啥?!你老糊塗了吧?蹣跚着小腳的祖母不知道什麼時候悄無聲息地走了進來,厲聲喝住了祖父。
祖母強勢,從來說一不二,祖父立刻閉了嘴。
再問,已沒了回答。呼嚕聲雷一樣在耳畔炸起。
匆忙穿上已烤乾的棉褲、狗套,晃了晃祖父的肩膀,呼嚕聲絲毫不見衰減。
我惱怒地跑出去,拿着竹竿,用力一揮,攔腰斬斷屋檐下長長的冰溜溜。它們死死地拽着一把把發黑的稻草,噗嗤噗嗤地落地,粉身碎骨。
後來多次纏着詢問,彷彿是一塊深及心靈的的傷疤,祖父諱莫如深,再不肯透露一字。
兩年後,八十歲的祖父緊隨八十歲的祖母,溘然長逝。
而關於父親被送進廟裏差點喪命的隱祕,如火塘裏不斷升起的青煙,刺激着眼耳鼻舌的同時,也在幼小的腦子裏留下了揮之不去的謎團……
(二)
謎團徹底解開,已是十年之後。
當我第一次接觸富金山戰役的文字資料時,多年前祖父口中的幾個關鍵詞,連同後來親戚鄉鄰零散的回憶片段,特別是比祖父小十幾歲的本家八爺講述,讓我窺到了特定歷史年代普通百姓如飄蓬一樣的殘酷命運。
去年九月的一個黃昏,我沿着山北的一條棱線再登富金山。
四周很靜,肅穆的氛圍一如穹頂,嚴嚴實實地罩在這座曾經流彈如雨、血流成河的山體;密實的樹林紋絲不動,隱隱泛着殺氣,彷彿正待衝鋒號響的剎那便躍出掩體,和入侵的敵寇搏命;三十年前尚能依稀辨認的戰壕溝塹,已被無情的風雨和孤寂的時間無聲抹平,荒草和灌木瘋長,滿天滿地都是急不可耐的蔥蘢,似乎要把遙遠的真實強行擠出記憶的硬盤;登上山頂,眺望西南,暮雲熔金,殘陽似血,一縷縷,從長空深處密集地斜射,如曳光的槍彈傾瀉,雄渾邈遠的蒼勁讓人顫慄;沒有常見的裸露巉巖,八十年前的遮天炮火,早已把它們炸成了齏粉,翻滾,攪拌,飛揚,成爲滾燙的炮灰,和着肉血、憤怒、吶喊,凝成英雄的底色……
民國二十七年九月,即公元一九三八年九月二日至十一日,國民革命軍第七十一軍軍長宋希濂,率軍在河南固始東南陳淋子鎮富金山地區,搏命血戰,以所部幾乎傷亡殆盡的代價,擊斃擊傷日軍一萬四千餘人,遲滯敵人十日。爲國民政府組織武漢會戰贏得了寶貴時間……
祖父母逃難時棄父親於小廟,便發生在這一歷史背景下。
(三)
民國二十七年,祖父住在只有十幾戶人家的祖師廟店子街上。一條土路穿街而過。
當時,這條土路是連通武漢和合肥的重要通道。在高速公路尚未四通八達的上世紀九十年代,它依然車流滾滾,塵土飛揚,依然是連接華東和中南的重要通道。沒有考證它開鑿的具體年代,只知道這條簡易的土路,穿谷越關,貫溪通河,斗折蛇行,於綠樹草莽荊榛之間艱難地向前延伸。形成了一方簡陋而闊大的舞臺,上演着千奇百怪的傳說和荒誕不經的故事。政客、商賈、小販、村夫、流民、乞丐、土匪、痞子各色人等麇集,荒誕的、悲慘的、殺人的、越貨的、鬥狠的、體面的、狼狽的、微笑的、啜泣的……未等對方唱罷,另一波強行登臺。江湖恩怨,快意情仇,刀光劍戟,血肉橫飛。一折折眼花繚亂的皮影戲,在那個特殊的動亂年代,不斷熱鬧地開啓,上演,謝幕。
祖父呢,就是這個舞臺上不知名的小角色。他像一餅陀螺,在生活的皮鞭——皮鞭尖上沾了水——兇狠抽打下,滴溜溜地在坎坷不平的泥地上竭盡全力地轉。不敢放鬆,也不敢懈怠,更不敢硬槓,對誰都笑臉相迎,哪怕被欺負得鼻青臉腫,遍體鱗傷——像當時的大多數老百姓一樣。老祖先基因遺傳的血性,被嚴酷的時代榨取得只剩下些許緋紅的痕跡。
沒田沒地的祖父死死地摽着這路,把它當作田地,把自己當作牛馬,套上生活的犁耙,繩索勒進骨頭裏,下死力氣拉,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在離家不遠的山坡山腳下,在穿街而過的羊行河邊的灘塗上,祖父砍藜棘,搬石塊,撿卵石,除沙礫,拾豬糞牛糞羊糞,挑來一擔擔黃土,覆蓋,發酵,過一段時間,瘦得嶙峋的地兒就豐滿起來,黑油油軟乎乎地嬉笑着,溫情地等待西瓜、綠豆、紅薯和芝麻的光臨。雖沒法和大地主李庚堂的山珍海味相比,但坐在盛夏的樹蔭下喫西瓜,蹲在黃昏的街頭喝綠豆稀飯,靠在火塘邊喫烤紅薯的感覺卻讓祖父的臉上洋溢着滿足。當然,這只是副業,主業則是掛掛麪、磨豆腐、炸油條。多年後,還有老人對祖父的手藝讚不絕口。八爺就曾對我說,早晨喫上你老爺炸的焦黃噴香的油果子(油條),配上一碗澆上佐料的豆腐腦,一天都舒舒坦坦的。曾見過繼承了祖父手藝的大伯掛掛麪的情景,那些灰撲撲的麥面,經過和麪、盤條、上筷、上架、下拉、晾曬、收扎等多道工序,變成纖細如發的掛麪,在冬天的陽光下格外醒目……
憑着勤勞和手藝,祖父蓋起了幾間簡陋的草房,娶了祖母,支起了門頭,並有了大伯。除了老搶(土匪)偶爾光顧騷擾(喝幾碗放糖的豆腐腦,並沒什麼值錢的入老搶的法眼)外,日子還算相對平靜。
(四)
民國二十六年冬天,日本人打下南京後,姦淫殺掠無惡不作的傳聞越來越多。祖父母開始還有點不以爲然,認爲日本人也是人,不是畜生,是人就會有人性,不會對手無寸鐵的老百姓怎麼樣。直到給老搶作眼線的本家八爺從南京跳江逃生,僥倖逃回祖師老家,語無倫次地講述自己如何從死人堆裏爬出來及日本人的種種殘暴行徑時,祖父母才感到脊背嗖嗖發涼。此時,祖母已懷了父親幾個月了。
惴惴不安地過了幾個月,農曆四月十七(陽曆五月十六),父親出生。後來,每天都有不同的壞消息傳來。祖母擔憂驚嚇,精神極度緊張,很快沒了奶水。喫不到奶水,等於掐掉了父親的口糧。祖父想盡了辦法也沒效果。只能熬米湯油一勺一勺地餵給父親喫。米湯油哪有奶水管餓?父親因此整宿不停地哭鬧。這使得祖母整夜整夜睡不好覺,情緒低落,鬱悶焦躁,竟產生了溺死父親的可怕念頭。今天看來,倒不能說祖母狠心,而是她可能患了嚴重的產後憂鬱症。
八爺說,那年閏七月,閏七月的年份都不好。有一天,保長通知說,畜生養的日本鬼子要過來了。這幫王八日的要打武漢。俺們的政府正調兵抵抗。但鬼子的槍炮厲害,估計打不贏。萬一俺們的軍隊擋不住,這些畜生們就要往西打,祖師街是必經之路。爲防萬一,要把能帶走的東西都帶走,帶不走的埋起來。不能把有用的東西留給那幫狗孃養的!各家要提前準備,畜生一來,趕快跑到山裏藏起來,藏得遠遠的,讓王八日的日本人找不着!等那些天殺的畜生走了咱們再回來,照樣種田、耕地、做生意!
恐慌的氛圍瘟疫一樣蔓延,家家戶戶開始找地兒埋東西。在祖母的要求下,祖父把凡是帶不走的,能埋的都埋了起來。只是那口磨豆腐的大鍋讓祖父犯了難,因爲砌在了灰磚裏,要拿出來埋,得把灰磚拆掉。祖母捨不得,自我安慰說,日本鬼子不會把鍋怎麼樣的,就擱那,不埋了。
然後祖父母開始連夜炒大米、黃豆、麪粉,分別灌進粗布口袋,紮緊,碼進稻籃。一鍋又一鍋。祖母坐在竈洞前,添着柴,淚水混着汗水。那一刻,秋意剛至,祖母卻渾身瑟縮……
(五)
八爺跟我說,打仗前兩天,廟店子街過隊伍,整整過了一夜。他從門縫偷看,黑壓壓的隊伍,不見頭,也不見尾,長江水一樣,一浪跟着一浪,撲着向東行進。那些人的眼睛和背在背上的槍支,隱隱閃着天上星子一樣的寒光。
八爺說,那天的天很怪,挨黑時,日頭像個得了癆的病人,噗嗤噗嗤吐了血,半個天都是紅的,血絲子一直掛到葉集那邊。
祖父母得到的確切消息說,日本鬼子已經佔領二十里外的葉集了,再不跑就跑不掉了。祖母慌忙把熬好的一小罐米湯油封好,放進一隻稻籃裏,用裝炒麪的口袋把它圍嚴實,防止歪斜傾倒。給父親熬米湯油用的小砂鍋,祖父本來是要拴在腰間的,那樣保險些。但祖母反對,理由是掛在身上晃來晃去,一不留神就會碰破。一番小小的爭執後,小砂鍋被強行拴在了稻籃的繩子上——事後證明,這是一個致命的錯誤。這個錯誤差點導致我們的名字不能在家譜上出現。當然,這是後話。
五歲的大伯被放進另一隻稻籃裏,爲了平衡,在大伯的身下也放了不少炒米口袋。於是,祖父挑着稻籃,祖母則抱着一百零六天的父親,戀戀不捨地離開自己燕子啄泥般壘起的巢,開始倉皇出逃——就是祖父母口中的跑老日——這是民國二十七年九月二日凌晨。
墨一樣的夜色吞沒了一切,瘮得讓人心裏發慌。祖父母們彷彿跌進了無邊無際的死亡之海,哭號、掙扎、呵斥、詛咒。求生的本能驅使他們拼命地朝西南方向的奶奶殿、鮑嶺灣、鐵衝、龍井衝方向奔去。
小腳的祖母,平時走路就相當費力。加之山路陡峭、狹窄溼滑,還要喂似乎永遠喫不飽的父親,只能走走,停停,歇歇,行進得極其緩慢。天亮時,一起出逃的鄉鄰早已看不到蹤影了,而祖父母剛走到奶奶殿的山腳下。
密集的槍炮聲在山那邊驟然響起。祖母顫慄着,哆哆嗦嗦地催促祖父快走。她抱着父親,抓住祖父的一隻稻籃,亦步亦趨地跟着。顧不得父親哭啞了嗓子,顧不得大伯的嗷嗷慘叫,蹣跚,趔趄,薅茅草,拽藤條,蹬石頭,跌倒,爬起,手腳並用,一身泥水,滿臉淚痕,拼命地往前爬。不知多長時間過去了,抬頭一看,還不到半山腰。他們心中的安全地兒,還橫亙着一座高高的奶奶殿山。
站在山腰,可以清晰地看到東面富金山有密集的柱狀煙霧升起,接着傳來了轟隆轟隆的炮聲,炮聲中夾雜着隱約的吶喊聲。不多時,一架又一架飛機鷂鷹一樣躥過來,從頭頂掠過。祖母既驚恐害怕,又勞累飢渴,幾乎癱倒在地,無法前行一步。祖父雖然也十分害怕,但還沒有慌亂,每走一段,就把稻籃放下,再回來背祖母,就這樣一步步往前挪。
這時,意外發生了。
當時,黑壓壓的飛機嗡地一下從頭頂的天空掠過,氣浪衝擊下的樹林發出恐怖的嗚嗚聲。祖母渾身戰慄,失聲尖叫,差點扔掉了懷裏的父親。祖父被祖母的尖叫嚇得一激靈,放下擔子就往回跑。驚慌之下,一隻稻籃沒放穩,骨碌骨碌往懸崖下滾,東西散落一地。要命的是,那個系在稻籃邊上的砂鍋被壓碎了,裝着米湯油的罐子也滾下了懸崖。更要命的是,大伯坐的另一隻稻籃也被拽倒,同時向懸崖滾去。眼看就要掉進深澗,幸而被一叢灌木擋住。懸崖邊上的大伯大哭大叫,半截身子從稻籃裏探出來,搖晃着雙手伸向祖父。
稻籃不停地晃動,下面就是萬丈深淵,大伯命懸一線。祖父臉色煞白,他輕聲安撫着,慢慢挪動腳步,靠近後,猛撲過去,一把把大伯從懸崖邊上的稻籃裏抱了出來,癱坐在地上。
大伯從死亡線上被拽了回來。可是本該哭鬧的父親卻顯得異常安靜。剛纔一路一直在哭鬧,因爲要逃命,祖父母都沒有注意父親的變化。顯然,他餓昏死過去了。需要喂米湯油,否則,就會死掉。但是砂鍋碎了,米湯油灑了,拿什麼喂他?
祖父安頓好祖母和大伯後坐在地上,思忖了會對祖母說,你先在這等着,我回去再找個砂鍋,我腳大,跑得快,一會就回來了。
祖母指了指山下:你看,回去不是送死嗎?
祖父向山下看去,小街已籠罩在滾滾濃煙中,顯然,街道上已有了鬼子,他們開始燒房子了。
富金山的槍炮聲越發激烈,轟隆的炮聲地動山搖。父親此時已哭啞了嗓子。祖父抱着一動不動的父親,束手無策。
我們走吧,到龍井衝,找到住家戶,再熬米湯喂他。祖父說。
那邊都是深山老林,哪裏有人家?祖母大聲地反問。
祖父呆坐,默不作聲。他曾多次去過那裏,走半天也碰不到一個人。
你看看,他已經昏過去了。還有這麼遠的路……
那你說怎麼辦?祖父無奈。
把他放在這吧,生死由命吧。祖母看着父親。
不!他是條命!是你兒子!祖父大聲叫起來。
那你說怎麼辦?要不咱全家都死在這?祖母逼問。
祖父緊緊地抱着父親,彷彿寶貝要弄丟似的。
這孩子是我身上掉下的肉,我不心疼嗎?你看看,剛纔差點把大的也弄死了。現在小的沒喫沒喝的,還有這麼遠的路要走,我們帶着他,也只能眼睜睜看着他死掉。他不能喫炒黃豆、炒麪粉、炒火米茶吧?也不能喝這山裏的涼水吧?眼看着死在懷裏,不如放在這裏……祖母冷靜地說。
又有飛機鷂鷹一樣躥來,東面的炮聲愈發激烈。
祖父緊緊抱着父親胡亂轉着圈,突然,他眼睛一亮,指着相鄰小山上的一座小破廟,語無倫次地對祖母說:那兒!煙!廟!和尚!快……
祖母也看到了,趕緊遞上一帶炒米和炒麪,狠狠地推了祖父一下:快去!
八爺調侃地對我說,就是那座廟,那裏的和尚救了你老叔。你老叔要是死了,你們兄妹到現在還不知在哪個田溝下扒着呢。
聽八爺說,當祖父衝進廟裏時,和尚正在燒水,祖父把父親往和尚懷裏一塞,拿出炒麪袋,往鍋裏撲撲地一通倒,然後,把目瞪口呆的和尚擠出了破竈房……
喝了麪糊糊,父親慢慢緩了過來。
後來,祖母覺得這裏離街太近,說不定鬼子會摸上來,堅持要往山裏去。祖父拗不過,只得留下一些炒米和炒麪,把父親託付給了那個我們永遠也無法知道名字的和尚照顧。
第五天,祖父抽身去破廟看了看,父親正發高燒,滿臉通紅地昏睡。當祖父轉身向外衝,準備給父親弄藥的時候,恰巧和回來的和尚撞在了一起。
孩子燒得厲害,我到彭家畈撿藥去了。和尚淡淡地說。
那多兇險!街上有鬼子!我去吧。爺爺急忙說。
沒事,我熟悉路,我知道怎麼走。你不用擔心,好好照顧妻兒吧。
第九天,富金山的槍炮聲減弱了,藏身在龍井衝的祖父不放心,隻身跑到破廟,沒進門,老遠就聞到一股腥味。祖父雙腿發軟,踉蹌地撞開柴門,黑霧似的綠頭蒼蠅倉皇地向祖父臉上撞來。
和尚倒在地上,身中兩槍,流了一地的血已成黑色。他的一隻手放在父親的腳上,另一隻耷拉在破凳子上。上面的粗海碗斜着,黑色的藥汁殘留早已凝固,半碗麪糊糊爬滿了蒼蠅。
父親奄奄一息,手指頭被吮吸得蒼白。
八爺說,和尚大概是下山撿藥回來,被日本鬼子打中了兩槍,他忍痛跑回廟裏,給你老叔餵了藥餵了麪糊糊後,血流多了,後來就死了。
……
第十一天,日本鬼子向西去了,祖父和鄉鄰們陸續回家。小街上的房子無一例外地燒光了,斷壁殘垣,滿目淒涼。
回到被燒光的家門口,奇臭味迎面撲來。
進屋一看,豆腐鍋砸了,裏面拉滿了大便。
天殺的日本鬼子啊!祖母的尖叫在小街上空淒厲。
過了幾天,識字不多的祖母重新給父親取了個大名,又取了個小名。
大名有個山字,小名帶個和字。
八爺說,那座山,那個不知名的和尚,讓祖母惦記了一輩子。每月初一、十五,祖母必定走到村前的那個十字路口,面向西南燒兩炷香。
對祖父母一家和鄉鄰們來說,民國二十七年是個劫。幸運的是,他們都在這場劫難中活了下來。他們的後人,一代代生息、繁衍。像繁茂的樹枝,蓬蓬勃勃地四散開來,活得灑脫、美好、幸福。而那些眼睛亮得如星子的青年人,鮮血流盡,倒在了異鄉的富金山上……
幸福地活着,便是對犧牲者的最好告慰。
作者簡介:遊宇,生於上世紀六十年代末,中學語文高級教師。現供職於固始縣國機勵志學校。出版文集《那一場青春的邂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