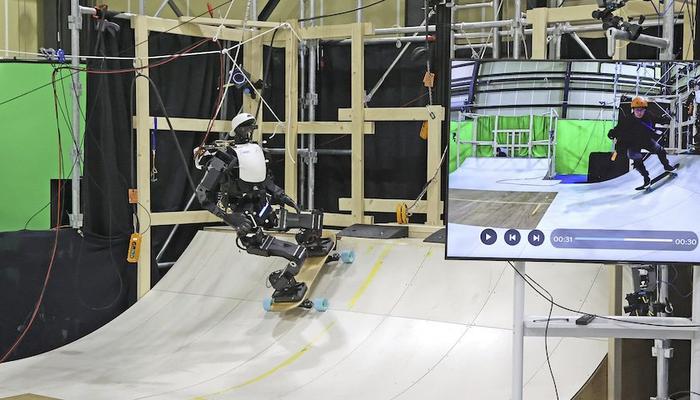日本在八國聯軍面前表演"行爲藝術":連搶劫都保持秩序
作者:雪珥
來源:《中國經營報》
庚子國難中,最大的入侵國是我們一衣帶水的東鄰日本,這也是日本在明治維新後第二次入侵中國。這次入侵中,日本將淪陷的北京當做一座巨大的走秀臺,向西方世界展示它的“文明形象”。另一方面,也是在日本的刺激下,清政府開始全面改革。當然,“文明”面具的後面是帶血的武士刀,在“親善”、“共榮”的口號下,日本對中國一次又一次舉起戰刀。
北京淪陷了,恐怖依然,只是換了色。
在此前義和團的“紅色恐怖”中,北京市民可能因一盒“洋火”(火柴)就被指爲“二毛子”,而被全家綁到莊王府(現今平安里一帶)門前開刀問斬。如今,在八國聯軍的白色恐怖中,北京市民又可能因爲穿了條紅褲子而被指爲“拳匪”,同樣遭到處決。步槍上那帶着深深血槽的刺刀,雖短,卻與古老的大刀片兒一樣令人膽寒。
八國聯軍將北京城分區佔領。北京人很快就發現,與那些高鼻子、藍眼睛的西洋鬼子們相比,身材矮小、能寫漢字的東洋鬼子倒不顯得那麼窮兇極惡,日本人所佔領的東北區(朝陽門以北、德勝門以東)隨即成爲刺刀下討生活的北京人的避難之地。
日軍有意將這座淪陷的城市作爲舞臺,向世界展示自己的“嶄新”形象。
滿城盡披太陽旗
日本之行事縝密令西方人望塵莫及。
在八國聯軍確定了各自的佔領區後,僅僅3天時間,不僅日佔區,而且整個北京城似乎到處都是日本的太陽旗。這是日軍主力第五師團從廣島出發時就帶上的“必要裝備”,他們精心準備了數萬面小型日本國旗,在那顆紅太陽邊上的留白處,用漢字醒目地寫着“大日本帝國順民”。如今,鐵騎入城,這些“免罪符”被迅速分發給北京的市民們,無論是朱門府邸、四合院還是貧民窟,都掛上了這一新的“門神”,西方人喫驚地發現:大清國的首都似乎被日本一家獨佔了。大街上的不少店鋪,除了太陽旗外,還掛上了拙劣的英文告示:“Belong Japan”(屬於日本)。
美國著名傳教士明恩溥(Arthur Henderson Smith,著有漢學名著《中國人的性格》,後來推動了庚子退款及清華大學、協和醫院的建立)記載道,北京市民爲了避免迫害,出行時手上都會拿着列強們的國旗,而以日本旗爲主。但除了日本旗外,其他旗子多是北京人自制的“盜版”,十分粗糙,一到下雨天,旗子上的塗料就掉色,看上去十分怪異。在刺刀之下,英語也得到了迅速的普及,北京胡同的牆壁上刷上了標語:“Pray officer excuse. Here good people”(求求官爺開恩,這裏都是好人),甚至在一座曾經作爲義和團壇口的寺廟門上,也貼上了“God Christianitymen”(上帝基督的子民)。
面對各色洋鬼子,北京人迅速地做出了自我調整,曾經滿大街的義和團們早就沒了蹤跡,似乎被人間蒸發,人們都將自己打扮成了“拳匪”的受害者,“使自己適應新的環境,如同水被倒進容器裏那麼自然”(明恩溥語)。
“文明”的招牌
一個名叫川島浪速的35歲日軍翻譯,應日本派遣軍司令福島安正的再三請求,在日佔區開始指導警務工作。日軍設立了“安民公所”,其所長、事務官和憲兵均由日本警官擔任,巡捕則僱傭中國人,成爲北京的新警察,在最爲動亂的數月間在轄區內迅速恢復了秩序,日佔區因此成爲北京最早恢復市面繁華的區域。
川島浪速還招收了40名“有文化”的中國人蔘與“警務速成訓練課程”,隨後又招收了50人。日本人回覆秩序的能力,和在人才方面實行可持續發展的眼光,給負責留守的大清國中央領導人、慶親王奕劻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局勢穩定後,另一位國家級領導人、肅親王善耆,應日本公使的要求,從清軍中精選了240名士兵,組成了“巡捕隊”,臂纏白箍,上蓋“安民公所”大印,腰間掛着佩刀或馬棒,執行巡邏,開創了北京警政的先河。而肅親王因此與川島浪速成爲哥兒們,甚至其女還拜川島爲義父,這就是日後大名鼎鼎的“川島芳子”。
日軍在佔領區內顯示出嚴明的軍紀,這幾乎得到了西方記者、外交官及軍官們的一致認同。美國隨軍記者、《紐約時報》的奧斯卡(Oscar King Davis,當時派駐菲律賓,隨美軍第14團從馬尼拉前往北京)爲著名的《哈潑斯週刊》(Harper’s Weekly)詳細報道了各國軍隊在京津地區的搶掠情況。他觀察到,俄、法軍軍紀極壞,到處燒殺搶掠,而日軍與美軍相對恪守紀律,其中,日軍的紀律更爲嚴明。他引用一個西方軍官的話說:“作爲基督教國家的一名軍官,我很羞愧,今天我見到一名被我們長期地稱爲異教徒的日本軍官,他說搶掠是不對的,並且絕不允許。我無話可說,因爲我的人都在搶掠,而他的人沒有。我無法阻止搶掠,而他卻能。”
美國公使康格(Edwin Hurd Conger)的夫人莎拉(Sarah Oike Conger)在其寫給美國親友的信中提到:“中國商人帶着貨物回到北京時,先是悄悄溜進日本人的轄區,因爲他們最信任日本人。後來,這些街道變得擁擠不堪,日本人就要求他們必須到城裏別的地方去,他們立刻就湧進了美國人的轄區,擠滿了街道,並留了下來。”
在八國聯軍中,日本是出兵最多的,在天津、北塘、通州等各次戰役中,日軍幾乎都擔當了攻堅先鋒,傷亡慘重,佔到聯軍總傷亡數的40%左右。日軍作戰兇悍,給其他國家的軍隊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美國外交官小田貝(Charles Denby, Jr, 1861-1938)給《哈潑斯週刊》撰文,認爲“那些在聯軍中與日軍曾經並肩作戰的他國軍隊,今後如果不得不與日軍爲敵,一定會猶豫再三的”。
搶劫的秩序
當然,日軍絕非不沾葷腥的貓,只是與其他軍隊的渙散相比較,日軍更爲剋制、更有約束,甚至在搶掠方面也更有組織紀律性。
當聯軍大多數官兵到處爲自己尋找發財機會時,日軍卻在嚴密的組織下,直插大清國的財政部(戶部,辦公地點在今公安部地址),一舉掠走庫存白銀近300萬兩。同時,他們從各衙門搶了大量的文件,其中不少至今尚未公開,成爲國際史學界最爲期待的寶庫之一,以期填補在中國近代史研究中的資料空白。
除了集團性的搶掠外,日軍個人也參與搶掠,但與其他國家軍人相比,他們更爲隱蔽。《中國與聯軍》一書作者、英國畫家、作家亨利(Henry Savage Landor)在現場觀察到:“日本軍隊在搶劫時與西方列強毫不相同,顯得十分有文化、有內涵”,他們在中國人的房子裏搜尋古瓷器,還聚在一起認真欣賞,如果不帶走,便輕輕放回原處,“而美國人、法國人、英國人或俄國人,更不用提德國人,他們除了碰到堅固的銅塊、石塊之外,沒有不打碎、弄彎、弄髒以及損壞的……日本人也搶掠,但他們搶掠的方式是沉默、安靜的,他們不把東西亂扔,不摔碎,也沒有任何不適當的藝術破壞。他們任意拿取他們所喜愛的東西,但是做得是這樣精細,以致似乎完全不像搶掠。”
軍紀逐漸敗壞
日軍在北京的表現,幾乎給西方世界一個“仁義之師”的形象,後世的日本右翼以此爲依據,來否定包括南京大屠殺在內的所有對日軍殘暴的指控。同樣是佔領中國的首都,但1937年日本人何以在南京如此殘暴?
第二次中日戰爭(即抗日戰爭)中的日軍將領岡村寧次,曾被控在中國華[0.14 -2.10%]北地區實施野蠻的“三光政策”,但他在戰地日記中卻對日軍軍紀敗壞有過深刻的分析。岡村寧次承認,“在這40 年中(從甲午戰爭起算),我官兵在戰場上的道義,特別是對現地居民的道義,比過去顯著降低,則是不應掩飾的缺點。日清戰爭(即甲午戰爭)、北清事變(即八國聯軍戰爭)、日俄戰爭當時的日軍,無任何掠奪、強姦行爲,這是爲許多外國人寫的材料所證實的。然而,同樣的日本人,現在卻有不少人對當地居民有虐待行爲。嘴上高喊‘聖戰’,高喊‘八紘一宇’,但事實卻與此相反。今昔對比,使人難以想象。”
他總結出,日軍的軍紀比八國聯軍時下降的表現是:一、對上級的服從性下降(表現於犯罪統計、言語態度、敬禮等);二、性道德下降(表現於強奸、隨軍有慰安婦);三、公共道德更加缺乏(爲圖省事,將送往修械所修理的武器棄之路旁;偷盜其他部隊的馬匹成風;侵佔送往前方的慰問品等等);四、幹部有犯強佔、收賄者;五、有藉口處理麻煩而殺害俘虜的野蠻作風。
岡村寧次認爲:“我們身爲指揮官,固然責任重大,但大部分士兵是從內地社會直接到戰場上來的,所以社會的責任也很重大……現在大部分官兵並非現役,一般都是應徵後立刻上陣,因此,與其說是軍隊之罪,莫若說是日本國民之罪。” 他認爲,日軍的暴行,暴露了日本國民的劣根,如“缺乏公共道德、消息閉塞、對國際事務缺乏理解、缺乏寬容和憐憫弱者的仁義教養等”。
在岡村寧次看來,戰爭的擴大化、長期化,導致了兵員得不到及時補充,官兵得不到及時的培訓,軍隊整體素質大爲下降。而岡村寧次的參謀長宮崎週一中將則一針見血地指出:“服兵役中的好兵,在家時也是良民。好兵是由良民培養出來的。因而,士兵的非法行爲,特別是軍風紀的渙散,可以說是國民倫理觀念下降和忽視教養的反映。維持嚴明的軍風紀,當然主要依靠部隊本身嚴格切實的指導與監督,但與直接掌握兵員的下級幹部的素質,有着重要關係。”
根據宮崎週一的分析,八國聯軍入侵及日俄戰爭時,日軍官兵都是經過嚴格訓練的現役兵,各級軍官也都是長期服役的職業軍人,因此,“保存了團結服從以及軍風紀各方面的優良風習”。但在二戰中,因爲戰爭擴大,軍隊數量急劇增多,“傳統的優良風氣越來越少,新建或改編的部隊,有如摻水的酒,軍隊傳統的優良風氣喪失殆盡。特別是應徵的下級幹部,除個別人外,在覺悟、信心及知識能力等方面,多數都不夠格……”他甚至將矛頭直指當時的日本社會風氣,認爲是日本受到了“資本主義”的嚴重侵害:“日清(甲午)、日俄之戰,關係到國家興衰存亡,當時全國軍民舉國一致,鬥志昂揚,成爲強大的精神支柱。但是,滿洲事變(九一八事變)、特別是中國事變(七七事變)後,隨着國家財政的龐大化,資本主義弊端到處氾濫,黑市盛行,社會上好人受難,在這樣的社會里要想得到優秀的士兵,無異緣木求魚。”
平心而論,沒有一支軍隊的指揮官不希望自己的軍隊能做到令行禁止、秋毫無犯,這不僅是政治上的需要,也是戰鬥力的重要保證。當日軍士兵都敢偷盜司令長官的戰馬時,岡村寧次也只好嘆息世風日下、人心不古,他雖然發佈了大量標語訓令,但是也只能在日記中感嘆:“‘討蔣愛民’的標語到處張貼,但毫無實效。”
隨後,義和團運動迅速轉化爲暴力排外事件,而日本駐北京使館的書記員杉山彬被清軍殺死,成爲第一個死亡的外交人員。駐紮在天津的日本海軍指揮官向東京緊急報告,要求迅速增兵,但日本政府對此採取了冷處理。在內部,他們必須對南北戰略進行權衡,而在外部,他們必須先徵詢列強的意見,以免無謂樹敵。實際上,他們此時的重點依然是南方,軍部甚至電令臺灣總督,立即做好軍事動員,準備隨時武力進佔廈門。
此時,華北局勢日益糜爛,列強們紛紛增派軍隊,日本的宿敵俄國更是一馬當先,在東北地區大舉增兵,矛頭直指日本。日本看在眼裏,急在心中,而與日本同樣心急的,還有俄國的第一敵人、當時世界老大英國。英國的軍力被南非的布爾戰爭所牽制,不得不從澳洲、新加坡、中國香港、印度等殖民地調兵(參閱本報2月8日《北京城裏的澳洲軍旗》),因此他們寄希望於日本,一是解決北京問題,二是牽制俄國北極熊。
日本人很沉得住氣,不見兔子不撒鷹,當英國表態希望日本出兵2萬~3萬人時,它依然要求英國駐日本公使幫助向列強徵詢意見。俄國和德國起初堅決反對,但隨着局勢日益危急,各國與駐北京使館的聯絡全部中斷,也只能同意動用日軍。英國方面更是起勁,主動表示日本出人、英國出錢,所有軍費由英國負責。經過這樣的千呼萬喚,日本才宣佈派遣駐紮廣島的精銳部隊、陸軍第五師團進軍中國。在參與八國聯軍的全過程中,日本人在處理與列強軍隊、中國政府等各方面關係時,韜光養晦,十分低調,成了個幾面討好的“琉璃蛋”。而保持嚴明的軍紀,展現日本軍人的“新形象”,自然是它的重要措施。
而在南方,日本則大打出手,出兵佔領了中國廈門。但南北兩線作戰,遭到了以伊藤博文爲代表的持重派的堅決反對,當俄國從北京首先撤軍並收縮到東北,對日本在朝鮮的勢力構成巨大威脅時,尤其是列強也紛紛派出艦隊前往中國福建時,日本政府才下令從廈門緊急撤軍,將廈門無條件交還中國,這就是所謂的“廈門事件”。
自此,日本在東亞的戰略重點轉向北方,四年後爆發了慘烈的、被國際史學界稱爲“第零次世界大戰”的日俄戰爭。
“悶騷”的尷尬
日本在八國聯軍中表現得十分低調,除了本身在中國福建的戰略考量外,還有被迫韜光養晦的無奈。此時的日本,正是西方大肆宣揚的“黃禍論”的首要攻擊目標,除了英國老大哥外,日本其實已經被西方孤立了。而參與八國聯軍行動,正是打破孤立的好時機,而關鍵就在於既要“任勞”,也要“任怨”。
日本此前在甲午戰爭中的巨大勝利,令西方看到了一種可怕的前景:已經掌握了西方技術的日本,如果團結帶領人口龐大的中國進行改革和擴張,則蒙古人席捲西方的“黃禍”必將重新上演。在德國皇帝威廉二世及俄國沙皇尼古拉二世的推動下,“黃禍論”在西方甚囂塵上。爲了分化中日,西方、尤其是俄國和德國,對中日採取了截然不同的態度。八國聯軍時期擔任日本首相的山縣有朋,在1896年與李鴻章一道參與沙皇的加冕儀式,也先後順道訪問了柏林,李鴻章到處受到國家元首般的禮遇,而山縣有朋則只得到一般的接待。
種族戰爭此時也成爲日本人最爲關注的話題。日本最有影響的政治家之一近衛篤麿公爵,在日本發行量最多、影響最大的雜誌《太陽》上發表文章,題目就是《同人種同盟,附支那問題研究的必要》,近衛篤麿公爵寫道:“我認爲,東亞將不可避免地成爲未來人種競爭的舞臺。外交策略雖然可能‘一時變態’,但僅是‘一時變態’。我們註定有一場白種人與黃種人之間的競爭,在這場競爭中,支那人和日本人都將被白種人視爲盟敵。有關未來的一切計劃,都必須把這一難點銘記心中。”(參閱本報2009年6月8日長篇《黃禍:中國威脅論的前半生》)
正是在這樣的危機意識下,日本向中國發動全面的友情攻勢,猛送秋波。1897年,俄、德兩國大演雙簧,分別奪取了青島和旅大,傷透了心的大清國,再度轉向同文同種的日本。兩個浴血搏殺的東亞鄰居,突然變成一對“歡喜冤家”,並且在軍事領域率先進行了全面的合作,而主導其事的正是甲午戰爭的主要策劃者、日本參謀總長川上操六及此前抗日調門最高的張之洞。
自此,中國與日本開始進入爲期10年的蜜月期,而當“戊戌政變”後,重新成爲中央領導核心的慈禧太后親自拍板,大清國派出了密使,攜帶專供兩國皇室聯絡的密電碼,希望能與日本建立同盟關係。代表團在日本受到了隆重的高規格接待,但是,面對西方鋪天蓋地的“黃禍”論調,對於大清國拋出的結盟繡球,日本最後並沒有接受。
當義和團運動給列強們攫取在華利益創造了前所未有的好機會時,日本卻陷入了作爲“悶騷”的兩難處境:既想渾水摸魚,又不想引起西方的任何警覺和恐慌,多幹少說、甚至幹了也不說,就成了唯一的選擇。
撕下面具
功夫不負有心人,日本人在八國聯軍這根鋼絲上的精彩表演,收穫巨大。
經此一戰,日本與大清政府的關係非但沒有受到影響,而且還得到了加強。日本人在北京佔領期間顯露出的行政管理能力,給大清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日本被中國朝野當做了效仿的榜樣。在逃亡途中,慈禧太后和光緒皇帝發佈了全面改革、尤其是政治體制改革的號召,而日本則成爲中國的第一教父。
在隨後爆發的日俄戰爭中,作爲戰場所在地的大清國雖然宣佈中立,但實際上朝野上下都是一邊倒地支持日軍,令日本在此獲得了顯著的“主場”優勢。西方也沒有被俄國刻意鼓動的“黃禍論”嚇倒,英國人甚至反脣相譏,認爲真正的“黃禍”並非是日本,而是俄羅斯,這大大幫助日本減少了國際壓力。這場中日親善的喜劇,在日俄戰爭後,因爲日本完全繼承了此前俄國所攫取的在華特權,戛然而止。大清朝野最後發現:最該當心的還是這位“侏儒”兄弟,在“威武之師”和“文明之師”的背後,是絲毫不亞於北極熊的貪婪和冷酷,並在三十年後徹底暴露出了野蠻之師、虎狼之師的真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