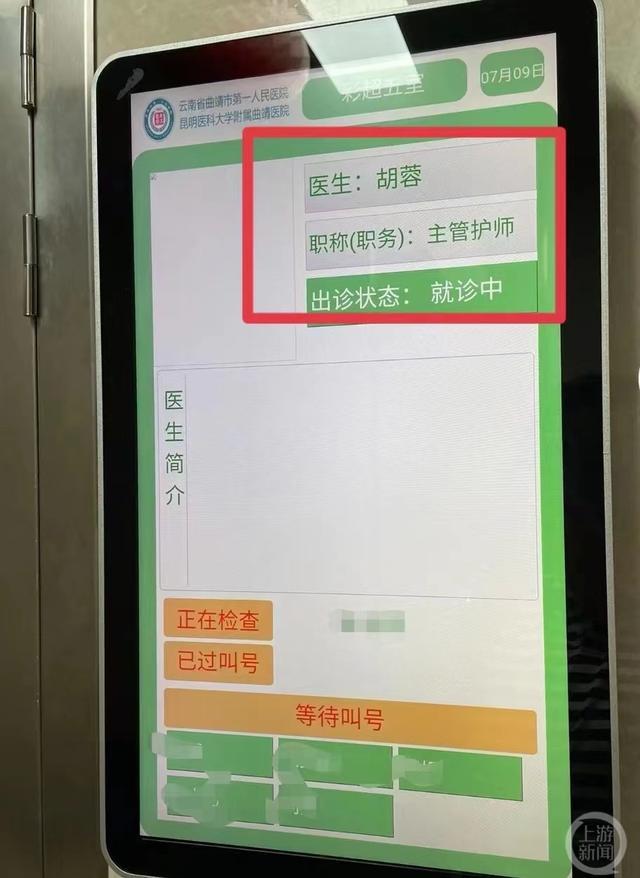他看上一塊靈璧奇石,乾兒子調動五百士兵搬運到臨安,難度有點大
靈璧石產於靈璧縣的深山之中,色黑如漆,有白色細紋如玉,石質堅硬,敲擊時聲音清越。
《齊東野語》記載,南宋武將趙葵曾經到過靈璧縣,看到大道旁邊奇石林立,其中一塊奇石矗立,“崷崪秀潤”。趙葵縱馬來到奇石前,觀看撫玩,許久不捨離去。
幾年之後,有人獻給趙葵一塊好石頭,趙葵對賓客們說起當年在靈璧見過的那一塊奇石,讚歎不已。
過了一會兒,幾百個士兵抬着一塊巨大的奇石來到趙府,把它安放在庭院之中。看上去,正是當年在靈璧見過的那塊奇石。趙葵又驚又喜,問這是怎麼回事?
原來,趙葵有一個義子,名叫趙邦永,是一名降將。當初趙葵在奇石前面徘徊時,趙邦永看在眼裏,知道他非常喜歡這塊石頭。趙邦永就讓屬下的五百士兵把石頭搬運回來,一直沒敢獻上,剛纔聽到趙葵又提到這塊奇石,方纔命人搬運進來。
靈璧縣在安徽的東北,距離臨安幾百公里,趙邦永把這樣一塊大石頭運回來,勞民傷財,只爲博得趙葵一笑。
晚明書畫家、收藏鑑賞家李日華的府中也有過一塊靈璧石,是一位朋友送他的,那人就是許同生。
許同生是吳興人,爲人孤介高朗,形象有些不堪,“骯髒巍峨,壯氣勃勃,意常不可一世,見貪鄙嗜利者尤唾罵不容口也。”是粗粗拉拉、愛憎分明的一個人。
天啓年間,李日華與許同生在北京第一次見面,許同生“破扇羸馬,踉蹌長安中”。李日華在《六研齋筆記》中提到許同生當時的職位,說他是刑曹。
二人一見如故,相見恨晚。後來許同生到淮陽任職,得罪了太監,不到半年就被迫離職。許同生打算移居別處,他宦囊空虛,身邊最拿得出手的是一座靈璧石,攜帶不便,就把它送給了李日華。
李日華把靈璧石移入恬致堂,安放在一棵松樹下,“朝夕相對,若見先生焉”。他又爲靈璧石作了一幅畫,送給許同生,還寫下一篇石銘。
許同生死後,李日華對這塊靈璧石的感覺更深,經常“勺酒酣酹,如對先生”。許同生死去兩年之後,也就是崇禎壬申年,李日華決定把這座靈璧石轉送給自己的學生石夢飛,理由也比較奇特。首先是自己開始煉氣養生,不敢多喝酒,也就不能經常用酒來敬奉靈璧石。而石夢飛一向仰慕許同生的大名,而且爲人嚴謹,酒量又特別大。
李日華把靈璧石和一棵松樹一起送給石夢飛,讓他好好看護自己與許同生心愛的這塊石頭,“庶千載之下,亦不沒我兩人氣誼”。
李日華擔心自己的子孫將來不認帳,再向石夢飛討要這塊石頭,或者向石夢飛要錢,專門寫下一份石劵,以爲證明。
和許多文人一樣,李日華喜歡收藏和把玩石頭,這種愛好也和他的繪畫大有關係。玲瓏多竅的奇石、峻巖一直是中國畫偏愛的描摹對象。其中,石與松、石與竹的搭配是畫家最喜歡的,所以李日華在一道《松石》中寫過:“松須石作伴,石頑松更奇”。
李日華的許多石頭是買來的,他在一首《買石》詩中寫道:華頂嵩巔費討尋,擎持容易到家林。眼前突兀餘增氣,意外雕鏤誰巧心。浪洗沙痕青靄溼,雲生瀑紫苔深。從教瓶儲緣渠罄,且得松根自在吟。
朋友贈送的、自己收買的石頭擺放在案頭、樹立在庭院之中,李日華安坐家中、不須奔波、攀登就能欣賞到自然的奇崛秀色。這正是收藏奇石的好處,所以李日華在一首《得擁秀峯石喜賦》中寫道:“不須更策探奇杖,秀色飛來到草堂”。
李日華喜歡的那種松與石的組合,張岱在《陶庵夢憶》中也提到過,是在董文簡的庭院中。其中的石頭形狀奇特,“磊塊正骨,窋吒數孔,疏爽明易,不作靈譎波詭”。
張岱看到的這塊石頭頗有來歷,據說是宋徽宗花石綱中的一塊,到了南宋時又被陸游移入自家的府中。董文簡得到這塊石頭,把它豎在庭中,石頭後面種了一棵剔牙松,石頭的北面又建了一處獨石軒。
李日華的身邊還有另一樣石器,就是大理石屏風。他在《六研齋筆記》中具體說到了大理石屏風的好處,最主要的一點是大理石本身的紋理帶有畫意:“所現雲山,晴則尋常,雨則鮮活,層層顯露。物之至者,未嘗不與陰陽通,不徒作清士耳目之玩而已。”
李日華對當時許多畫家的作品感覺失望,認爲“令人憒憒思嘔,不如環列大理石屏,以一榻坐臥其下”,反而能從中看出一點名家的筆意,“所謂天不足則補之人,人不足則還之天”。
產自雲南的大理石白黑分明,體量大的可達七八尺,最適合製作石屏風,一塊好的雲南大理石價值百兩銀子。
於左 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