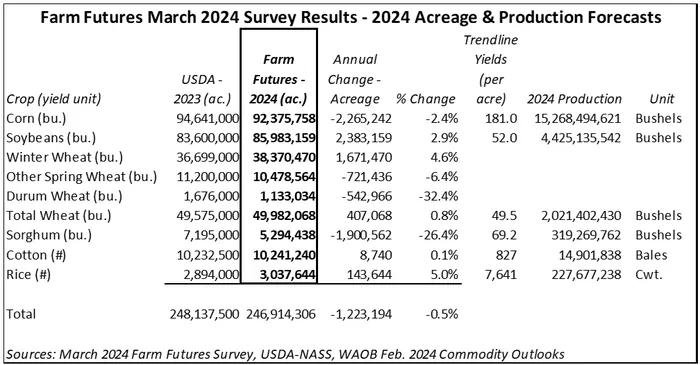大旱之年,地裏的菌子乾渴着不出芽,看不見大片野生菌的蹤影,急壞了菇農
本文刊載於《三聯生活週刊》2019年第27期,原文標題《尋菌記》
“白天暴曬,晚上大雨,接着再暴曬。陰晴交替幾日之後,趕上一個雨夜,菇農揣着手電、披上雨衣就騎摩托上山了。一家來得比一家早,手電像成羣的螢火蟲把山點亮。被照亮的山頭就不能上了,就得往黑的地方扎。”
記者/劉暢 攝影/蔡小川
林俊熹(左)在山裏尋找牛肝菌(蔡小川 攝)
當地人的描述讓我想起電影《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中,夜晚海里的熒光把船圍住,彷彿我只要摸着夜色,坐到一輛摩托車後座上,漫山的菌子就會將我包圍。我6月底來到昆明,正是往年下菌子的時節。菇農們有說法,“天上的雷一震,地裏的雞樅就冒出來”。不惟雞樅菌,各色牛肝菌、青頭菌、竹蓀、珊瑚菌也早已次第長出。滇中、滇西的菌子一天可以收穫兩輪,半夜上山的人採一次,菌子成筐送到山下。菌販子把蒐集的菌子裝車,下午便出現在昆明的菜市場裏。中午又能採一次,第二天凌晨三四點,帶着泥土的菌子就會發往全國各地。
我想探訪採菌的過程,當地人覺得擰開瓶子喝水一般容易的事,卻趕上今年大旱。山裏人說,石榴幹到經一次雨便炸開,土地皴裂,地裏的菌子也乾渴着不出芽。昆明周邊不見大片野生菌的蹤影,我到楚雄等雨,那裏是“野生菌王國中的王國”。雲南省餐飲協會採供分會副會長林俊熹也着急,他有無數山頭菇農的信息,每年這個時候,忙着採購、分銷各地的野生菌。他抱着手機與菇農接頭,終於雷達般搜尋到楚雄祿豐縣的山中尚有牛肝菌可採。
祿豐縣在昆明與楚雄市區之間,距兩者均一個多小時車程,我得到消息當日下午,直奔縣東的山裏。平地海拔1700多米,山頂不到2200米。平緩的山坡在三四十年前,仍是放牛娃的樂園。那時既不是“採”,也不是“找”,菌子幾乎只是用來“撿”的。當地人說,小時候他們放牛的當兒,看到青頭菌、銅綠菌、羊肚菌,就摘幾棵野草,一頭打個結,一頭把菌子串起來拿回家;遇到奶漿菌,就擦擦直接喫;挖着松茸,則折些木枝,生堆火烤着喫。菌子值錢後,菇農成了當季的職業。他們大多把摩托車停在山腳便往上爬,有時一天會翻三四座山,遇到下雨得手腳並用。林俊熹帶我來這裏,既因爲見到了菌子,也因爲對於我這樣的外行,此地路途便捷,車能直接開到山上。山腳下尚有農田和果樹,越往深處越是原始的松林,野生菌就長在樹下的松針堆裏。
越往山頂走,我對採菌的浪漫幻想越幻滅。從上往下看,松林像蔓延在幾座山間的原野,而城裏野生菌市場的寂寥,轉化爲林間暴曬的烈日。地上的紅土彷彿吹口氣就會飄起來,松針乾枯,像理髮店地上胡亂堆的頭髮。這裏怎麼可能長蘑菇?
我沉默地坐在車裏,生怕最終尋到的只是一段背陰的枯樹枝上的幾朵黑灰色“耳朵”,甚至與南方梅雨天氣裏家中門框上冒出的還是同胞兄弟。只要菌絲在,蘑菇就年年長。當地人帶着我們往有固定“菌窩”的地方走。也因爲菌子這樣的特點,守住“菌窩”便等於守住了天降之財。菌子季時,很多菇農一家子搬到山上,守在樹下,爲此發生過不少爭鬥。因祿豐縣產菌尤其多,遂有了包山的形式,運氣之爭變成一家之私。
這座山頭便是這種情況。野生菌棲身在半山腰以下的陰溼地段,我們到達山頂後,再由上往下開。車顛得七葷八素,原始森林中被走出條路。沿途有人放牧,水牛大角如盤,山羊披着黑亮的毛。司機卻問:“看着好喫嗎?”當地人把它們燉成火鍋,誇耀說這些喫着菌子長大的牛羊極富營養。但它們實際是喫不上蘑菇的,且不論菌子未見得在它們的食譜裏,這條羊腸小道是通向野生菌產地的唯一道路,包山人的住所在路的盡頭,路口圍起一段鐵絲網。
我們在包山人的家門口停車,狗嫌籠裏的雞鴨迎接我們不夠熱烈,也對着我們狂吠,又憚於初次見面便過於親密恐對自己不利,沒拴鏈子也與我們若即若離。包山人老李在家畜的通報後登場,一位四十多歲、總躲着相機鏡頭的靦腆農民。他與林俊熹相識,但不直接相關,林俊熹是司機的收貨商,而司機是老李的好友兼收貨商。老李與家人幾乎常年住在山上,以雞鴨爲食,與狗爲伴,菌子季採菌子,冬天和早春便採藥材。
老李帶我們採菌。他院中晾着切成片的牛肝菌,與家人炒着喫,我們到時,他早上已在山裏巡視了一圈。他在前面如履平地,對“菌窩”的位置瞭如指掌。松林一人多高,因之前的蟲害,上百畝的松樹枯萎,只剩彷彿被燒乾的枯木。“菌子對環境非常挑剔,枯樹會長蟲,只有活着的樹底下才能長菌子。”老李時不時停下來等我們,地上新冒的松苗擋住踩出的縱橫的路,一不小心就迷了方向。我們拿着一個二齒釘耙把樹下的松針撥來撥去,撅根樹枝,或是用腳也可以。松針夾着腐葉有四五釐米厚,像一層毯子爲野生菌鋪上溫溼度適宜的溫牀。
“哦呦呦!這裏有一朵!”林俊熹誇張地尖叫,一朵“白蔥”出現在松樹下,完全不需要特意尋找,它的菌帽有兩個手掌大,通體淡黃,挺立在松針上。這種菌是“見手青”的一種,菌體被鐵刀削過後會變色,有輕微的毒性,適合炒而不適合在火鍋裏煮。林俊熹採到的這朵菌長成已有兩三天,做成菜後肉質韌,口感鮮美,但因爲已經完全長熟,需要趕快食用。而它也有乾旱的印跡,菌帽已經“開花”,像一個餅,上面縱貫長長的斷痕,“一般菌子一出就是一窩,這裏只有一個,其他的都乾死了”。
難以判定這朵菌冒頭的原因,周圍仍一片乾燥,再見不到野生菌的蹤影。老李告訴我,即使雨量充沛時,山上也不會如我想象一般,珍稀的野生菌俯拾即是。把菌子裝在竹籃裏,我們繼續往山下走,村裏人把祖墳蓋在山上,不出幾步便能遇見壘起的墳冢,周邊藏着蛇。山下有河,半山腰的地方溼潤起來,松針的清香漸濃,我也在一個小土坡的底部見到了一朵“白蔥”。它藏在兩個樹根間最爲陰溼的地方。
這是一朵幾乎完美的雙生菌,一大一小的菌帽都是飽滿的傘狀,連在同一個根上。我學着林俊熹的樣子,用耙子刨開松針,再用手圍着菌子攏成一個圓,把菌子地表的部分充分露出來。我不敢像老手一樣,用靶子的齒卡住根部把菌子直接撬起,爲保菌子完整,還是雙手比較溫柔。但我立刻領略到耙子的用途,手接觸得越多,不願割捨的也越多,最終便探到土裏,把菌子連根挖起。“這是給人家‘斷子絕孫’了!”林俊熹教我把菌子的根部掰下來、埋回土裏,將松針也撥回去,“菌子的根留在潮溼的土裏,每年才能一直長”。
行至山下,林俊熹仍感嘆平時兩三籃的量只採了一籃。“下過大雨,再過一週再上山,那就漂亮了。漫山遍野都是五顏六色的菌子。”老李正說着,天邊的烏雲降下閃電,要下暴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