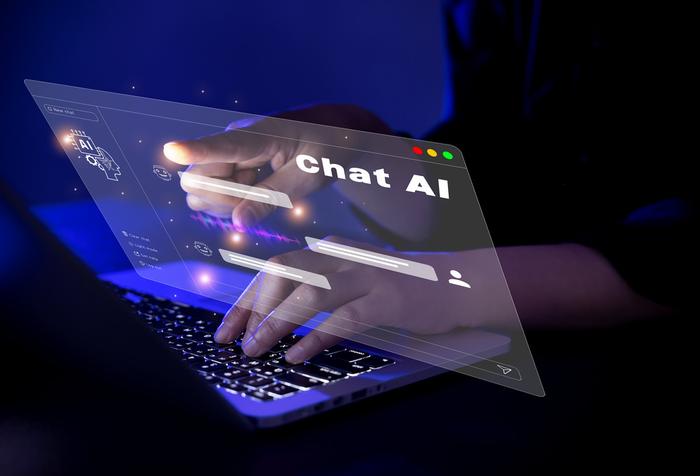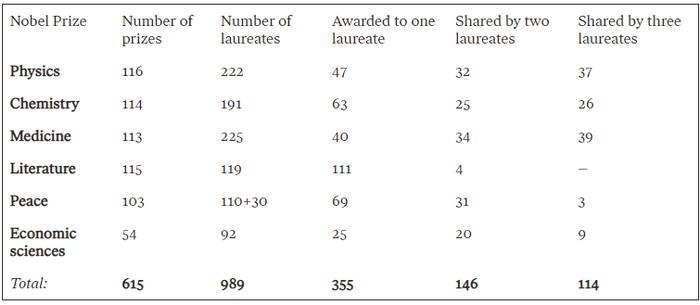怎麼有 90 後這樣寫小說|Editor's Pick
在這個青年寫作大多要麼依賴想象,要麼關注人類命運的時代,小說已經將人心剖得足夠瑣碎,也提供了足夠多的社會構思,作家們真正該思考的是,我們還能寫些什麼?今天的 Editor's Pick,單讀編輯沈律君帶來了 90 後四川作家周愷的長篇小說《苔》。周愷獨樹一幟,他採用方言寫作的手法,依託家鄉樂山的地方誌,聚焦那些被清末歷史洪流遺忘的小人物,他企圖將個體拉回渺小卑微但真實的生命狀態,將“活着”這件事寫出悲情和赤誠來。
《苔》
周愷 著
中信出版集團 / 楚塵文化 出版
“小說要完”的悲情反題
沈律君
《苔》擺在桌上,像一個怪物,五百頁厚,接近四十萬字,早期白話文結合古代白話小說的語言構成了行文,小說講述的則是光緒宣統年間四川樂山鄉鎮的故事。種種跡象表明,在對小說的語言和個性有強烈要求而且時長難免心浮氣躁的今天,它像是那種必須得發宏願才能看完的小說。
確實,關於這本書的一切信息都在阻止我進入。故事簡介說到,命運迥異的兩兄弟在清末亂世中成長浮沉。這樣一條主線容易讓人聯想到一些常見電視劇情節、一些期刊上陳舊的“鄉土故事”。還有一些嚴肅的、崇高的評議,比如說到它對歷史的嚴謹考證還原、對方言與袍哥暗語的呈現、繼承失傳的民間長篇小說衣鉢,以及直接追溯到《孽海花》甚至《紅樓夢》的文學傳統……這些說法被安置在一位 90 後作者首部長篇小說上,顯得它沉重難翻。
當我試圖拋開一切在書之外的外部負載,摒棄自己對家族、兄弟、前現代故事背景的刻板印象,只純粹以對 90 後寫作的好奇開始閱讀時,卻在度過最初的幾頁之後,找回了久違的“被抓住”的感覺。
這多半來自於小說對其所在時空的構建或再現,半白話文的簡練剛好能在很短的篇幅裏沉穩而乾脆地再現一個清末四川鄉鎮的“說書式”原貌,又能讓懸念和衝突——威脅、女屍、兇殺、“賣子”迅速出現而不顯得唐突,因爲故事與人物,它們原本就內嵌在那個憑藉小說所重建的世界裏。
故事開篇像一個緩緩搖動的俯拍大全景鏡頭,作者周愷用文字導演,對大量人物展開調度——前半本書的主角、故事中的第一代人:李普福和劉基業、鄉場上的袍哥勢力、桑農、幾位姨太太,他們先後出現在畫面中。接下來,你發現戲臺上吊死的女屍出現在了畫面裏,突然鏡頭向前推,特寫,定格,故事開始。
90 後作者中,還沒有誰是這麼寫小說的。
《苔》被認爲和李劼人的《死水微瀾》有直接傳承關係。兩者寫的都是清末民初的四川鄉鎮,都是小地方的世情和人物。除了表面的相似,技法上也貌似同源:李劼人早年翻譯法國文學,對《包法利夫人》和左拉的自然主義推崇備至,而自然主義式的寫作更是在《苔》中隨處可見。其中所謂“全景式”描寫,着眼於對各行各業、民間組織、鄉鎮神鬼、歷史事件展開全面細緻的描述。
但仔細對比會發現,《苔》所謂傳承,其實更像一種借鑑。李劼人的寫作,使用的基本已經是現代白話文,但《苔》的語言、人物對白、詞彙使用相比《死水微瀾》更爲“復古”,而且非常純熟,幾乎看不到模仿或者刻意的痕跡。這也是作者周愷所追求的:全面還原清末民間語言的質感,再現歷史在細微處的真實。對於清代嘉定(樂山)地方社會的描寫中,他有時直接使用文化人類學和微觀歷史的方式,這是《死水微瀾》中所沒有的。
小說中用大量筆墨展現江運駕船、縴夫拉縴,詳細描寫傳統桑蠶制絲過程、民間行會運作規則,袍哥之間的互動關係和權力爭奪、節日與集會的情貌流程……這種紀錄片式的地道再現,有時甚至比故事情節更奪目。周愷在創作時參考了大量的包括嘉定縣誌在內的歷史文獻,讓整部小說堪稱是清末樂山城鄉市井的“百科全書”。
但千萬不要被文字所迷惑,《苔》本身並不是一個“純復古”小說,它擁有自然主義沒有的現代技法。小說在敘述上做大量交叉、閃回、倒敘,甚至是 POV 寫作,常常需要讀者自己做拼圖遊戲,把多個人物發生在不同時間的故事進行組合。有些情節則直接刪除,需要靠前後文推演猜測。比如寫管事劉基業和老闆李普福的幺姨太偷情,作者直接抽掉偷情一事,幾乎全靠劉基業的心理和夢境意象來“暗寫”。
《苔》和李劼人、和西方自然主義流派最大區別在於,它並不真正“用力”描寫某一個人物。左拉對娜娜抱有批判和同情,李劼人對蔡大嫂和蘿歪嘴這兩個人物也非常用心,但對於自己筆下的人物,作者周愷似乎 “莫得感情”。
周愷作爲樂山人,我天然以爲他會用《苔》爲故鄉往日人事著書立傳。但事實上,故事中的主要人物,不管是李普福、劉基業,還是第二代人——被抱給大戶李普福的李世景和留在貧苦本家的劉太清,他們並沒有比其他人在小說中多佔太多分量。
《苔》寫到大量人物——石匠、袍哥、末代文人、妓女、桑農、絲商布商、行會頭領、袍哥、傳教士、地方官、土匪、煙館煙客、城市遊民、買辦、進步青年……在這些小地方的時代羣像裏,周愷並不偏愛於哪一個人,但這不代表他不關心這些人,就像這本小說名字所顯示的那樣,他的關注點是所有人既微小又輕易消逝的命運。
上一代人裏,嘉定“絲織大亨”李普福失蹤,從此再無音信,幾房姨太太都接連亡軼。下一代人裏,無政府主義革命者世相臣與官吏同歸於盡,袍哥們爲革命送命,李世景改名遠走,劉太清和他的土匪兄弟被“團滅”,人們甚至連那些死去的人是誰都不會知道,也不想知道。
越到故事的尾聲處,時代或者說世道,就越壓倒人物。無論是起高樓的、威震一方的、投奔山林的,還是更多老實度日的人,他們都像是地上隨處可見的青苔,在天翻地覆的大時代裏短暫出現又寂靜地消失。這讓小說通篇都散發着非常冰冷的質感。在《苔》的世界裏,人是無足輕重的,但《苔》就是專門爲這些無足輕重的人所寫的故事。在小說之外,不會再有人記得他們。這是《苔》在冰冷下面的溫度。
《苔》並不是一部完美的小說。它有很多明顯的瑕疵,《百年孤獨》“多年以後”式的句法重複出現多次,主流宏觀歷史事件和地方故事之間的敘述過渡略顯生硬,作者對真實再現的追求與文學虛構之間存在着對抗……它的前三分之一像大師手法,中段顯得筆力不繼,到了後三分之一,當所有瑕疵和破綻開始被坦誠顯露的時候,我們反而能看到一位擁有天賦且極爲認真的青年作者的誠意。
作家們早已經學得太聰明,知道怎麼去寫完美作品——需要有個性的語言,敘事的詭計,絕妙的比喻,需要隱微多意,儘量少觸碰經驗之外。這樣的作品當然容易完美,因爲它是個人的,個性的,是小說收縮自己的領地成爲一個準藝術品以後的產物。
這方面《苔》沒得眼色。它偏在其他同代作者早已放棄的領地上重新拓土。這當然並不意味着要宏大到奪回小說在 19 世紀的王位,而是在時空之網的漏洞下,打撈那些在任何時期都不被注意的,被篩掉的細碎東西。
清末轟轟烈烈的大事兒,我們聽過無數次,對那些大人物也如數家珍。但是一個四川小城、鄉鎮,那裏有什麼人做了什麼?對這些被網眼漏掉的小事兒,過去就過去了,不重要。就像傍晚街上看萬家燈火,在火車上看路過的村莊,那些不同房舍裏的人事,它們都被省略了。
《苔》要記住那些“小事”和“小人”。這可能會顯得過時、非主流、徒勞無功。但不會比單純把小說作爲情感容器的做法更差。
在今天時髦小說對人的內在做了太多呈現和剖析之後,《苔》試圖重新把人放回大的環境和空間裏面去,而不是單獨拎出來看。人不再高級,不再配得上罪惡、幸福、偉大、恥辱的道德價值,他們也不再是讓人嘆息的娜娜和艾瑪,不是說書人口中傳頌的英雄美人,他們如此微小,但還在那,還在他所在的羣體與社會中活着。
小說該怎麼寫下這樣的活着?在“小說要完”(已經完了?)的時代裏,出自青年作者之手的這部《苔》是一個悲情但確有可能的反題。
這裏可以把埃瑪·拉札勒斯那首著名的詩做一個改寫:把你疲憊的、你貧窮的、你多如牛毛卻在歲月中轉瞬即逝的人都給我/把那些無家可歸、飽經風浪、無人在意、默默死去的人都送來/在註定被遺忘的小說裏,我要爲他們留下印記。
《苔》 節選
周愷
不堪欺辱怒而殺人的年輕石匠劉太清與衆石匠一起逃上山上的觀音廟庵,遇到了老尼姑和她收養的女娃——
山上的日子是平靜的,若非偶爾念起嘉定城還有兩個同夥,念起巧聖祠還埋得有銅錢,劉太清和五個石匠恐怕都已忘記犯下的事情,仿若他們將永遠過着這樣與世隔絕的日子。
十多天後的一個傍晚,留在嘉定城巡風的石匠找來了。劉太清正巧同女娃子在劈柴,見到他們,便跟女娃子說,他要去商量事情,讓女娃子莫跟到他。他帶着他們去找另五個石匠,巡風的兩人說,捕快已經從巧聖祠撤走,他們到竹林地看過,銅錢還在那兒。不過,近幾日,城門口兵勇查得緊,官府已經描出了劉太清的畫像。八人合議了一宿,決定由沒有露過臉的兩人以及在嘉定城巡風的兩人,佯裝成菜販子,去把那些銅錢挑回來。
翌日,天未亮,那四人便出發,先到白廟場買了四雙籮兜,裝起洋芋,又一人買了頂草帽子,蓋在腦殼上。趕在落更前,他們進了城門,再到無人處,將洋芋傾一半到河溝頭,挑起剩下的一半,去了水井衝的護國寺,要了柴房的四張鋪。到半夜,四人爬起來,從側門往巧聖祠的竹林地去,兩人徒手挖銅錢,兩人各站一頭放哨。籮兜底下墊一層洋芋,中間放銅錢,銅錢使備好的土布包好,面上再覆一層洋芋,走動的時候,就不會發出叮叮噹噹的聲音。裝好後,四人繼續回去睡到五更,然後挑起籮兜,從護國寺正門出去,走到蝦蟆口,等城門一開,混在衆多的商販中出去。
劉太清本是想跟到一路去,可別的石匠不準,說官府已經曉得他的模樣了,他若跟到去,只會平添風險。那四人出發後,劉太清就坐立不安的,下午,他擔起水,跟女娃子到山腳洇地,一面洇,一面望到山路。那四人哪會這麼快就回來,這會兒,恐怕都還沒有走攏嘉定城。他是放不下心,他總覺得他們要出岔子,他怕他們在城門口就遭攔下來,怕捕快從巧聖祠撤走,只是爲了引他們上鉤。若那四人被逮到了,得不得供出他們躲在官帽山,兵勇得不得按起過來?
女娃子說:“太清,你莫再澆了,菜都遭你洇死完了。”
劉太清丟了糞勺,找塊石頭坐到起。
女娃子問:“昨天來的兩人是哪個?”
劉太清說:“石匠。”
女娃子問:“他們今早走了?”
劉太清說:“你莫問那麼多。”
女娃子小聲說了一句:“我曉得他們去了嘉定城。”
劉太清側過頭盯到她。
女娃子翻弄地上的石子,說:“我還曉得他們去搞啥子。”
劉太清嚇一跳,趕忙說:“你可亂講不得。”
“我不得跟別個說。”女娃子望到他說,“我還以爲那兩個生人是來引你們走的。”
劉太清說:“我們不得走。”劉太清猜到,昨天她定是在洞口偷聽到了,又說一道:“你莫對別個講,要砍腦殼的。”
女娃子說:“打死我也不得說。”沉默一陣,“太清,你娘沒有給你說過媳婦子?”
劉太清這時才放鬆了些,笑起來說:“還小嘞,再說,哪有女子肯嫁給我們石匠。”
女娃子有些急,說:“天下女子那麼多,你咋個曉得沒的?”臉上突然起了一團紅,“我是說,女子的心思,你們猜不透的。”可愈解釋,愈慌亂。
劉太清低聲哼:“東邊下雨西邊晴,子規只歇大樹林。鯖魚喫的是銅河水,妹兒麼只愛富家弟。”
女娃子說:“瞎唱。”
劉太清問她:“哎,你婆婆咋個沒有給你剃度?”
女娃子說:“本來說,今年四月初八剃的,我不肯。”
劉太清問:“你不肯當尼姑?”
女娃子說:“不甘心在這山上待一輩子。”
劉太清不開腔。
女娃子嘴一撇,說:“可不做尼姑,我還做得來啥子?”
劉太清說:“喫佛家飯好,體面,又受菩薩護佑。”
女娃子的眼淚水順到臉蛋兒流。
劉太清見到,趕忙說:“女娃子,我打胡亂說的,你莫哭。”
女娃子站起來,默默地朝山上走,劉太清挑起擔子,跟着。
這天夜裏,劉太清沒有睡覺,他爬到高處坐着,時不時站起來,朝山下望一眼,望一眼山下,又望一眼觀音庵,望一眼老尼姑她們睡的那口洞。他想,女娃子這時候是不是也睡不着?身上一層層冒着細汗,哎呀,女娃子那副要哭要哭的樣兒,真是揪得他心窩子痛。偶有一兩聲獾子叫,個女娃子呀,你咋個不肯把話說透嘞,可他不是也不敢把話說透麼?清風吹來,山上的樹林子在響,他歡喜女娃子,他曉得,女娃子也必必是歡喜他的,這便是石匠些唱的情愛喲,這便是說不清道不明的情愛喲。
那四個石匠從嘉定城出來,沒有走白廟場,而是坐船到楊家,在楊家場買了糧油酒菜,再過麥子坳,沿鴨口山山回官帽山。這條路要比走白廟多費點船錢,也要更快當點,到山腳下時,天還沒有黑,劉太清與另三個石匠正等着他們。兩個石匠先將洋芋和糧油、酒菜挑上山,其餘的人抽出六十吊錢,再把大頭使土布包起,埋到了對面的山坡上,插上樹丫子作記號。
將銅錢埋到了泥巴頭,劉太清的心纔算落了地,這幾籮兜銅錢夠他們過一陣闊綽日子了,至於花完了咋個辦,劉太清想不到那麼遠。他們好幾日沒有沾過油葷,這會兒,只想大喫大喝一頓。他叫上劉譚氏,同石匠們一起,走到帽兒頂,將白宰雞、油燙鴨、滷蹄花和幾罈子燒酒擺出來,點起一團篝火,圍到坐。石匠們個個都脫成了光膀子,抱起罈子,大口喝,燒酒順到嘴角,流到胸膛,流過黑黝黝的皮膚。
一個石匠說:“打一個碌碡,連石料一起,才掙三百文,只怕把嘉定城的碌碡都打完,還掙毬不到恁呃多錢。”
一個石匠說:“日他的娘,那魯班會會首,可年年都有恁多錢兒收。”
一個石匠吼:“該殺。”
一個石匠說:“除了魯班會,還有賣匹頭的三黃會,裁衣裳的軒轅會,打鐵的老君會,賣膏藥的藥王會……”
一個石匠說:“數不盡喲。”
一個石匠吼:“都該殺。”
劉譚氏說:“喫酒。”
一個石匠說:“晚上老子就捱到這酒罈子睡。”
一個石匠說:“噫,像條毬,要挨就捱到錢串子睡。”
一個石匠說:“噫,像條毬,要挨就捱到牛兒他娘睡。”
一個石匠說:“呔,爛眉日眼物,你就配捱到老尼姑睡。”
劉譚氏說:“喫酒。”
……
編輯丨十三
圖片來自電影《菊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