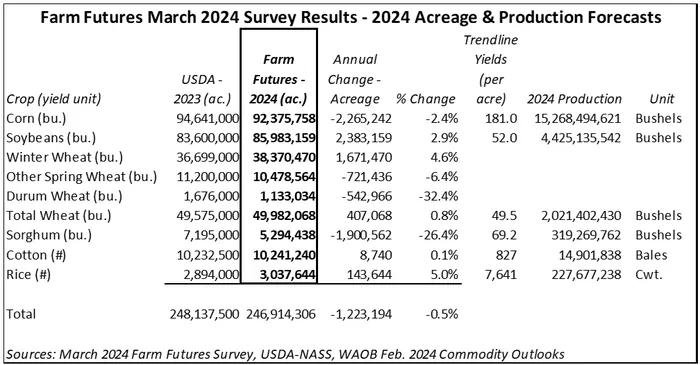小說《柿園結義三兄弟》連載二、楊母遺愛辭世/李子豐(西安)
摘要:”管官當差,母親端一碗清水擺在院庭中央,雙腿跪下去禱告天地三界十方萬靈之神保佑。管官想跟着瘋,母親和藹地一奓手,“猴去,猴去。
楊母遺愛辭世
作者:李子豐
渭水一石,其泥數鬥,且溉且糞,長禾長黍。寶雞峽乾渠全長215公里,覆蓋13縣170萬畝土地。1971年7月15日,渠首開閘放水,坡邊村前渭水滾滾,一渠兩岸的農人奔走相告,彈冠相慶,好光景來了。土是農之根,水是農之脈,有滿漾漾的一渠水澆地,就不怕卡脖春旱,“荒春三,苦七月”的日子,一去不復返了。順口溜道:釘耙能摟土,牽着龍頭走,荒坡變水田,畝產一石九。
這一天,坡邊村悲喜交集,楊母遺愛辭世,撂下一家七口,一個父親,六個兒子。世上痛無醫母藥,靈前哭倒斷腸人。歲月不居,天不永年,流淌不盡的乾渠渭水,猶如楊家人漣漣的淚水。“藍田日暖玉生煙,滄海月明珠有淚。”這不僅是逝者的不幸,更多的是生者的痛楚。對於失去母親的六個兒子來說,天寒了不再暖,山禿了不再綠,夜黑了不再明。
精氣聚合而生,循環不息爲命,與天地相往來。若肺氣不足,眼多白花,故見白鬼,若腎精不足,眼多黑花,故見黑鬼,由此心生黑白無常。無常爲閻王當差,尖帽“一見生財”,顙門有“令”,一手攥威嚴的令箭,一手提冰冷的鐵鏈,在天空不分晝夜地巡邏查訪,尋找在生死簿上勾銷姓名的魂魄。在關中農村,世代迷信“生有時辰,死有地方”,更相信一個人的壽數早已註定,一天不少,一天不多,閻王叫你三更死,誰敢留人到天亮。
這一年秋,楊家三子管官上小學五年級,根本不知這個“死”字,在傳統文化概念裏的不同定義。佛祖死曰涅槃,高僧死曰圓寂,道士死曰羽化,伊斯蘭教徒死曰認主歸真,皇帝死曰駕崩,諸侯死曰薨,大夫死曰卒,士死曰不祿,庶人死曰亡。一個草民百姓死了,常常稱之亡人,老伴遺孀稱之未亡人。民間喪服講究,以五服(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緦麻)爲基本等級,以人倫社會親親、尊尊關係爲經緯,配合名分、長幼與從屬關係的轉換,將人與人之間各種親疏遠近、情誼薄厚的相對關係蘊涵其中。一旦出五服,至親至密的宗族血脈關係相對疏鬆,一籠統地稱爲某姓某氏一枝葉。
在管官心裏,有說不清、理還亂的一團情結,那就是對母親的綿綿思念。他記得母親說過一個鄉間謎語(筷子):肥瘦高低一個樣,竹家村裏是家鄉;喫進多少辛酸味,終身不得見爹孃。一家人端碗喫麪,大哥二哥的筷子捉得高梢梢的,好象踩着高蹺,管官的筷子捉得低矮。母親瞅一眼,又瞅一眼,輕輕地笑了,“喫飯筷子捉得高,這個娃長大了,一定會離開家門,走得遠遠的。喫飯筷子捉得低,這個娃就是成人了,娶了媳婦,還在門邊頭打轉轉。” 管官哧溜一下,右手高抬到筷子頂頭,惹得大哥二哥一齊笑了。母親撩起圍裙擦溼手,“一樹之果有酸有甜,一母之子有愚有賢;你們兄弟六個,或者愚,或者賢,或者不愚不賢,就象手指頭有長有短,這都是天意。”母親從地上捏起一根火柴,又思思量量地說,愚有愚的長處,賢有賢的短處,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天地這麼寥廓,社會這麼寬展,一個人有一個人的活法,一切都要順其自然;是鳥,你就去天上逮食,是魚,你就去水中覓食,是雞,你就去土裏刨食。
光陰荏苒,酷夏飛逝。野曠沙岸淨,天高秋月明。霜降過後,大雁朝西北遷徙,十五六隻結伴,二三十隻結夥,爲補充能量,時常落地喫麥青。有時夜以繼日,匆匆趕路,嘎——嘎——嘎——使得夜空更加苦寒淒冷,更加空曠無物。楊母在世時,土炕一整夜暖烘烘的。楊母歿了,土炕變臉,前半夜熱,後半夜涼,夜殘奇靜,油燈如豆。管官蜷縮被窩裏,冷得睡不安穩,夜空雁叫,聲聲入耳。在容量有限的小小顙殼裏,父母就是一個村童的天和地——
“六月白雨,親似閨女。”夏至雨點值千金,兩場透雨就有秋糧餵豬,豬價一定飛漲,家家多養兩頭,下午放學拔豬草,那是村童必修課。管官跑得遠吊,有時十幾裏,滿滿一擔籠豬草。一回到家,父親接過手提到圈裏餵豬,又擰身一聲囑咐,“一爪拐棗,窗臺上。”父親時常跟集趕會,買十幾爪扭顙歪脖的拐棗,帶回家給兒子們啖嘴。母親笑吟吟的,叫他洗手喫饃,撫摸他刺蝟一樣的頭髮。他依偎母親腿胯,一口饃,一口拐棗,香甜透了。有時餓急了,不洗手便喫饃,嘴裏有一絲苦味,那是豬草汁液殘留手上了。一入冬,麥田降落大雁,雁屎是軟化的糊狀麥青,倒是餵豬的發酵飼料。經常看見,老漢在村道拾牛糞肥田,村童在麥田拾雁屎餵豬。
碧空如洗,雁翼翽翽。一隊大雁飛行,一會兒排成“人”,一會兒排成“一”,不停地變換着。管官瞭望,心裏好奇,“娘,大雁會寫字,誰教的?”一羣村童圍攏過來,母親嗓音清亮,“老天爺教的,大雁學會了,又來教娃娃。二十年後,無論莊稼漢,無論國家幹部,男人要象男人,女人要象女人。”這些村童似懂非懂,嗷地一聲,一窩蜂似的跑散了。管官想跟着瘋,母親和藹地一奓手,“猴去,猴去。”“爺婆爺婆照我來,我給你擔水飲馬來;誰遮我的陽陽,狗喫誰的腸腸。”“花喜鵲,尾巴長,娶了媳婦忘了娘……”
母親不等天落黑,把洗曬的衣裳收回屋裏,“一入夜,天上有賊(流)星,落到娃娃衣裳上,手腳就不會乾淨,小時偷秤,長大偷城,一直到老成不了人。”管官當差,母親端一碗清水擺在院庭中央,雙腿跪下去禱告天地三界十方萬靈之神保佑。父親去有水的土溝挖蘆葦根,熬煎湯汁喝下來,紅疹子滲出來了。夜觀月亮,一坨灰暗影跡,一起一伏,忽縮忽脹,那是月宮疥蛙。左鄰小兒發燒,母親把一隻疥蛙用瓷碗反扣在小兒肚皮上,那是滲涼的冷血生物,一炷香工夫燒退了。世界上有一種最美的聲音,那就是天下母親的呼喚。右鄰小兒從壕岸跌落,把三魂六魄嚇散了,天黑實,夜靜謐,母親幫着念口訣招魂,“山高路遠不得到,清水化氣把書捎……”
這是管官夢境,母親在孝村鋤地,鋤得熱汗長淌,前胸後背溻溼了。“娘渴了。”一瓷罐水,放上糖精,舌尖一嘗,甜得合適。已經立冬三日,管官手提水罐,來到孝村東頭,看見一摟大槐樹,一隻老鴰高坐樹頂,沉默不語,儀態高古。他想起傳說,丁蘭經常打罵母親,看到老鴰反哺,後悔莫及,母親卻一顙撞死了。丁蘭伐木刻成母親,夏穿單,冬裹棉,一天伺候三頓飯,早早晚晚都請安。
按照夢中記憶,一罐糖水緩緩淋下去。一綹麥青頓時綠亮,快要張嘴說話了。他在心裏默默祈禱,“娘,你若解渴了,就指示樹頂上的老鴰叫兩聲,朝咱坡邊村飛去。”老鴰哇地一聲,全身一個後挫,朝相反的方向飛走了。蒼穹混沌不清,飄灑淡淡雪花。管官心頭一熱,“我娘生前最愛下雪,說雪花是天宮白麪。”忽然,從孝村傳來天真無邪的童謠——
雪花兒飄
雪花兒綻
老天爺爺下白麪
下滿了缸
下滿了罐
我媽給我擀長面
作者簡介
李子豐,陝西扶風縣人,17歲奔赴新疆喀什203部隊服役四年。1980年考入寶雞師範學院中文系,1982年在《四川文學》發表小說《山溝軼事》,遂被《作品與爭鳴》轉載,引起廣泛爭論。1986年調入中航工業西安制動公司(514廠),任宣傳部副部長,中航作協會員,有著作《蝶變》。
(世間風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