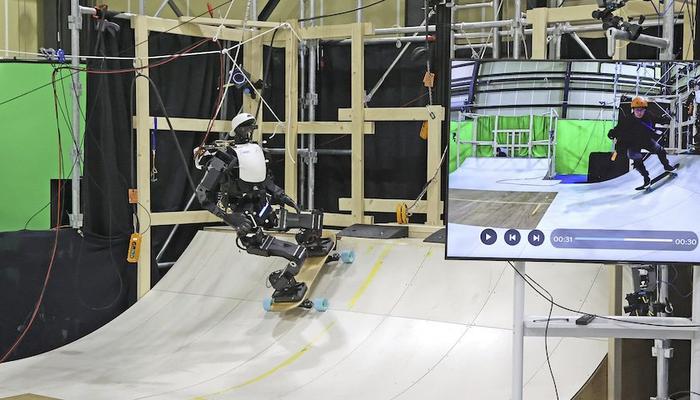张謇在甲午之战前后的变脸 | 这样做人太不厚道
"\u003Cdiv\u003E\u003Cdiv class=\"pgc-img\"\u003E\u003Cimg src=\"http:\u002F\u002Fp9.pstatp.com\u002Flarge\u002Fpgc-image\u002F0e879fdd149a41d0890c60d625899676\" img_width=\"355\" img_height=\"383\" alt=\"张謇在甲午之战前后的变脸 | 这样做人太不厚道\" inline=\"0\"\u003E\u003Cp class=\"pgc-img-caption\"\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u002Fdiv\u003E\u003Cp\u003E吾友李礼以大著《求变者》见赠。该书着重写了清末到民初十位士大夫在内政腐败、外侮频加、民生艰难的时局中,追求由变而日新之道。作者游其地,读其书,析其人,考其思想流变,解其所处历史大势。为我近来所读的一本不可多得的好书。\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清光绪甲午恩科(1894)状元、江苏南通人张謇是书中十人之一。在清末前赴后继、薪火相传的“求变”之路中,张謇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人物。“状元实业家”已成其历史脸谱,其在南通兴办实业、教育、进行市民自治所取得成就亦为今人所肯定,张謇至今仍是南通这座滨海城市的荣光。\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在清末那个大时代里,求变的人不知凡几,譬如行旅,前路堵塞而求改弦易辙,是人之本能。关键是知“求变”之必须,而需有“善变”之才能。张謇可谓当得起“善变”。\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张謇少年神童、青年名士、中年状元,加上曾入吴长庆幕,随其驻守朝鲜多年,其才华,其见识自是非凡。只是我总认为张謇为人是太聪明,太会变通了,在重大的历史时刻,他总能尽快地占据道义优势,掌握话语权,并与当时实力最强者结盟。\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以张謇亲身经历两大历史事件为例,一位甲午中日之战,二为武昌起义而致清帝逊位,民国诞生。张謇的所作所为体现其“善变”之特点。\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甲午恩科,张謇因为帝师、军机大臣翁同龢的多方运作,才得以大魁于天下。翁师傅善于利用权势而市恩,来延揽天下名士为自己的门生,从而增强在官场的实力。张謇这位同乡名士,早就入了求才若渴的翁师傅彀中。为了张謇得状元,翁同龢可谓操碎了心。甲午殿试排名第一的读卷大臣亦是状元出身的张之万,本来张之万心目中的状元人选是湖南茶陵籍的尹铭绶。这尹是做过两广总督的谭钟麟孙女婿,谭延闿是其妻子的亲叔叔。\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翁同龢极力游说张之万同意自己的状元人选,还做通了收卷官翰林院修撰黄思永的工作。——翁师傅权倾朝野,黄思永当然要给面子。收卷时,黄看到张謇试卷中有一字空白,有科考经验的人知道,这是挖了一个错字,却忘了填补正确的字。《世载堂杂忆》记录:“黄即取怀中笔墨,为之补书。”黄思永又看到一处错,张謇将单独一个“恩”字抬格,上面缺了一个“圣”字——清代行文,逢“圣”“皇帝”必须抬格表示尊重。黄思永又给张謇补了个“圣”字。\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有翁同龢的力挺,加上收卷官的擦屁股,张謇四十一岁那年中了状元,尹铭绶屈居榜眼。茶陵谭家大概没有状元命。光绪甲辰科(1904)中国最后一次会试中,谭延闿得了第一名(即会元),殿试只得了二甲第三十五名。据说他进三鼎甲本来没问题,慈禧太后最后圈前三名时,看到谭延闿是湖南籍的,又姓谭,便心生恶感(因为和谭嗣同同姓同省),他就被赶出了一甲。\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张謇当然对翁同龢所谓恩惠没齿难忘。那一年,正碰上因为朝鲜问题中日纷争。因为他在朝鲜历练多年,翁师傅极为看重他的意见,他事实上成为翁同龢在中日问题上最重要的决策参谋。\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翁同龢的另一位门生王伯恭在《蜷庐随笔》中载:\u003C\u002Fp\u003E\u003Cblockquote\u003E\u003Cp\u003E日本闻叶提督(注:叶志超)率兵入其国(注:即朝鲜),大惊,以为轻背前约,是必将夷为郡县也,因议大出师,与中国争。(注:朝鲜“甲申政变”后,日本同清朝订立了《天津会议专条》,约定中日两国同时从朝鲜撤兵,嗣后两国出兵朝鲜须互相通知。甲午之战前,清廷应朝鲜王室之邀出兵平东学党起义,日本以此为借口而已。其实当时日本政府希望清廷不正式照会该国而擅自出兵,落下背约之口实。)事为合肥(注:即李鸿章)所闻,亟奏请撤戍。而是时张季直(张謇字季直)新状元及第,言于常熟,以日本蕞尔小国,何足以抗天兵?非大创之,不足以示威而免患。常熟韪之,力主战。合肥奏言不可轻开衅端,奉旨切责。\u003C\u002Fp\u003E\u003C\u002Fblockquote\u003E\u003Cp\u003E翁同龢在当户部尚书时,奏定十五年之内不得添置一枪一炮。翁利用自己对亲政未久、年轻气盛的光绪帝巨大的影响力,促成了浪战,其中张謇又以自己对翁同龢的影响力,坚定了翁主战的决心。\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战败后,李鸿章成了最大的背锅侠,代表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天下许多不明白内情的士林清流之辈,皆曰李鸿章该杀。而张謇马上脸变过来,上疏弹劾李鸿章,把甲午战败的所有责任归咎于李鸿章。张謇毕竟是状元,文章做得好,用笔如刀。他在奏疏开头就说:\u003C\u002Fp\u003E\u003Cblockquote\u003E\u003Cp\u003E直隶总督李鸿章,自任北洋大臣以来,凡遇外人侵侮中国之事,无一不坚持和议。天下之人,以是集其诟病,以为李鸿章主和误国,而窃综其前后心迹观之,则二十年来坏和局者,李鸿章一人而已。\u003C\u002Fp\u003E\u003C\u002Fblockquote\u003E\u003Cp\u003E在这封奏疏中,张謇不再像战前的众多国人那样从道德层面褒主战为有血气是爱国忠君,贬主和为畏葸避战,丧我中华志气。而是认为主战与主和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是李鸿章误国甚深,开战则打不赢别人,和谈则没有资本。其中几段话堪称诛心之论:\u003C\u002Fp\u003E\u003Cblockquote\u003E\u003Cp\u003E自来中外论兵,战和相济,西洋各国,惟无一日不存必战之心,故无一人敢败已和之局。李鸿章兼任军务、洋务三十余年,岂不知之?\u003C\u002Fp\u003E\u003C\u002Fblockquote\u003E\u003Cblockquote\u003E\u003Cp\u003E计无一而不工,气无一而不壮。而言及军事,则仅任能守天津;言及军械,则转而委过户部。试问以四朝之元老,筹三省之海防,统胜兵精卒五十营,设机厂、学堂六七处,历时二十年之久,用财数千万之多,一旦有事,但能漫为大言,胁制朝野,曾无一端立于可战之地,以善可和之局。稍有人理,能无痛心?此又徇纵欺罔,骄蹇黠猾,兼而有之,见于事外而坏及事中矣。.........而李鸿章之非特败战,并且败和,无一人焉以发其覆。\u003C\u002Fp\u003E\u003C\u002Fblockquote\u003E\u003Cp\u003E甲午之战败,原因是多方面的,概言之是清朝政治腐败,内斗严重,无论从战备、军事组织及执行力远不如日本,战败是毫不意外的结局。李鸿章当然要负相当的责任,但他身处其间,只能做“裱糊匠”弥缝多年,消极避战是不得已的事。别人责备李鸿章,犹不失春秋责备贤者之意。唯独张謇上奏劾李鸿章,是难以让人服气的。李鸿章有责任,难道张謇和他的恩师翁同龢就没有责任?开战前,张謇和座师义正辞严主战,如果打赢了,那是他们主战者的首功;而战败了,他们这些主战者没有责任,责任还是兴办北洋水师的李鸿章。因为你李鸿章不积极备战,所以连与日本和谈亦没有筹码。“惟无一日不存必战之心,故无一人敢败已和之局”,这道理是不错的,可由张謇用来指责李鸿章,就真的理直气壮?他对战前怂恿翁同龢主战,没有一点内疚之心?\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黄濬在《花随人圣庵摭忆》中说了一段比较公允的话:\u003C\u002Fp\u003E\u003Cblockquote\u003E\u003Cp\u003E予以为中日甲午一战,原因甚多,从世界大势及中日国情论之,不勃发于甲年,亦必忽作于乙岁。唯就甲午年各方面情势论之,我国政局中朋党角抵,首促成之者,自为翁、李之隙。唯文恭(翁同龢)之极力窘文忠(李鸿章)以快意,则那拉氏族亦不得逞其灭洋之志也。若就本事件言,则不止翁须负责任,李亦须负责任。\u003C\u002Fp\u003E\u003C\u002Fblockquote\u003E\u003C\u002Fdiv\u003E"'.slice(6, -6),
groupId: '67145503479452144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