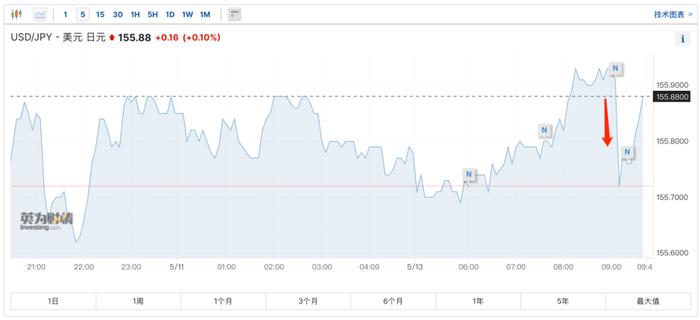張謇在甲午之戰前後的變臉 | 這樣做人太不厚道
"\u003Cdiv\u003E\u003Cdiv class=\"pgc-img\"\u003E\u003Cimg src=\"http:\u002F\u002Fp9.pstatp.com\u002Flarge\u002Fpgc-image\u002F0e879fdd149a41d0890c60d625899676\" img_width=\"355\" img_height=\"383\" alt=\"張謇在甲午之戰前後的變臉 | 這樣做人太不厚道\" inline=\"0\"\u003E\u003Cp class=\"pgc-img-caption\"\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u002Fdiv\u003E\u003Cp\u003E吾友李禮以大著《求變者》見贈。該書着重寫了清末到民初十位士大夫在內政腐敗、外侮頻加、民生艱難的時局中,追求由變而日新之道。作者遊其地,讀其書,析其人,考其思想流變,解其所處歷史大勢。爲我近來所讀的一本不可多得的好書。\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清光緒甲午恩科(1894)狀元、江蘇南通人張謇是書中十人之一。在清末前赴後繼、薪火相傳的“求變”之路中,張謇是一個不容忽視的人物。“狀元實業家”已成其歷史臉譜,其在南通興辦實業、教育、進行市民自治所取得成就亦爲今人所肯定,張謇至今仍是南通這座濱海城市的榮光。\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在清末那個大時代裏,求變的人不知凡幾,譬如行旅,前路堵塞而求改弦易轍,是人之本能。關鍵是知“求變”之必須,而需有“善變”之才能。張謇可謂當得起“善變”。\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張謇少年神童、青年名士、中年狀元,加上曾入吳長慶幕,隨其駐守朝鮮多年,其才華,其見識自是非凡。只是我總認爲張謇爲人是太聰明,太會變通了,在重大的歷史時刻,他總能儘快地佔據道義優勢,掌握話語權,並與當時實力最強者結盟。\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以張謇親身經歷兩大歷史事件爲例,一位甲午中日之戰,二爲武昌起義而致清帝遜位,民國誕生。張謇的所作所爲體現其“善變”之特點。\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甲午恩科,張謇因爲帝師、軍機大臣翁同龢的多方運作,才得以大魁於天下。翁師傅善於利用權勢而市恩,來延攬天下名士爲自己的門生,從而增強在官場的實力。張謇這位同鄉名士,早就入了求才若渴的翁師傅彀中。爲了張謇得狀元,翁同龢可謂操碎了心。甲午殿試排名第一的讀卷大臣亦是狀元出身的張之萬,本來張之萬心目中的狀元人選是湖南茶陵籍的尹銘綬。這尹是做過兩廣總督的譚鍾麟孫女婿,譚延闓是其妻子的親叔叔。\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翁同龢極力遊說張之萬同意自己的狀元人選,還做通了收卷官翰林院修撰黃思永的工作。——翁師傅權傾朝野,黃思永當然要給面子。收卷時,黃看到張謇試卷中有一字空白,有科考經驗的人知道,這是挖了一個錯字,卻忘了填補正確的字。《世載堂雜憶》記錄:“黃即取懷中筆墨,爲之補書。”黃思永又看到一處錯,張謇將單獨一個“恩”字抬格,上面缺了一個“聖”字——清代行文,逢“聖”“皇帝”必須抬格表示尊重。黃思永又給張謇補了個“聖”字。\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有翁同龢的力挺,加上收卷官的擦屁股,張謇四十一歲那年中了狀元,尹銘綬屈居榜眼。茶陵譚家大概沒有狀元命。光緒甲辰科(1904)中國最後一次會試中,譚延闓得了第一名(即會元),殿試只得了二甲第三十五名。據說他進三鼎甲本來沒問題,慈禧太后最後圈前三名時,看到譚延闓是湖南籍的,又姓譚,便心生惡感(因爲和譚嗣同同姓同省),他就被趕出了一甲。\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張謇當然對翁同龢所謂恩惠沒齒難忘。那一年,正碰上因爲朝鮮問題中日紛爭。因爲他在朝鮮歷練多年,翁師傅極爲看重他的意見,他事實上成爲翁同龢在中日問題上最重要的決策參謀。\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翁同龢的另一位門生王伯恭在《蜷廬隨筆》中載:\u003C\u002Fp\u003E\u003Cblockquote\u003E\u003Cp\u003E日本聞葉提督(注:葉志超)率兵入其國(注:即朝鮮),大驚,以爲輕背前約,是必將夷爲郡縣也,因議大出師,與中國爭。(注:朝鮮“甲申政變”後,日本同清朝訂立了《天津會議專條》,約定中日兩國同時從朝鮮撤兵,嗣後兩國出兵朝鮮須互相通知。甲午之戰前,清廷應朝鮮王室之邀出兵平東學黨起義,日本以此爲藉口而已。其實當時日本政府希望清廷不正式照會該國而擅自出兵,落下背約之口實。)事爲合肥(注:即李鴻章)所聞,亟奏請撤戍。而是時張季直(張謇字季直)新狀元及第,言於常熟,以日本蕞爾小國,何足以抗天兵?非大創之,不足以示威而免患。常熟韙之,力主戰。合肥奏言不可輕開釁端,奉旨切責。\u003C\u002Fp\u003E\u003C\u002Fblockquote\u003E\u003Cp\u003E翁同龢在當戶部尚書時,奏定十五年之內不得添置一槍一炮。翁利用自己對親政未久、年輕氣盛的光緒帝巨大的影響力,促成了浪戰,其中張謇又以自己對翁同龢的影響力,堅定了翁主戰的決心。\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戰敗後,李鴻章成了最大的背鍋俠,代表清政府與日本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天下許多不明白內情的士林清流之輩,皆曰李鴻章該殺。而張謇馬上臉變過來,上疏彈劾李鴻章,把甲午戰敗的所有責任歸咎於李鴻章。張謇畢竟是狀元,文章做得好,用筆如刀。他在奏疏開頭就說:\u003C\u002Fp\u003E\u003Cblockquote\u003E\u003Cp\u003E直隸總督李鴻章,自任北洋大臣以來,凡遇外人侵侮中國之事,無一不堅持和議。天下之人,以是集其詬病,以爲李鴻章主和誤國,而竊綜其前後心跡觀之,則二十年來壞和局者,李鴻章一人而已。\u003C\u002Fp\u003E\u003C\u002Fblockquote\u003E\u003Cp\u003E在這封奏疏中,張謇不再像戰前的衆多國人那樣從道德層面褒主戰爲有血氣是愛國忠君,貶主和爲畏葸避戰,喪我中華志氣。而是認爲主戰與主和不是問題的關鍵,關鍵是李鴻章誤國甚深,開戰則打不贏別人,和談則沒有資本。其中幾段話堪稱誅心之論:\u003C\u002Fp\u003E\u003Cblockquote\u003E\u003Cp\u003E自來中外論兵,戰和相濟,西洋各國,惟無一日不存必戰之心,故無一人敢敗已和之局。李鴻章兼任軍務、洋務三十餘年,豈不知之?\u003C\u002Fp\u003E\u003C\u002Fblockquote\u003E\u003Cblockquote\u003E\u003Cp\u003E計無一而不工,氣無一而不壯。而言及軍事,則僅任能守天津;言及軍械,則轉而委過戶部。試問以四朝之元老,籌三省之海防,統勝兵精卒五十營,設機廠、學堂六七處,歷時二十年之久,用財數千萬之多,一旦有事,但能漫爲大言,脅制朝野,曾無一端立於可戰之地,以善可和之局。稍有人理,能無痛心?此又徇縱欺罔,驕蹇黠猾,兼而有之,見於事外而壞及事中矣。.........而李鴻章之非特敗戰,並且敗和,無一人焉以發其覆。\u003C\u002Fp\u003E\u003C\u002Fblockquote\u003E\u003Cp\u003E甲午之戰敗,原因是多方面的,概言之是清朝政治腐敗,內鬥嚴重,無論從戰備、軍事組織及執行力遠不如日本,戰敗是毫不意外的結局。李鴻章當然要負相當的責任,但他身處其間,只能做“裱糊匠”彌縫多年,消極避戰是不得已的事。別人責備李鴻章,猶不失春秋責備賢者之意。唯獨張謇上奏劾李鴻章,是難以讓人服氣的。李鴻章有責任,難道張謇和他的恩師翁同龢就沒有責任?開戰前,張謇和座師義正辭嚴主戰,如果打贏了,那是他們主戰者的首功;而戰敗了,他們這些主戰者沒有責任,責任還是興辦北洋水師的李鴻章。因爲你李鴻章不積極備戰,所以連與日本和談亦沒有籌碼。“惟無一日不存必戰之心,故無一人敢敗已和之局”,這道理是不錯的,可由張謇用來指責李鴻章,就真的理直氣壯?他對戰前慫恿翁同龢主戰,沒有一點內疚之心?\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黃濬在《花隨人聖庵摭憶》中說了一段比較公允的話:\u003C\u002Fp\u003E\u003Cblockquote\u003E\u003Cp\u003E予以爲中日甲午一戰,原因甚多,從世界大勢及中日國情論之,不勃發於甲年,亦必忽作於乙歲。唯就甲午年各方面情勢論之,我國政局中朋黨角抵,首促成之者,自爲翁、李之隙。唯文恭(翁同龢)之極力窘文忠(李鴻章)以快意,則那拉氏族亦不得逞其滅洋之志也。若就本事件言,則不止翁須負責任,李亦須負責任。\u003C\u002Fp\u003E\u003C\u002Fblockquote\u003E\u003C\u002Fdiv\u003E"'.slice(6, -6),
groupId: '67145503479452144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