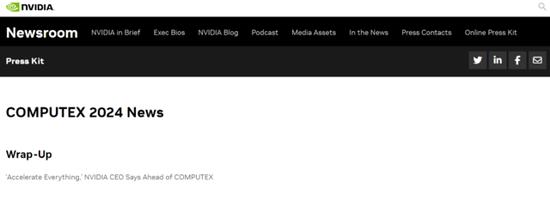科創高地投資銳減?以色列背後的中國資本怎麼了
摘要:\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這樣的景象與兩三年前的情況有一些不同,以色列駐上海總領事館華東地區經濟商務處負責人向經濟觀察報回憶:“2014年至2017年,中國企業投資以色列趕上一波投資熱潮,當時響應國家號召鼓勵企業和投資機構走出去,許多龍頭企業也在這個期間積極部署和調整國際市場戰略。”\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中國金主畫像\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太庫科技以色列總經理鄭小星用了一個現象,來說明以色列科創資源在與中國這樣的資本、市場大國對接上的不匹配:以色列有一家非常知名的科研機構,該研究所的研究範圍橫跨多個重要領域,如生物、醫藥、農業,每年的技術轉移到海外的收入高達幾個億美金,但遺憾的是,在中國幾乎沒有——儘管,對雙方來說,技術的成色不成問題,交易的需求也不成問題。
"\u003Cimg src=\"http:\u002F\u002Fp1.pstatp.com\u002Flarge\u002Fpgc-image\u002FRXNpG4N7gOSeTe\" img_width=\"800\" img_height=\"400\" alt=\"科創高地投資銳減?以色列背後的中國資本怎麼了\" inline=\"0\"\u003E\u003Cp\u003E(圖片來源:壹圖網)\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經濟觀察報 記者 李紫宸 梁曉純\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strong\u003E沈家虹 \u003C\u002Fstrong\u003E2019年7月7日,在北京CBD一處裝扮一新的辦公樓中,以色列人AmirGal-Or創辦的中以跨境創新平臺——INNONATION已經辦了第五屆投融資交流會,這是一場數字健康專場,來自這個國家的慷慨激昂的年輕人,爲臺下觀衆推介他們的創新技能。\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具有視聽能力的智能眼鏡,爲嬰兒輸送氣霧劑藥物的頭巾式輸送系統、革命性的糖尿病治療方法等等,來自以色列的科創項目路演依然層出不窮,這些實用並具有專業主義的新技術,充滿了以色列猶太人富於探索的精神。在外界看來,這個國家的立國之本就是科技創新,它的一切生態就是圍繞科創而展開。\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以色列擁有超過6600家科創企業,對於只有800萬人口、2.5萬平方公里的國土,這甚至顯得有一些“擁擠”。問及天然缺乏市場的以色列科創企業是否迫切需要一個更大的市場,INNONATION董事長AmirGal-or非常肯定得說:“需要”。“中國和以色列天然地聽起來匹配度特別高,比較適合‘一見鍾情’,這符合人們的想象。”太庫科技全球CEO唐亮告訴經濟觀察報。\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但INNONATION的數據庫發現,剛剛過去的半年,中國企業對以色列的投資並不盡如人意。INNONATION執行董事薛冰說,“你每個月看到的以色列那些數量不小的投資,但很難找到中國人的身影,反而是美國和歐洲那邊始終如一的高頻。”\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儘管以色列大量的科創項目依然源源不斷地來到中國,但去往以色列的投資數量卻減少明顯。\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來自中以跨境創新服務平臺——INNONATION的數據(以色列經濟部亦引用該機構的數據)顯示,2019年上半年,中國對以投資一共發生了15筆,其中公開投資額的投資13筆,總投資額約爲3.65億美元,而去年同期約爲5.7億美元。\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這與往年相比,出現了不小的下滑:2018年、2017年和2016年,中國對以色列的投資和併購數量分別爲45筆、42筆和35筆;完成投資總額分別爲9.09億美元、5.18億美元和4.74億美元。\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13筆投資\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事實上,在過去半年中國對以投資中,其中3筆來自臺灣,剩下的投資主體多以國資背景爲主。\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唐亮在出任太庫科技全球CEO之前負責太庫科技美國市場,熟知硅谷科創市場的動向。唐亮認爲,儘管長期來看,資本出海一直存在困難,但現在似乎處於一個更加微妙的時刻:過去兩年中,中國對美科創投資狀況發生了較大的改變,投資量少了90%多以上,這與美國對外資的限制有關。\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2017年11月,在美國國會提出並經過長達數月的和解進程後,2018年“外國投資風險評估現代化法案”(FIRRMA)(以下簡稱FIRRMA法案)由國會兩院通過,並於2018年8月13日簽署後正式生效。FIRRMA法案代表了自2007年以來首次對美國外資投資委員會(CFIUS))的流程進行立法改革,預示着CFIUS對美國外國投資審查範圍的大幅擴展。\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國有資本在美國的投資受到了限制,可以說是完全停止,具有國有資本的基金都受到限制,包括國有背景的孵化器現在也都不做,但民營資本還可以投美國。(這種情況下)國有資本不得不再轉向其它的市場去看。”唐亮說。\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與此同時,唐亮認爲,投資方也會對自身的風險有所考量:“即使是(資金)已經出去了,現在也不太願意去投,例如智能機器人,所有這些國內特別需要同時美國比較領先的科技技術,事實上會比較猶豫。”\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薛冰回憶說:“2014年的時候,中國很多的風投會去以色列,風投機構本身也開始裂變,老牌的基金中,很多合夥人選擇出來單幹。無數基金公司都去跟以色列對接,我碰到很多人,都是國內募資的時候打着這個旗號,去拿以色列的技術和國內的上市公司或者風投公司做聯動。”\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但現在平息了很多。AmirGal-or認爲:投資減少與中國跨境投資的規定有關,也和中國當下的經濟形勢以及科技商業活動的週期相關。與此同時,絕大多數用於風險投資和跨境交易的自由資金都掌握在國有企業手中,而非私營企業。\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2019年6月4日,以色列初創公司Guardknox宣佈完成2100萬美元的A輪融資,該輪融資由FraserMcCombsCapital領投,由汽車技術領導者Fau-recia,SAICCapital(上汽集團旗下資本平臺)等公司跟投。這家公司於2016年創立,主要從事汽車網絡安全產品研發,包括結合軟件和硬件的全面端到端解決方案,爲汽車行業提供高性能計算平臺和附加服務。\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6月10日,以色列另一家公司In-noviz宣佈完成C輪融資,募集資金總額1.7億美元,該輪融資由深創投領投,上海聯新資本、招商局資本和兩家以色列本土機構跟投。Innoviz研發固態LiDAR傳感器和感知軟件,激光雷達傳感器通過激光照射目標物體,並測量反射回來的脈衝從而得出物體距離,是包括Uber和Lyft在內的許多自動駕駛汽車系統的核心部件,可應用於機器人、安全和農業科技等領域。\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這是過去一個月中,中國對色列僅有的兩筆投資。根據INNONATION的數據(以色列經濟部也引用了這一數據),在剛剛過去的6月份,在以色列獲投的31筆海外投資中,美國爲15筆,其餘境外投資分別來自荷蘭(3個)、中國(2個)、英國(2個)、法國(2個)、韓國(2個)、加拿大(1個)、印度(1個)、新加坡(1個)、日本(1個)和愛爾蘭(1個)。\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薛冰注意到,來自中國的這兩筆投資呈現出兩個特點,一是均爲汽車相關領域,巧合的是,6月份商務部等三部委發佈《推動重點消費品更新升級暢通資源循環利用實施方案 (2019-2020年)》,要求“大力推動汽車產業電動化、智能化”,二是投資主體均爲國資產業或者資本平臺,這反映出國資在當前跨境高科技投資中的領導力和牽引力。\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薛冰補充說:“2016年外匯管理收緊ODI投資後,中國投資以色列本土基金項目幾乎沒有,我們一直在嘗試爲美元基金募資也沒有成功。”\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中國金主畫像\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太庫科技以色列總經理鄭小星用了一個現象,來說明以色列科創資源在與中國這樣的資本、市場大國對接上的不匹配:以色列有一家非常知名的科研機構,該研究所的研究範圍橫跨多個重要領域,如生物、醫藥、農業,每年的技術轉移到海外的收入高達幾個億美金,但遺憾的是,在中國幾乎沒有——儘管,對雙方來說,技術的成色不成問題,交易的需求也不成問題。\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鄭小星認爲,如何建立互信和互相的瞭解是其中的關鍵:以色列是一個資本競爭激烈的市場,來自各個國家的資本都在那裏淘金,那是一個典型的技術輸出國,在輸出過程中他們需要找到最爲理想的夥伴。中國是一個巨大的資本來源地,也是一個全球商品在這裏競爭異常火熱的市場,中國的資本需要找到最好的“商品”。在這種心態之下,雙方帶着不一樣的優勢走向談判桌,如果沒有前期的溝通與協作,很難最終成交。\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唐亮認爲,中國大企業去海外投資和收購還有一個特點,它們對於相對早期的項目或者說技術含量比較高的項目,判斷能力是較低的。這與美國的大企業形成了較爲鮮明的對照。\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爲什麼會形成這樣的差別?唐亮告訴經濟觀察報:“很大程度上在於,中國的大企業自己做原創的研發不多,再者,中國的大企業本身缺乏專業的投資團隊,往往是最高層拍板,歷史上都是如此,但在歐美企業中,通常有投資部門,也有做頭部管理的團隊,這是相對專業的過程。”\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鄭小星認爲,對於以色列的科創企業來說,他們面臨諸多疑問:中國能不能去?中國哪個地方值得去?發一臺貨會不會有危險,還是最好只發一個樣品?過去,以色列的企業對於中國在知識產權保護方面一直心存擔憂,但隨着大的環境越來越好,這樣的擔憂在減弱。\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他們對中國資本做盡職調查,原因也是基於中國市場環境很複雜,有這麼多的參與者,這讓以色列的企業感到無所適從。比起錢,他們的確更需要一個夥伴。”鄭小星說。\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AmirGal-Or也認爲:中國的資本在和以色列的項目對接時,會出現許多理念上的分歧。例如,中國資本更多地在尋找擁有更大規模的公司,而以色列則在尋找可靠的合作伙伴,用以開發仍處商業化早期階段的產品或技術;以色列人對知識產權保護問題非常敏感,而中國人則更關注營銷和財務。\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對於那些在技術開發上具有硬需求的中國大企業來說,毫無疑問,以色列是一塊科創資源的寶地。\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鄭小星介紹,在過去十多年中,只有一家中國大企業真正把研發基地放到了以色列,這家企業正是華爲。現在,這個以色列的團隊已經達到數百人的規模,它給華爲貢獻了諸多優秀的科研研發。\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薛冰提到,華爲在以色列能夠做到更好地利用當地的工程師資源,儘管這些工程師不擁有股權。這些工程師通常也不會參加一個完整的項目,而是針對一個解決方案,這是一種碎片化的合作方式。而國外的科技巨頭,如微軟、英特爾等,早已與以色列形成了很強的業務互動。\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鄭小星認爲,對於大多數想要利用好以色列科創資源的中國企業以及希望融入中國市場的以色列企業來說,他們都缺乏一個本地化的過程。\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以色列一共有300多家跨國公司,他們大部分的做法是在當地設立自己的項目平臺,不一定是自己的人在設立,很多時候他們也會跟其他的項目平臺合作,在以色列尋找技術,但可惜的是,這裏面中國客戶的數量太少。”鄭小星說。\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鄭小星認爲,對於中國的資本和企業來說,更多時候要通過變通,讓投資這件事情變得更容易。讓更多的國外科創企業來到中國,與中國資本和企業實現對接,是她認爲的更加合適的方式。\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反轉的背後\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以色列駐上海總領事館華東地區經濟商務處負責人認爲,中國對以投資現在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這位負責人告訴經濟觀察報,近幾年,對以色列投資增速整體放緩的原因有幾個:之前投資的以色列企業,比如財務投資,更多的是利用這幾年“消化”和退出在當地的投資項目。而企業投資人也在這幾年更多的在做以色列技術在中國市場的運營和落地。更集中的在做市場端的推廣,比如復星收購的A-HAVA和AlmaLaser這幾年一直在組建自己的專業團隊,專注做本土化的運營。這兩家以色列公司在中國市場發展的非常好。\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再者,這些年中國企業和機構對創新的理解更深度更透徹,特別是在比較了很多以色列創新企業後,投資人更知道中國市場需要什麼,哪些是更貼近於中國市場的,在做投資的時候更懂得調整自己的方向做出更優的選擇。\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該負責人還提到,整個投資的目的地在轉移,前些年資本主要集中在以色列本土,近幾年由於境外投資審覈相對嚴格,ODI審批週期較長。投資的熱情有所降低,但是近幾年更多的以色列項目落地在中國,技術迴流到中國市場,應用在中國市場,這個是趨勢。“我們以色列企業在國內的子公司這幾年也受到在中國資本的青睞,助力其在中國的發展。”該負責人告訴經濟觀察報。\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上述負責人表示,民營資本投資有些更願意低調處理,不太願意提及投資的對象和金額。對有一些國有資本而言,也不排除他們的LP是一些民營企業,只是更願意以一種基金領投參投的形式操作。此外,也不排除政府對於ODI境外投資審覈更爲嚴格、週期更長這一因素。“我們之前有一些以色列企業也有很多投資TS簽好之後,因爲中方投資未在以方規定的限期內投進來而導致項目流標。另一方面這兩年,也受經濟大環境,投資週期等因素影響,市場總體屬於資本寒冬。對於民營企業也更專注於做好自己本來優勢的拳頭產品,對於新產品新技術的試錯成本在這幾年也更謹慎的去投放。如不是國外非常優質的項目,看的多但是投的少。”上述使領館負責人表示。\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INNONATION董事長AmirGal-Or向經濟觀察報表示:投資減少與中國跨境投資的管理規定有關,同時也和中國經濟形勢和科技領域商業活動的週期相關。此外,絕大多數用於風險投資和跨境交易的自由資金都掌握在國有企業手中,而非私營企業。\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這樣的景象與兩三年前的情況有一些不同,以色列駐上海總領事館華東地區經濟商務處負責人向經濟觀察報回憶:“2014年至2017年,中國企業投資以色列趕上一波投資熱潮,當時響應國家號召鼓勵企業和投資機構走出去,許多龍頭企業也在這個期間積極部署和調整國際市場戰略。同時另一部分傳統行業的企業尋求轉型和產業升級的需求非常旺盛,熱錢遊資也相對雄厚,而以色列也通過多年的創新技術的積累和迭代,恰巧嫁接中國企業的資本,做了個高度的匹配和融合。”\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太庫科技全球CEO唐亮認爲,資本出海一直都是個瓶頸,而對於經驗尚顯不足的中國企業,在與海外項目對接的過程中,會出現多方面的障礙,本地化的匱乏則使得對接的效率不夠理想。\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現在,跨境服務平臺開始更多地展開逆向的操作——將以色列的公司帶到中國來,尋找中國的資本與市場。對中國和以色列來說,儘管中國資本的出海遇到了瓶頸,但以色列數量龐大的科創企業依然需要中國資本和中國市場的支持,同時,中國的企業則對以色列的高新技術依然保有濃厚的興趣。\u003C\u002Fp\u003E"'.slice(6, -6), groupId: '67181484104965166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