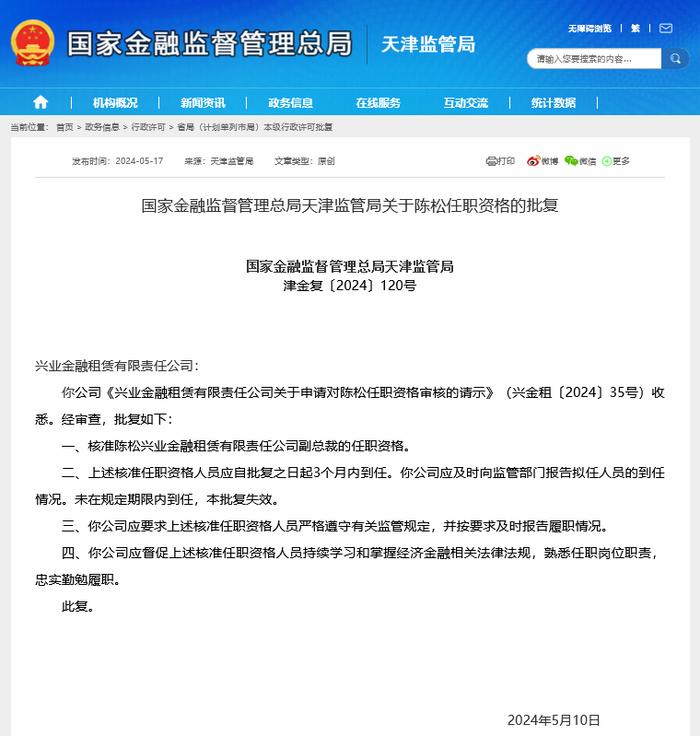【興業強身】資本寒冬下的投後管理(上)
核心觀點:
大多數投資機構認爲,被投項目發展的好與壞,在投資的那一刻便基本確定了,與投後的關係並不大。正是基於這種想法,絕大多數的投資機構在歷史上一直不重視投後管理。
然而,這些投資機構卻嚴重忽視了另外一個方面,項目發展的好與壞,和投資機構的投資收益高與低,是兩件雖然相關但有一定獨立性的事情。投資機構在一個項目上的投資收益高與低,十分關乎於投後。一個發展好的公司,投資機構的收益未必高;一個發展不好的公司,投資機構的收益未必差。這一切取決於投後退出。
舉例而言,大家都知道OFO現在狀態不佳,未來前途未卜;大多數投資機構都不得不將其對OFO的投資做壞賬處理,然而金沙江創投卻依然在該項目上獲得了鉅額回報,原因就在於當OFO還處於高光時刻,金沙江創投卻看到了未來的潛在風險,堅定的將其所持股份在最後一輪賣給了阿里巴巴。
在我所接觸的投資機構中,有些投後做的好的投資機構,投後人員一年能幫所在機構從問題項目中拿回十餘億、數億元(非通過IPO和併購退出的優質項目),這些收益對於任何一家基金都是不可小覷的財富。
在過去的兩三年時間裏,我在很多文章、很多場合的演講中,反覆的表達一個觀點:投後管理的好與壞,很大程度影響基金的收益,投資機構應該加強對投後管理的重視。
儘管市場的變化是緩慢的,然而,在資本寒冬到來的2018年,在很多機構無新錢可投的情況下,很多機構或主動或被動的重視起來投後管理了。這對投後管理當然是一件值得高興的好事。
潛力股在2018年底,對國內近100家投資機構的投後做了一次全面的問卷調查,也對十餘家投資機構的投後人員做了深入的訪談;結合潛力股在過去三年裏從事老股轉讓的經驗,及與投資機構打交道過程中所見、所聞、所感,我將我對投後管理的一些感悟總結和梳理一下,希望與諸君探討。
1. IPO的窘境:普遍破發、極度缺乏流動性
我曾在《年度觀察:30支2009-2011年人民幣股權投資基金退出數據統計分析》一文中統計對比過中國和美國的退出比例,在中國風險投資的退出結構中,所呈現的是一個倒金字塔的結構。我們以2009-2011年的30支人民幣基金的退出統計和美國的退出統計做對比,發現:中國100個退出項目中,有59%是通過IPO退出,有19%是併購,16%是轉讓;而美國是5.6%通過IPO退出,56%通過併購,38%通過轉讓。
表1. 中國2009-2011年基金退出結構統計及與美國的對比
可見,中國的投資機構更傾向於以IPO的方式退出,即使是在中國本土資本市場IPO如此困難、IPO幾率如此低的情況下,中國的投資機構依然爭先恐後的擠IPO的獨木橋。
在絕大多數中國投資人的思維體系中,唯IPO是上,成了一種宗教。
我一直認爲並不斷呼籲,我們應該改變這種唯IPO是上的信仰,而更應該考慮各種形式的退出機會,原因在於:一是社會自然規律,能IPO的畢竟是那些頂尖的公司;二是中國市場IPO的政策變化太快,不確定性太強;三是即使IPO,摺合下來的收益率也不一定是最高的;四是通過其他方式退出的收益也並不一定比IPO的收益低。
然而,儘管有項目IPO是每一家投資公司值得驕傲的事情,但能否在二級市場將股票順利的賣出、能否賣一個很好的價格,依然是一件不確定的事情。在2018年,儘管很多投資機構收穫了多個IPO項目,但是從實際收益的角度來看,心裏的苦與尷尬,可能卻是“誰上誰知道”,甚至對於很多機構來說,撈了名卻沒撈到利,更多是收穫了一次媒體宣傳和PR。原因在於兩個方面:
根據微信公衆號青蘭研究針對十家科技股獨角獸公司的研究,截至2018年12月24日,與其IPO發行價相比較,這10家獨角獸,平均跌幅達46.2%。跌幅最大的易鑫集團,在12個月裏跌掉了76.2%。與IPO發行價相比,十大獨角獸平均跌幅達到了46.2%;70%以上的獨角獸最後一輪投資人是虧損的,90%以上的最後一輪投資人投資收益未能跑贏年化8%的理財收益。
在美港股如此普遍破發的現狀下,別說最後一輪投資人,恐怕連C/D輪投資人的收益都將受到極大影響。
我在2018年底統計了全部美股中概股和港股新上市的互聯網公司日成交額(詳見《美港股IPO衆生相:平均跌幅46.2%,日成交額只有10萬美金》),從交易額分析,大量公司的成交額在幾十萬美金或兩三百萬港幣之間,每日的交易額十分慘淡。更有甚者,像信而富、英語流利說、1藥網、尚德機構等公司每日的股票交易額僅爲10萬美金左右。
如此低的成交量,導致的最直接後果就是,對於投資人股東來說,要賣出其所持有的股份,所需要的時間十分長,即使上市了之後,依然面臨着退出十分困難的窘境。
我們按照日成交量計算如果要出售1%的股票需要交易的天數。請注意,該交易天數的前提條件是在別的股東都不進行股票出售,整個市場只有這一個賣家在賣股票的情況下實現的。
大量公司1%的股票需要賣超過20天以上的時間,如海底撈、1藥網、信而富、尚德機構、流利說、華米、51信用卡、獵聘、易鑫集團、觸寶等。
衆所周知,很多互聯網公司發展到IPO階段,從股權比例來看,機構投資人一般是大股東,團隊是小股東了。對美元基金來說尤其如此,因爲美元基金的風格是加註型投資,股份比例越來越多。
在如此低的成交量下,即使公司IPO了,投資機構的股票也很難順利賣出。我在與多家投資機構投後人員的交流中,則印證了這一觀點。投後人員表示,對於美港股而言,即使上市了,賣股票也是一個長期和煎熬的事情,每天掛單一點點,不能賣太多,因爲賣太多,就將股價砸下去了,公司也會過來找與投資機構問情況,這種賣股票的行爲,視個股而言,可能持續長達1-2年,有一些公司如果持股比例高的話,可能很多年都無法賣掉。
2. 當前國內投後的現狀
2018年底,潛力股平臺對國內近百家投資機構的投後情況進行了問卷調查,形成了一篇報告《投後怎麼做?看看這96家投資機構的投後情況調研吧 ——中國投資機構投後管理調查研究報告 》。結合報告的內容和潛力股在過去幾年與投資機構投後人員打交道的實踐,對於中國投資機構的投後,我們認爲:
3. 投資機構在投後工作存在的普遍問題
筆者綜合對近百家投資機構投後人員的調查及十多家投資機構的訪談發現,當前投資機構對於投後普遍存在以下的問題:
(1)對投後普遍的不重視
正如本文開篇所說,大多數投資機構對投後不重視,在募投管退四個環節中,機構對募資和投資的重視程度遠遠大於對投後管理和退出的重視程度。
(2)投後的人員投資嚴重不足
我們在對近百家投資機構投後人員的調查中發現,75%的投資機構中投後人員在1-5人之間;18家人數在31-50人的投資機構中,僅有不到1/3的機構人數超過5人;而基金規模在10-30億人民幣的投資機構,投後人數在超過5人的佔比僅爲8%。(《投後怎麼做?看看這96家投資機構的投後情況調研吧 ——中國投資機構投後管理調查研究報告 》)
(3)投後缺乏標準化的流程和考覈標準
絕大多數投資機構的投後工作都處於初步摸索狀態,投後工作相對隨意,缺乏標準化的流程。舉例而言,多久開一次董事會;多久統計一次被投企業數據;多久召開一次被投企業交流沙龍;如何系統化的爲被投企業提供人事、融資方面的幫助;多久對被投項目進行一次覆盤;如何確定被投項目的退出策略……
在筆者調查的投資機構中,很多投後人員對於如何量化自己的工作成果並無明確標準,公司在年終如何評判投後的工作好壞亦缺乏標準。比如說,負責PR的同學,到底怎樣才能算是把投後的PR做好了呢?負責PR的同學不知道,公司也不知道,更多是靠感覺。
缺乏標準流程、缺乏考覈標準,最直接的後果便是投後人員的不知所向並導致鬆散懈怠,使得投資機構看似付出了人力財力,效果卻不盡如意,從而使投資機構產生“投後無用論”的感覺。
(4)投後不以退出爲目的
不以退出爲目的是絕大多數公司投後存在的最重要、最普遍問題。
我認爲,投資的終極目的和唯一目的便是退出。所有不以退出爲目的的投資都是對LP耍流氓。
然而,大量投資機構的投後管理注重監控,偏向服務,卻不以機構自身的退出爲目的。這體現在:
投後不以退出爲目的的一個最直接結果是,使得投後部門變成了成本部門,而不是創收部門。
實際上,在我看來,投後部門應該成爲一個投資公司內創收的主要部門,項目該什麼時候退出、通過什麼方式退出、以什麼價格退出,這些退出的收益就是投後最直接的創收;更進一步來說,投資公司的PR/HR/IR服務是否可以變成一個不僅對自己所投公司,甚至對其他第三方公司輸出的服務,是否可以由一個免費服務變成價格合理的收費服務?這也是值得探討的問題。
筆者所瞭解,有些投資機構的投後人員,能從被公司判了“死刑”或除了問題的項目中,每年拿回數億甚至上十億的資金回來。這對於投資機構來說,自然是一筆十分巨大的收益。
(5)投後的功勞難以衡量
投後從業者一個普遍的困擾是,自己的工作功勞很難衡量。
一方面,投後所涉及的工作十分繁雜,類似於統計聯繫類工作、PR/HR類工作,更多是行政性輔助工作,其有多大價值難以用金錢來直接評估;
另一方面,對於一個項目的退出收益,投資人員有多大功勞,投後人員有多大功勞,其實很難去衡量。
筆者認爲,對於行政職能性工作,應該以定性爲主的方式來衡量其價值,如工作的專業性、被投企業的評價等;輔助以定量的方式,比如一年幫多少被投企業招了多少人等。
對於退出的工作,筆者認爲除了正常的IPO之外,對於股權轉讓、回購等工作成績實際上比較好衡量。因爲IPO項目,投資公司更多處於被動配合的角色;而對於股權轉讓、回購,投資機構則是主動去管理的狀態,如果該部分工作由投後來完成,其功勞自然大部分屬於投後人員。
(6)投後人員激勵不足,動力不強
在我們投後的調查中,有91.7%的人認爲投後人員應該參與到收益分成中來。現實中,大多數投資機構未能給予投後人員收益分成的權利,投後人員以固定薪酬+績效獎金爲主,激勵不足。
4. 投資機構爲什麼不重視投後
個人認爲,投資機構不重視投後工作,主要在於如下原因:
(1)第一大原因:絕大多數投資機構的主要商業模式是賺取管理費
對於大多數中國的投資機構而言,其核心的商業模式是賺取管理費,而不是賺取後續的超額收益分成。
在一定程度上,這句話可能會得罪行業裏很多從事投資的朋友。然而,筆者並非不看好投資這一行業,也並非是站在大家的對立面。我只是認爲,無法形成正循環、無法爲客戶賺錢的行業和公司,從長遠來看一定是不可持續的。只有那些真正賺錢的行業和公司,纔可長期的蓬勃發展。
我曾在2017年統計了大量投資機構的財務數據,由於很多投資機構上新三板或者A股,要獲取其公開數據並不難。通過這些統計數據我們發現,投資機構的收入主要由三個部分組成:一是管理費、二是超額收益分成(所謂carried interest)、三是以公允價值變動計入當期損益的金融資產。
第三個部分是不太好理解的。什麼是以公允價值變動計入當期損益的金融資產?通俗點來說,就是估值的變化導致浮盈的變化。舉個例子來說,如果我天使輪投資某公司100萬,估值1000萬;如果這個公司融A輪,估值10000萬,融資1000萬,那麼我所持股份的賬面價值變成了900萬,900萬減去100萬*20%=160萬,就是我作爲GP當期可得到的賬面收益。
大家都知道,所謂賬面浮盈是否能變成現金,是具有極大不確定性的。然而,不幸的是,絕大多數投資機構的財務報表利潤之所以如此豐厚,是因爲有了這個部分。
這也就是爲什麼後來全國股轉系統對投資機構的掛牌時提出了一個明確的規定,即管理費+超額收益分成不得低於總收入的80%。在此規定提出之前,絕大多數投資機構的管理費+超額收益分成不足總收入的20%。而在這其中,管理費又佔據了絕大部分。
正是因爲絕大多數公司都很難賺取超額收益,於是管理費便變成了主要收入來源。而要提高管理費收入的方式無非是兩種:一是提高資產管理規模;二是提高收費比例。由於管理費比例是行業約定俗成的規則,很難提高;因此,提高資產管理規模,變成了唯一的方式。
而要提高資產管理規模,一方面是不斷提高機構的品牌知名度;另一方面是擴大募資團隊和投資團隊;第三方面則是投資那些知名度高的項目(未必是未來回報高)。
這也是爲什麼,很多投資機構對募資十分重視,在募資方面的投入十分捨得。
(2)第二大原因:投資機構認爲項目好壞與投資有關,與投後無關
如本文開篇所說,絕大多數投資機構認爲,所投項目的發展好壞,在投資時便基本確定,與投後無關。
投資即投人。在某種程度上,這種觀點確實是正確的,尤其是當公司相對來說比較成熟和穩定時,投後所產生的價值確實難以體現。
然而,對於早期投資而言,投後所做的很多工作對於被投企業就顯得十分重要了。比如戰略建議、競爭情報、人才物色、融資支持等。
(3)第三大原因:認爲投後是成本部門,對提高收益沒什麼幫助
很多投資機構將投後狹隘的理解爲投後管理,而不去考慮投後退出方面,認爲投後部門是花錢的部門,卻創造不了收益。
然而,筆者可以負責任的說,投資機構投後做的好,對於提高投資收益率具有十分明顯的幫助。
且不說,我們前面提到的有一些投資機構投後每年幫助公司從問題項目中拿回數億的投資款。
潛力股平臺在過去幾年時間內,統計了大量投資機構的退出比例,我們發現,在股權轉讓、回購方面比例比較高的投資機構,其投後普遍做的比較重、比較好。
原因在於,股權轉讓、回購退出是由投資機構自己主導的,而什麼時候轉讓、回購,是需要對市場、對競爭、對公司自身有十分了解的基礎上才能做出的決策,且還需要通過各種溝通技巧、法律手段、人際關係、外部資源才能實現的。
而這些工作又很難交由投資該項目的投資經理來實現。原因在於:一是投資經理喜歡“護犢子”,“報喜不報憂”,畢竟是自己投資的項目,如果說沒投好,自己臉上無光;且投資經理更容易偏樂觀的看待項目的未來;二是投資經理大部分時間在投項目,在投後管理方面花的時間普遍偏少;三是投資經理在投後退出的經驗、人脈、技巧方面都欠缺;四是退出是一個極度耗時耗力的事情。
(4)第四大原因:投資行業發展階段的必然過程
所謂募投管退,從時間上,先有了募資,纔有投資,當投資到一定時間、積累到一定項目數量,纔會產生更強的投後管理和退出需求。
中國資本市場本質上還是一個年輕的市場,大多數公司成立的時間還不夠長,投資的項目還不夠多。因此在過去的很多年,大多數機構還是以募資+投資爲主。
5. 投後工作的價值
我認爲,投後工作無論對於投資機構還是對於被投企業,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價值。
(1) 投後有利於投資機構實時瞭解被投企業狀況
坦白說,投資機構對所投項目最瞭解的時候就是在投資時。爲了投資,投資機構花了數月的時間對項目進行盡職調查,所掌握的信息最爲全面,也最爲深刻。
一旦投資完成之後,一方面,對被投企業花的時間少了;另一方面,公司也在持續的發展和變化過程中,投資機構對被投企業瞭解越來越少。
投後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幫助投資機構實時的掌握被投企業現狀,從而爲後續工作提供信息基礎。
(2)投後有利於幫助被投企業發展
投資機構所提供的戰略諮詢、業務整合、市場情況、人才物色、資本對接、媒體公關等工作,對於被投企業的發展,有時候能起到十分關鍵和重要的作用。
(3)投後有利於被投企業之間形成業務協同
投資機構所投企業之間或多或少能產生一些協同和相互合作,由於有共同的投資人股東,被投企業之間合作的概率更大,信任的基礎也更牢固。
(4)投後對於提高投資的收益率具有極大幫助
在我們的調查中,我們發現,投後做的好的投資機構,其退出率遠好於其他投資機構。
首先,對於那些併購和IPO項目,投後做的好的機構,會幫助企業把握正確的時間窗口,提供資本市場的建議,幫助尋找靠譜的券商和中介機構,幫助尋找董祕/CFO等關鍵人員,對於提高IPO成功率、降低風險、減少成本會有出其不意的效果;
其次,對於股權轉讓和回購,投後做的好人員,會判斷什麼時候、以什麼方式退出,捕捉到別人未發現的退出機會,而很多時候,往往這種退出機會轉瞬即逝,不可再來。
我們瞭解到,有一些投後做的好的基金,每年能通過股權轉讓、回購、變賣資產團隊、組合資產等各種方式,從發展狀況不太好的項目上拿回數億元的資金,對於投資機構來說,某種程度上這些錢屬於原本是“壞賬”的,所以投入產出比十分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