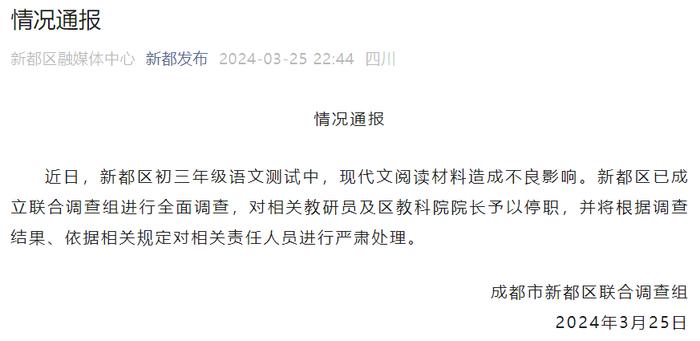悼念恩师赵希奎
摘要:\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那些天赵老师主动找了我两次,询问发生群殴械斗的情况,并积极去医院与“失聪”学生的家长沟通做工作,本着息事宁人、教育为主的出发点与校方力争驳辩,终使我有了“留校察看”的学习机会。\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毕业离校后,我虽偶有去母校探望,但因繁杂巨细的掺入,只见过两次赵老师。
"\u003Cdiv\u003E\u003Cp\u003E王晟\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2016年7月27日,我与曾在富家滩汾局二中的同窗女同学范爱红、王雪花相邀,一同驱车前往祁县西六支村,探望已退休归隐故里的高中班主任赵希奎老师。\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那是个悲伤的日子。当我们到了祁县西六支村时,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鳞次栉比整齐又极相似的街道和家户庭院,当时我等就举步难定傻眼了。打电话给师母(得知恩师已失语),师母便说派人出来接我等。当我仨人跟随师母派来的向导来到赵老师家的院门前时,远远地看见在赵老师家斑驳失修的两扇老式大门上各贴一张菱形白纸。心一沉,顿有不祥预感倏突间弥漫了周身,同行的俩女同学用疑惑而惊悚的眼神看着我。赵老师在同天早上8点多与世长辞!享年73岁。\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我们仨同学尾随领路人穿过有些阴暗的门洞,进入狭窄的庭院,两边各修筑两间年久失修的灰色瓦房,相向而对,使得庭院空间更显狭长。檐瓦上的瓦缝中有几棵瓦松低垂地长着,看得出院主人已有很久没有清理过了。师母及俩女儿泣迎了我们。师母哭泣着拉着王雪花的手,哽咽诉说着老师谢世前的凄清,范爱红在侧轻抹眼泪安慰抚劝师母节哀顺变。我们心情沉沉浸痛,焚香鞠躬,祭奠了尚未入殓枯瘦嶙峋的恩师。神思飞绪,似真似幻地仿佛恩师就在眼前正襟危坐着……\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赵老师是我高中时的班主任老师,教语文。初识赵老师是在1982年初秋时节,高中录取入学的第一天找班主任老师报到时。四十来岁的他,身材略高且壮实,平实的国字脸庞上泛着那种健壮的红润,鼻挺嘴阔,两条短剑眉中间是深深的“川”字纹理,眼神甚是犀利,被他的眼神扫过,有种被刺痛的感觉,看得出来脾气不大好。\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分在同一宿舍的同学都是第一次离家住校生活,脱离了家长的视线,个个都似刚出窝的小鸟,都变得活泛起来。收拾打理好各自的床铺,几个人聚在一起相互认识后便神谝胡侃起来。\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赵老师进来了。我们忙起身立迎,老师和蔼伸手,示意我们随意些,他也随即坐在床上抻了抻床单,摸了摸被褥的薄厚,又掀起褥子下的床垫看了看说:“: 条件比上届时好多了!你们步入高中已属不易,要好好珍惜此学习机会,刻苦努力充实自己,万不能以基础差底子薄为借口,给自己的不努力找出客观而正当的理由来搪塞。倘若如此这般,那就别说如何对不起含辛茹苦的父母双亲了,真真贻误时光对不起的人还是自己!”随后又逐个拉家常式地询问了些个人的情况,最后甚是诚挚地说:“既然凑在一起了,也是缘分所致,咱们都是自己人,有什么困难和要求可以直接向我反映,千万不要客气!”说完便又起身去了别的宿舍。记得那天直到晚上10点多了,他仍在学生宿舍里与入学新生攀谈着,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是个“婆婆式”老师。这倒让我觉得上午对他那犀利刺人的眼神是自己的判断失误,同时也给了我些许不畏“师威”的感觉。\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生性好动的我总喜欢不分场合地随意搞怪放肆一下,抑或在课堂上不拘绳墨地出个“小风头”,哄堂过后,则貌似安然的一本正经。不知谁背后向赵老师打了小报告。有一次自习课我正在与一同学唾沫横飞地指点江山时,赵老师悄然而至。好一通疾风骤雨般五指山压顶的招呼过后,又把我俩一左一右分置惩罚站在讲台两侧,紧接着又是一通挖苦教育。那一次我俩算是颜面尽失威风扫地了!我的违规招致的切肤之痛令我重新审视了赵老师的“威仪”所在。事毕赵老师又把我俩叫到他宿舍,边做饭边和我俩唠嗑,知晓了他苦难艰辛的过往和秉烛夜读的学生时代……\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寒冷的冬夜里,皴裂的手就着煤油豆灯翻看着课本,抄摘课堂笔录;炎热如炙的夏天,除乏解困的高招竟然是舔一舔辛辣的干辣椒面。孜孜不倦的努力终使其跳过了“龙门”,也算成了故里桑梓的佼佼者,告别了祖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方式。师范学校毕业后,分配到富家滩矿子弟学校任教,成了一个吃“皇粮”的公家人。自然那天的晚饭我和同伴是在赵老师的宿舍“风卷残云”了一番。\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他总是不失时机地肯定着每个学生的成绩和进步,循循善诱地激励着我们在知识海洋中努力前行。记得有一次作文课,我刚刚学了朱自清的《荷塘月色》,深觉作者描写荷姿百态的那段,有妙笔生花的感触,便情不自禁拈来使用融入自己文中。事后忐忑待评,当时也不知算不算剽窃。结果赵老师给了我很肯定的评价说:“学了能用上,说明你吃进去消化了!正所谓‘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就是这个道理。”也许这是一个在他看来微不足道的话语,却给了我强大的鼓励支撑,使我后来学习阅读的能力有所提高,毋庸置疑,那次的当堂鼓励是我学生时代的里程碑。\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少不更事、好胜斗勇是那时候帮派学生的共性。由于汾局二中的学生来源主要是南关、富家滩、张家庄三个矿的子弟,加之1983年严打前期的社会青年鱼龙混杂,本来就有些排他敌对的各矿学生,又掺和了社会闲杂人等的恃强凌弱,常有掺杂着社会青年的学生群械众殴的事件发生。我是弱者反击的一方,但终因群殴械斗的后果,致使一个对方学生失聪,学校核查后,我阴差阳错竟成了“祸首”。据说学校起初决定给予“开除出校”的处分,以儆效尤。那些天,我无时无刻不在打探着校方对我们的处理决定,急切盼望着此事的尘埃落定。无助的我也真的豁出去了,爱咋咋地吧!\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那些天赵老师主动找了我两次,询问发生群殴械斗的情况,并积极去医院与“失聪”学生的家长沟通做工作,本着息事宁人、教育为主的出发点与校方力争驳辩,终使我有了“留校察看”的学习机会。不能不说这是我学生时代的转折点,赵老师的力排众议才给我留下了继续课堂学习的机会!\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赵老师在杏坛执教的生涯中,治学严谨,执着而诙谐。一次我去他的宿舍执卷求教,恰逢他和朱本祥老师怡情小酌,一盘炒胡萝卜丝、一小碟咸菜已消灭殆尽。酒酣耳热之际,朱老师呵呵打着诨语:“你们赵老师呀,天天都是浑浑噩噩地活着,哪里去给你们解惑答疑。”赵老师则一本正经地接话:“浑浑:深厚的样子;噩噩:严肃的样子,本意是浑厚而严正。你不要这么隐晦地表扬我了!”当时我真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回来细品回味,还真为此翻了回《现代汉语词典》,深为赵老师博闻强识而折服。\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毕业离校后,我虽偶有去母校探望,但因繁杂巨细的掺入,只见过两次赵老师。他总是默默聆听着我离校后的点点滴滴,从不轻易打断我的话,像个智慧而慈祥的长辈。分别时总要叮嘱一番“好好努力,谨慎做人”之类的话。再后来诸多因素的不便,终和赵老师失联了!\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后来微信网络有了班群,才得以知晓有关赵老师的消息,他已于1999年退休回了祁县老家。探知消息后的第二天,我便独自去探望了我的恩师。他已经沉疴卧床数年,师生相见,两手相握,唏嘘不已。目睹着口不能言、足不挨地瘫卧在床的恩师在忙不迭地打着手势与我极力 “交谈”时,那“呀呀”声、比划语竟成了师生多年邂逅的悲摧见证时,我的心惨然滴血、情悲凄楚,甚是难安……年迈的师母则站立一旁权作“翻译”,并不时给我续添着茶水。\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中午时分,我委婉地谢绝了再三挽留我在家中吃饭的恩师夫妇,一再坚持谎称有人约在先,握别了恩师母。时隔一月相约旧时同学再探恩师,本想好好慰藉恩师抱疾孤卧的落寞心绪,使其尽享一番“桃李满天下”的人生欢悦时,不曾想却已与我们无言诀别,成了永久停留在阴阳两界的遥远思念了!\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恩师,无语言状的情愁思念;恩师,难以抹去的心底记忆!静思难耐,以七律记之:\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悼恩师\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夏暑悲天紫燕鸣, 浮云低泣素遮楹。\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寻师执卷无如愿, 叩拜拈香寄悼情。\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恬淡生平勤俭朴, 无奇终日慎言行。\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经年一别孤村殁, 再扰先生梦里萦。\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附:刘海红讲矿务局二中之于她\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比我年长8岁的大姐考上了初次成立的富家滩高中。据说当时师资力量雄厚,整合了南四矿所有高中的精英老师,组建了这所富家滩的高等学府,奠定了其在矿务局的文化领地。\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 20世纪80年代的高中是两年制。记得一周当中,母亲总会抽出时间做些可口的食物给大姐送去,两角钱的车票,十来分钟的车程。这两年,家人像走亲戚似的往返于富家滩和南关之间。\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 每到周末,我都会站到铁路旁,等着坐绿皮火车回来的大姐,帮她拿吃空了的装咸菜的瓶瓶罐罐,干粮布包。也许是对陌生地方新奇感的驱动,或者是对坐火车的向往,我几次央求母亲带我一同去,母亲都以怕添乱为由拒绝了,这成了我幼小心灵的一个遗憾。这个遗憾,也让富家滩成了我可望而不可即的地方。\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2高三那年我因病未参加高考,大姐找到了已是校长的当年的高中班主任,希望我能在这儿复读。富家滩接纳了我,也圆了我儿时所期盼的一个心愿。\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 校舍还是大姐们曾经用过的旧校舍,梁上依稀还回荡朗朗的读书声,坚守着故土的老师们已经两鬓花白,践行着“春蚕到死丝方尽” 的使命。\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 课余之外,我总会抽出一些时间来亲近一下富家滩的山山水水,亲自体验一下印象版和现实版有何不同。\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 90年代初期,由于富家滩矿井已经不再生产,职工大部分都分流出去,富家滩的人口明显稀落。走在马路上,两边的排房门口都是老人歇息的身影,安静、恬淡。排房的尽头还有几间低矮废弃的房屋,据说是当年日本人修建的,带着历史沧桑的印痕。排房的尽头就是富家滩曾经的繁华地带,并排有几间店铺,几个摊位,一两间饭店,一个邮局,一个已经关闭的文化宫,构成了富家滩相对集中的消费阵容,让人有一种“门庭冷落车马稀”的感慨。\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 沿着这条路往前走,过了马路对面,就是萦绕在我脑海深处的“阶级教育馆”了。十来年的风雨锈蚀,门上的字迹已经斑驳,墙体已出现裂纹,如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早已没有了昨日的辉煌。馆的左边便是汾河水,哗啦啦地诉说着昨日的蹉跎过往。\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 从北到南,仅用了十来分钟便丈量完富家滩矿的领地,不免生出许多感触:没有灯红酒绿,没有高楼林立,没有车水马龙,就这样一个巴掌大的荒凉瘦弱的地方,却承载了几多灾难,几多沧桑,几多历史的厚重。\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 由于学业的繁忙,只是走马观花地对富家滩了解一些概貌,但我知道,在某一个排房的某一个老人的记忆里,一定深藏着富家滩的灵魂,富家滩的秘密。\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 也许,这就是富家滩的特点吧:不拼颜值,只讲内涵。\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 拜富家滩补习所赐,我考上了矿务局护理学校,分配了工作。\u003C\u002Fp\u003E\u003C\u002Fdiv\u003E"'.slice(6, -6), groupId: '67184653767509283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