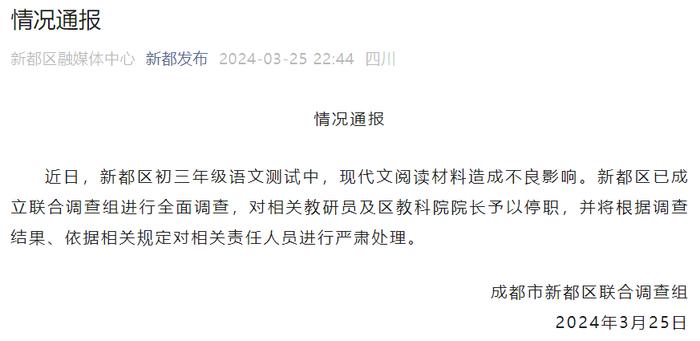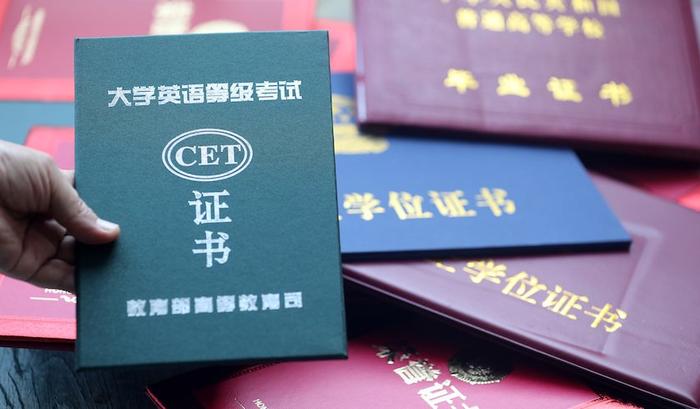悼念恩師趙希奎
摘要:\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那些天趙老師主動找了我兩次,詢問發生羣毆械鬥的情況,並積極去醫院與“失聰”學生的家長溝通做工作,本着息事寧人、教育爲主的出發點與校方力爭駁辯,終使我有了“留校察看”的學習機會。\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畢業離校後,我雖偶有去母校探望,但因繁雜鉅細的摻入,只見過兩次趙老師。
"\u003Cdiv\u003E\u003Cp\u003E王晟\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2016年7月27日,我與曾在富家灘汾局二中的同窗女同學範愛紅、王雪花相邀,一同驅車前往祁縣西六支村,探望已退休歸隱故里的高中班主任趙希奎老師。\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那是個悲傷的日子。當我們到了祁縣西六支村時,首先映入眼簾的是鱗次櫛比整齊又極相似的街道和家戶庭院,當時我等就舉步難定傻眼了。打電話給師母(得知恩師已失語),師母便說派人出來接我等。當我仨人跟隨師母派來的嚮導來到趙老師家的院門前時,遠遠地看見在趙老師家斑駁失修的兩扇老式大門上各貼一張菱形白紙。心一沉,頓有不祥預感倏突間瀰漫了周身,同行的倆女同學用疑惑而驚悚的眼神看着我。趙老師在同天早上8點多與世長辭!享年73歲。\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我們仨同學尾隨領路人穿過有些陰暗的門洞,進入狹窄的庭院,兩邊各修築兩間年久失修的灰色瓦房,相向而對,使得庭院空間更顯狹長。檐瓦上的瓦縫中有幾棵瓦松低垂地長着,看得出院主人已有很久沒有清理過了。師母及倆女兒泣迎了我們。師母哭泣着拉着王雪花的手,哽咽訴說着老師謝世前的悽清,範愛紅在側輕抹眼淚安慰撫勸師母節哀順變。我們心情沉沉浸痛,焚香鞠躬,祭奠了尚未入殮枯瘦嶙峋的恩師。神思飛緒,似真似幻地彷彿恩師就在眼前正襟危坐着……\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趙老師是我高中時的班主任老師,教語文。初識趙老師是在1982年初秋時節,高中錄取入學的第一天找班主任老師報到時。四十來歲的他,身材略高且壯實,平實的國字臉龐上泛着那種健壯的紅潤,鼻挺嘴闊,兩條短劍眉中間是深深的“川”字紋理,眼神甚是犀利,被他的眼神掃過,有種被刺痛的感覺,看得出來脾氣不大好。\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分在同一宿舍的同學都是第一次離家住校生活,脫離了家長的視線,個個都似剛出窩的小鳥,都變得活泛起來。收拾打理好各自的牀鋪,幾個人聚在一起相互認識後便神諞胡侃起來。\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趙老師進來了。我們忙起身立迎,老師和藹伸手,示意我們隨意些,他也隨即坐在牀上抻了抻牀單,摸了摸被褥的薄厚,又掀起褥子下的牀墊看了看說:“: 條件比上屆時好多了!你們步入高中已屬不易,要好好珍惜此學習機會,刻苦努力充實自己,萬不能以基礎差底子薄爲藉口,給自己的不努力找出客觀而正當的理由來搪塞。倘若如此這般,那就別說如何對不起含辛茹苦的父母雙親了,真真貽誤時光對不起的人還是自己!”隨後又逐個拉家常式地詢問了些個人的情況,最後甚是誠摯地說:“既然湊在一起了,也是緣分所致,咱們都是自己人,有什麼困難和要求可以直接向我反映,千萬不要客氣!”說完便又起身去了別的宿舍。記得那天直到晚上10點多了,他仍在學生宿舍裏與入學新生攀談着,給我留下的第一印象是個“婆婆式”老師。這倒讓我覺得上午對他那犀利刺人的眼神是自己的判斷失誤,同時也給了我些許不畏“師威”的感覺。\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生性好動的我總喜歡不分場合地隨意搞怪放肆一下,抑或在課堂上不拘繩墨地出個“小風頭”,鬨堂過後,則貌似安然的一本正經。不知誰背後向趙老師打了小報告。有一次自習課我正在與一同學唾沫橫飛地指點江山時,趙老師悄然而至。好一通疾風驟雨般五指山壓頂的招呼過後,又把我倆一左一右分置懲罰站在講臺兩側,緊接着又是一通挖苦教育。那一次我倆算是顏面盡失威風掃地了!我的違規招致的切膚之痛令我重新審視了趙老師的“威儀”所在。事畢趙老師又把我倆叫到他宿舍,邊做飯邊和我倆嘮嗑,知曉了他苦難艱辛的過往和秉燭夜讀的學生時代……\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寒冷的冬夜裏,皴裂的手就着煤油豆燈翻看着課本,抄摘課堂筆錄;炎熱如炙的夏天,除乏解困的高招竟然是舔一舔辛辣的幹辣椒麪。孜孜不倦的努力終使其跳過了“龍門”,也算成了故里桑梓的佼佼者,告別了祖輩面朝黃土背朝天的生活方式。師範學校畢業後,分配到富家灘礦子弟學校任教,成了一個喫“皇糧”的公家人。自然那天的晚飯我和同伴是在趙老師的宿舍“風捲殘雲”了一番。\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他總是不失時機地肯定着每個學生的成績和進步,循循善誘地激勵着我們在知識海洋中努力前行。記得有一次作文課,我剛剛學了朱自清的《荷塘月色》,深覺作者描寫荷姿百態的那段,有妙筆生花的感觸,便情不自禁拈來使用融入自己文中。事後忐忑待評,當時也不知算不算剽竊。結果趙老師給了我很肯定的評價說:“學了能用上,說明你喫進去消化了!正所謂‘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就是這個道理。”也許這是一個在他看來微不足道的話語,卻給了我強大的鼓勵支撐,使我後來學習閱讀的能力有所提高,毋庸置疑,那次的當堂鼓勵是我學生時代的里程碑。\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少不更事、好勝鬥勇是那時候幫派學生的共性。由於汾局二中的學生來源主要是南關、富家灘、張家莊三個礦的子弟,加之1983年嚴打前期的社會青年魚龍混雜,本來就有些排他敵對的各礦學生,又摻和了社會閒雜人等的恃強凌弱,常有摻雜着社會青年的學生羣械衆毆的事件發生。我是弱者反擊的一方,但終因羣毆械鬥的後果,致使一個對方學生失聰,學校覈查後,我陰差陽錯竟成了“禍首”。據說學校起初決定給予“開除出校”的處分,以儆效尤。那些天,我無時無刻不在打探着校方對我們的處理決定,急切盼望着此事的塵埃落定。無助的我也真的豁出去了,愛咋咋地吧!\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那些天趙老師主動找了我兩次,詢問發生羣毆械鬥的情況,並積極去醫院與“失聰”學生的家長溝通做工作,本着息事寧人、教育爲主的出發點與校方力爭駁辯,終使我有了“留校察看”的學習機會。不能不說這是我學生時代的轉折點,趙老師的力排衆議纔給我留下了繼續課堂學習的機會!\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趙老師在杏壇執教的生涯中,治學嚴謹,執着而詼諧。一次我去他的宿舍執卷求教,恰逢他和朱本祥老師怡情小酌,一盤炒胡蘿蔔絲、一小碟鹹菜已消滅殆盡。酒酣耳熱之際,朱老師呵呵打着諢語:“你們趙老師呀,天天都是渾渾噩噩地活着,哪裏去給你們解惑答疑。”趙老師則一本正經地接話:“渾渾:深厚的樣子;噩噩:嚴肅的樣子,本意是渾厚而嚴正。你不要這麼隱晦地表揚我了!”當時我真有點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了!回來細品回味,還真爲此翻了回《現代漢語詞典》,深爲趙老師博聞強識而折服。\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畢業離校後,我雖偶有去母校探望,但因繁雜鉅細的摻入,只見過兩次趙老師。他總是默默聆聽着我離校後的點點滴滴,從不輕易打斷我的話,像個智慧而慈祥的長輩。分別時總要叮囑一番“好好努力,謹慎做人”之類的話。再後來諸多因素的不便,終和趙老師失聯了!\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後來微信網絡有了班羣,才得以知曉有關趙老師的消息,他已於1999年退休回了祁縣老家。探知消息後的第二天,我便獨自去探望了我的恩師。他已經沉痾臥牀數年,師生相見,兩手相握,唏噓不已。目睹着口不能言、足不挨地癱臥在牀的恩師在忙不迭地打着手勢與我極力 “交談”時,那“呀呀”聲、比劃語竟成了師生多年邂逅的悲摧見證時,我的心慘然滴血、情悲悽楚,甚是難安……年邁的師母則站立一旁權作“翻譯”,並不時給我續添着茶水。\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中午時分,我委婉地謝絕了再三挽留我在家中喫飯的恩師夫婦,一再堅持謊稱有人約在先,握別了恩師母。時隔一月相約舊時同學再探恩師,本想好好慰藉恩師抱疾孤臥的落寞心緒,使其盡享一番“桃李滿天下”的人生歡悅時,不曾想卻已與我們無言訣別,成了永久停留在陰陽兩界的遙遠思念了!\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恩師,無語言狀的情愁思念;恩師,難以抹去的心底記憶!靜思難耐,以七律記之:\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悼恩師\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夏暑悲天紫燕鳴, 浮雲低泣素遮楹。\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尋師執卷無如願, 叩拜拈香寄悼情。\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恬淡生平勤儉樸, 無奇終日慎言行。\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經年一別孤村歿, 再擾先生夢裏縈。\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附:劉海紅講礦務局二中之於她\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小學二年級的時候,比我年長8歲的大姐考上了初次成立的富家灘高中。據說當時師資力量雄厚,整合了南四礦所有高中的精英老師,組建了這所富家灘的高等學府,奠定了其在礦務局的文化領地。\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 20世紀80年代的高中是兩年制。記得一週當中,母親總會抽出時間做些可口的食物給大姐送去,兩角錢的車票,十來分鐘的車程。這兩年,家人像走親戚似的往返於富家灘和南關之間。\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 每到週末,我都會站到鐵路旁,等着坐綠皮火車回來的大姐,幫她拿喫空了的裝鹹菜的瓶瓶罐罐,乾糧布包。也許是對陌生地方新奇感的驅動,或者是對坐火車的嚮往,我幾次央求母親帶我一同去,母親都以怕添亂爲由拒絕了,這成了我幼小心靈的一個遺憾。這個遺憾,也讓富家灘成了我可望而不可即的地方。\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2高三那年我因病未參加高考,大姐找到了已是校長的當年的高中班主任,希望我能在這兒復讀。富家灘接納了我,也圓了我兒時所期盼的一個心願。\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 校舍還是大姐們曾經用過的舊校舍,樑上依稀還回蕩朗朗的讀書聲,堅守着故土的老師們已經兩鬢花白,踐行着“春蠶到死絲方盡” 的使命。\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 課餘之外,我總會抽出一些時間來親近一下富家灘的山山水水,親自體驗一下印象版和現實版有何不同。\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 90年代初期,由於富家灘礦井已經不再生產,職工大部分都分流出去,富家灘的人口明顯稀落。走在馬路上,兩邊的排房門口都是老人歇息的身影,安靜、恬淡。排房的盡頭還有幾間低矮廢棄的房屋,據說是當年日本人修建的,帶着歷史滄桑的印痕。排房的盡頭就是富家灘曾經的繁華地帶,並排有幾間店鋪,幾個攤位,一兩間飯店,一個郵局,一個已經關閉的文化宮,構成了富家灘相對集中的消費陣容,讓人有一種“門庭冷落車馬稀”的感慨。\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 沿着這條路往前走,過了馬路對面,就是縈繞在我腦海深處的“階級教育館”了。十來年的風雨鏽蝕,門上的字跡已經斑駁,牆體已出現裂紋,如一個風燭殘年的老人,早已沒有了昨日的輝煌。館的左邊便是汾河水,嘩啦啦地訴說着昨日的蹉跎過往。\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 從北到南,僅用了十來分鐘便丈量完富家灘礦的領地,不免生出許多感觸:沒有燈紅酒綠,沒有高樓林立,沒有車水馬龍,就這樣一個巴掌大的荒涼瘦弱的地方,卻承載了幾多災難,幾多滄桑,幾多歷史的厚重。\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 由於學業的繁忙,只是走馬觀花地對富家灘瞭解一些概貌,但我知道,在某一個排房的某一個老人的記憶裏,一定深藏着富家灘的靈魂,富家灘的祕密。\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 也許,這就是富家灘的特點吧:不拼顏值,只講內涵。\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 拜富家灘補習所賜,我考上了礦務局護理學校,分配了工作。\u003C\u002Fp\u003E\u003C\u002Fdiv\u003E"'.slice(6, -6), groupId: '67184653767509283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