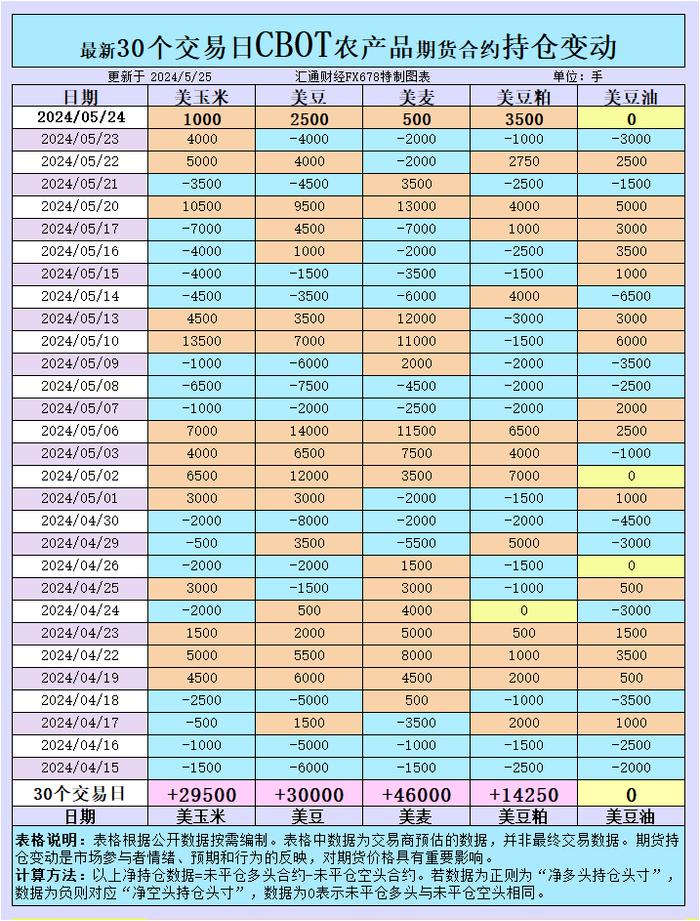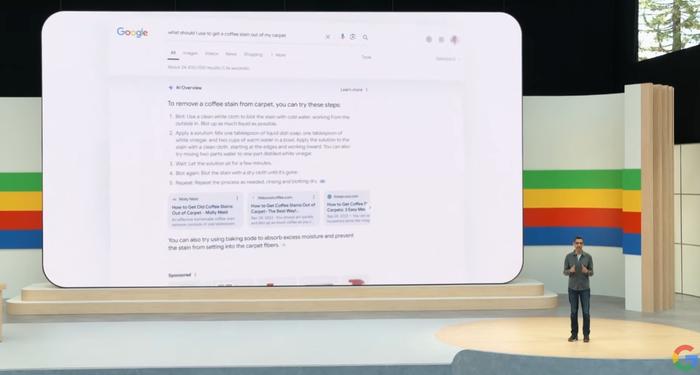窮孩子、富家子與瀕臨破碎的美國夢
文章來源:“雅理讀書”微信公衆號;作者:任軍鋒
我們生活的世界已被逼入“特朗普時代”:民主無節操,撕逼無底線;民選總統公開食言,自由媒體謊話連篇;霸權國家嫁禍於人、出爾反爾、蠻不講理、不顧喫相;生活在這樣的時代,出乎意料之事接踵而至,令人目不暇接,三觀時時被刷新,道德底線一再被下調;教科書上學到的概念框架紛紛失效,“專家”不說人話,“教授”淪爲笑柄;由於受到反覆刺激,我們的神經感覺麻木且遲鈍,卻感到莫名地失落加憤怒:表達立場吧,卻發現情節迅速翻轉終被尷尬地打臉;宣示主張吧,卻發現只能徒增噪音的分貝,原來自己只不過是在語詞的陷阱中堆砌着貧乏和無意義。我們不禁要問:在浮躁焦慮喧囂分裂怨怒等諸多症狀之下,一定潛藏着某種深層的與日俱增的社會危機。
“特朗普時代”的主體並非特朗普總統本人,即便幸得冠名,特朗普卻稱不上這個時代的首要締造者,它毋寧是之前數十年美國乃至西方政治、社會危機長期積澱的衍生物:美國人曾經引以爲傲的民主制度日趨陷入黨派傾軋的旋渦無法自拔,競選淪爲公開的金錢遊戲,政府職位被政客明目張膽地拿來作爲權錢交易的籌碼,利益集團彼此掣肘,致使亟待解決的公共政策議題只不過是政客們爲贏得職位的華麗許諾;顯得振振有辭,實際卻是語詞的泡沫;民生艱困、社會嫉怨,政客們卻在自己一手編造的美詞麗句構築的幻象之中非常醉且非常美,意識形態僵硬,公職家族化,國家軟弱,政府低效,法律制度陷入功能性失調式的政治均衡,政治衰敗日趨明顯……。
對此,政治學者福山業已作出了系統診斷。可惜國內知識界要麼囿於某種意識形態慣性,要麼爲派性立場裹挾,福山的著述只是被斷章取義、隨意用來爲各自的立場背書罷了,致使其無法真正進入福山的現實關切和理論視野。即便特朗普的“意外”當選也未能使他們在智性上獲得絲毫的長進。
如果說福山對締造“特朗普時代”的政治根源作出了全方位診斷,帕特南則通過《我們的孩子》對其背後的社會根源給出了系統分析,該書副標題“危機中的美國夢”傳達的正是作者強烈的現實關懷和深切危機意識,與2000年發表的《獨自打保齡:美利堅社羣的衰頹與重整》相比,《我們的孩子》字裏行間透露出深深的焦慮、傷感甚至悲憤,眼看自己深愛的祖國疲態日顯,貧富懸殊導致的機會鴻溝愈演愈烈,窮孩子和富家子完全生活在兩個天差地別的“美國”:富家子住在寬敞的臨湖別墅裏,日常瑣事有保姆管家打理,高牆門衛,錦衣玉食,享受最好的教育,在父母親戚鄰里朋友的助力下籌劃着美好的未來;而那些底層的孩子卻生活在毒品氾濫、暴力橫行的貧民區裏,連基本的人身安全都難以保證,穩定的家庭、良好的教育以及與之密切相連的充滿希望的前途,對他們來說無異於天方夜譚,生存對他們而言不過是無奈的掙扎,他們的人生是一曲曲在他們出生時即已被寫定的悲歌。
《我們的孩子》針對的是當下的美國,折射的卻是未來的美國。眼見國勢日頹,江河日下,帕氏不由悲從中來,《我們的孩子》無疑是帕特南的一部發憤之作。在對美國社會長期且持續的觀察研究中,帕氏目睹美國人的社會關係網不斷塌陷,人們彼此隔離,個人淪爲一個個孤島,階級差距不斷疊加,由此帶來的機會鴻溝與日俱增,下層階級通過努力改善自身境遇的外在條件相繼喪失,他們的下一代的前途早早地被定格在貧困、羞辱、絕望之中。
在書末題爲“《我們的孩子》的故事”的附識中,帕特南和他的研究助理以動情的筆調這樣寫道:“我們在本書中講述了許多窮孩子的令人悲傷的故事,但我們絕沒有在樣本上動手腳以擴大窮孩子的困境,如果說有的話,反而是我們實際上低估了生活在我們社會最底層的孩子們的悲劇人生,他們是美國社會中最孤苦伶仃的孩子。”
在走訪調查過程中,遇見的許多事令帕特南和他的團隊心碎不已:他們原本打算訪談一個工人家庭出身的男孩子,但男孩兒的父親之前問他們,他是否可以把自己的小女兒也一起帶來,只是爲了看一眼真正的大學畢業生長得什麼樣;依照慣例,他們會向參與訪談的家庭支付50美金的酬勞,中上階級的父母一般會婉拒這份報酬,但對工人階級的家庭來說,這點酬金無異於雪中送炭,足解燃眉之急,因爲那天家裏正在等米下鍋,50元錢解決了他們拖欠的燃氣費和飯錢,而另一位女孩則用這筆錢去弔唁前幾天在黑幫火併中被槍殺的一位親戚。
在過去四十年裏,美國社會組織紛紛解體,人們日趨淪爲孤零零的原子化個體,他們彼此疏離、冷漠,整個社會消極被動、一盤散沙,對此,帕特南不無憂慮地寫道:“在常規環境下,羣衆對政治穩定僅有微乎其微的威脅,而且這僅有的危害也會因羣衆自身的冷漠而化解。在這種情形下的政府可能不那麼民主,但至少可以保持穩定。
而一旦陷入嚴峻的經濟或國際壓力,就好像20世紀30年代席捲歐洲和美國的那種壓力,原本‘消極被動’的羣衆可能在一夜之間變得歇斯底里,值此之世,就會有反民主的煽動政客用極端的意識形態來操縱羣衆。”不幸的是,2016年大選以及特朗普的上臺,最終使帕特南的上述隱憂一語成讖。現在想來,當初帕特南在大選臨近尾聲在美國政治學界發起針對特朗普的聯署簽名,絕非出於一般意義上的意識形態分歧或黨派立場分野,實在是傷心到底無法釋懷不能已於言的憂憤之舉。
“美國夢” vs. 美國的現實
1 《我們的孩子》:文體
對於學院裏的研究者尤其是政治科學學者來說,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科學與行動、理論與實踐、學術與政治,構成了他們時刻需要面對的張力甚至矛盾,學院研究者經常的疑慮在於:關注公共議題,是否是學術研究本身職責所在,是否應當作爲研究者的旨趣和目標。然而,在帕特南看來,諸如此類的非此即彼的思維定勢只不過是研究者作繭自縛式的想象的產物。事實上,好的研究從來就是兩者兼得,而不是非此即彼。對政治學者來說,科學研究與現實關懷、科學真理與公衆關切、科學與政治、象牙塔與公共廣場,並非慣常所認爲的非此即彼,而只是側重點不同罷了。
政治學者孜孜以求的應當是一種“更加務實的政治科學”(a more engaged political science)、“具有批判眼光的變革主義的政治科學”(acritical, reformist political science),它要求政治研究者在事實與價值之間做跨界思考,拋棄所謂“價值無涉的社會科學”或“事實無涉的哲學批判”,“問題”先行而非“方法”先行,尋找經濟學、社會學、心理學、歷史學等學科之間積極的跨界合作,通過提出新的與當代社會密切相關的重大問題,突出那些被忽視的價值,找出影響這些價值的關鍵要素,揭示事實與價值之間內在的邏輯關聯,從而與社會公衆展開真誠的對話,政治科學家能夠對公共生活做出積極貢獻。在2002年新一屆美國政治學會主席就職演講中,帕特南強調指出,好的社會科學研究無不關注最爲緊迫的公共議題,政治科學承擔着重要的公共使命,對公民同胞的日常關切作出有針對性的回應,非但不是政治科學研究者的額外義舉,而是政治學者追求科學真理過程中不可推卸的責任和題中之意。
一種更加務實的政治科學的旨趣“既不是向當權者提供明智的意見建議,更不是充當高高在上的牛虻,而是這樣一種政治科學,它力圖開啓與公民同胞真正意義上的對話,在啓迪他們的同時,也從他們那裏獲得新知。”它是一種嚴肅誠懇、開放包容的公民教育(civic education)過程,其核心旨趣在於涵育有着強烈“立法家”情懷、關心並積極參與政治行動的公民,而不是充滿“怨婦”情緒的消極旁觀者、怨憤者。
帕特南自己正是用上述原則使命的踐行者。從《獨自打保齡:美利堅社羣的衰頹與重整》(2000年)、《和衷共濟:復興美利堅社羣》(2003年)、再到《我們的孩子:危機中的美國夢》(2015年),相繼高居暢銷書榜,相關議題引發了廣泛且熱烈的跨界討論。在哈佛教授羣中,類似帕特南這樣的公共寫作者並非孤例,從早期的費正清、賴肖爾,到傅高義、約瑟夫.奈,再到晚近的桑德爾(Michael Sandel)、弗格森(Niall Ferguson)、艾利森(Graham Allison)。這樣的公共寫作不僅要求研究者具有較爲深厚的學術造詣,還要求他們具備嫺熟的文字把控能力,從謀篇佈局到故事線索,寫作者既要言簡意賅穩健精到地將核心論題抽絲剝繭、層層推進,又要充分掌握讀者的閱讀節奏,牽引閱讀者的注意力,使其完全進入寫作者構築的文本世界,循着故事情節的次第轉換產生強烈的代入感和精神共鳴。
得益於團隊助理高水準的文字編輯能力和出版編輯的文稿編輯素養,《我們的孩子》在文體上可以說達到了爐火垂青的地步,加之兩位中文譯者田雷、宋昕已入化境的譯筆,更是錦上添花,可謂中文讀者一大幸事。從結構上看,《我們的孩子》圍繞縱橫交錯的兩大軸心展開:縱軸即“50年代”與“21世紀”前後四十年對襯,橫軸即“窮孩子”與“富家子”人生故事的對比,每章論題都以具體而微的個體經驗開篇,繼之推演至一般性的學理分析,具體案例與一般學理彼此交融,既有“顯微鏡”,即深度聚焦,觀察單個孩子及其家庭、社區的生活經驗,又有“廣角鏡”,即涵蓋多學科的智識資源,同時包容更多元的視角。
全書文字極具畫面感,由近及遠,又由遠及近,鏡頭切換與論題轉換相互配合,嫺熟自如,天衣無縫。作者文筆簡潔生動,要言不煩,讀之如同觀看一部牽動人心的紀錄片。筆者這裏建議有興趣的讀者不妨先閱讀書末附識“《我們的孩子》的故事”和“致謝”兩部分,帕氏在其中詳細交代了整個調研和成書過程,讀者會發現作者將豐富的個體生命感受充分融匯在整個調查研究過程之中,讀之感人至深,相信對相關領域的研究者和初學者都會啓發多多;接着可以讀第六章“路在何方”和第一章“美國夢:幻象與現實”,最後依次分別讀第二(家庭結構)、三(爲人父母)、四(學校條件)、五(鄰里社區)各章,而全書核心論題正是圍繞這四個方面展開的。
2《我們的孩子》:論題
《我們的孩子》聚焦的小羣體,揭示的卻是大問題。
《我們的孩子》的研究對象是“小羣體”,即18歲到22歲的美國年輕人,這個年齡段的孩子正值高中畢業,剛剛步入成年,他們開始籌劃自己的未來,是進入大學還是走向社會。他們身上都留下了明顯的成長痕跡,他們的社會處境和精神狀態無疑向我們打開了一扇窗戶,通過它,我們可以透視他們童年成長的環境,包括家庭、父母、學校、鄰里等方面的成敗利鈍、利弊得失。
《我們的孩子》揭示的是“大問題”,即美國過去四十年累積起來的結構性危機:貧富懸殊愈演愈烈,階級鴻溝不斷拉大,階層隔離觸目驚心,社會流動舉步維艱,窮孩子與富家子生活在完全不同的世界,天差地別的家庭出身和成長環境,使得窮孩子力圖通過個人努力改善自身處境的可能性幾近於零,機會平等不復存在,“美國夢”瀕臨破碎,一個“窮人的美國”與一個“富人的美國”,彼此區隔、相互疏離,兩個世界的孩子由於完全不同的成長經歷,他們對他人、社會的看法也截然對立。
細思恐極,如果說今天的美國在爲過去四十年不斷積累的社會危機“買單”,那麼可以想見,明天的美國也將不得不在社會和政治方面爲“兩個美國”可能導致的惡果付出沉重代價,爲此,帕特南發出如下警示:“階級之間的機會鴻溝不僅會危及美國的繁榮,而且會破壞我們的民主,甚至是我們的穩定。”
富家子在暢想未來,從容構築他們的詩和遠方,而窮孩子連眼前的苟且都不可得,更別說對未來的希望。
克林頓港的“大衛”,18歲,從童年開始,父母離異,家庭破碎,居無定所,父親酗酒、吸毒,最終因搶劫被關進大牢。由於無人照顧,大衛淪落爲社會盲流,打架鬥毆,結交狐朋狗友,尋釁滋事一度被關進少管所。在訪談中,帕特南和他的團隊發現,大衛並非一般人想象的那種無可救藥的壞人,事實上,他對九個同父異母的兄弟姐妹懷有強烈的責任感,他渴望家庭的溫暖、父母的關愛,但這些對他來說實在是過分的奢望。
更爲雪上加霜的是,大衛的女友意外懷孕,生下一女後棄他而去,而且後來發現這個孩子不是大衛自己的,即便這樣,大衛也欣然承擔其對孩子的監護責任。或許是因爲面對訪談,大衛要故作男子漢的堅強,強作鎮定,但生活對他來說實在是一部“狗血劇”,孤獨焦慮,不堪重負,暗無天日,他要求不高,命運卻對他如此吝嗇,幾無生存下去的希望,他在Facebook上的一次狀態更新反映的纔是他的真實心境:“我總是人生輸家,我只想再感受下完整的生活,爲什麼卻一錯再錯!我對生活竭盡全力,但卻一無所獲。完了……我他媽的真完了!”
俄勒岡本德鎮的“凱拉”,她生在一個家徒四壁、一貧如洗的家庭,全家依靠父親打零工勉強度日,凱拉有五個兄弟姐妹,要麼同父異母,要麼同母異父,屬於典型的“拼盤家庭”。父母離異後,各自再婚,凱拉跟着父親,艱難度日。然而禍不單行,父親中途又患重病,凱拉不得不承擔起照顧父親的重任。當初父母離異給青春期的凱拉造成巨大的心靈創傷,她性格變得孤僻自閉,抑鬱症狀表現日趨明顯,他懷疑生活,懷疑他人,對凱拉來說,“這個世界變幻莫測,難以駕馭,充滿惡意。……在她的人生中從來沒有過穩重可靠的長輩。‘好像我的人生一直在走下坡路,生活的一切都在瓦解、崩潰’”
還有在亞特蘭大北城一座破敗的購物中心裏幹打包雜物體力活的“伊利亞”,還有加利福尼亞橘子郡的“羅拉”和“索菲亞”姐妹,還有住在費城最危險的街區肯辛頓的“麗莎”和“艾米”姐妹,還有……這一幕幕出身工人階級家庭的美國年輕人的生命悲歌,絕非作者刻意篩選出來以博取布爾喬亞們同情的素材,而是一場遍及全美的“美國噩夢”來臨的朕兆。作爲讀者,我們儘可以懷疑作者選擇講述案例的所謂“客觀性”,但那些關於美國貧富分化、階級隔離的冷冰冰的統計數據卻不會騙人:“從克林頓港到費城,從本德鎮到亞特蘭大再到橘子郡,家庭之間的經濟懸殊是每一段故事的關鍵情節。每段故事各有不同,但不變的是令聞者傷心,甚至感覺到危機將至的伏線:下層階級家庭的經濟狀況每況愈下,但與此同時,上層階級的父母卻控制着越來越多的資源。”
3《我們的孩子》與我們
《我們的孩子》是一曲由諸如大衛、伊利亞這樣的窮孩子們生存境遇合成的命運悲歌。帕特南筆調溫暖而不失理性,通過講述那些窮孩子們令人心碎的人生故事,帕特南絕非意在暗示富人道德上的冷漠、批評政府的無能、譴責所謂社會的不公,更不是要將危機的源頭歸咎於某種單一的責任方,而是條分縷析,從諸如婚姻家庭、學校狀況、鄰里社區等各個不同的角度,揭示導致階級隔離和機會鴻溝在美國愈演愈烈的紛繁複雜的社會根源。
帕特南洞察到危機的伏線,同時不放過任何人性的光輝,改變現狀的希望: 出身拉美裔移民家庭的“克萊拉”和“裏卡多”夫婦,青少年時期曾在貧民窟度過,個人的不懈努力,加上幸運地得到學校老師的加持鼓勵,克萊拉得到良好的受教育機會,作爲第二代移民,他們已經完全擺脫了上一代的困境,成功攀登至中上階層。也許出於自身的人生經歷,克萊拉對女兒的教育可謂不遺餘力,但這位典型的拉美裔“虎媽”並沒有忘記那些出生在貧困家庭、成長於危險社區的孩子們,如今克萊拉是一名兒童社工義工,在她眼裏,那些孩子同樣也是“我們的孩子”。
這位媽媽可不是如今一般的富人的做派,而是作者在20世紀50年代記憶中的美國家長:他們認識到每個人都不是一座座孤島,他們深知養育一個孩子,需要舉全村之力,需要美國社會中那些幸運者向那些不幸者施以援手。或許援助者力所能及的付出,就足以幫助諸如大衛、凱拉、伊利亞、米歇爾、羅拉和索菲亞、麗莎和艾米們擺脫困境,改變他們的人生軌跡。
美國人所奉行的絕非如人們慣常想象的所謂“堅定不移的個人主義”,事實卻是,每個人的潛力只有在家庭、鄰里、社羣的守望相助中才能得到發揮甚至放大。爲此,帕特南提醒我們,美利堅民族的創業史更準確的形象應是“一列馬車隊伍,上面滿載着同心戮力的邊疆拓荒者,他們篳路藍縷,以啓山林。”《我們的孩子》正是要在個人主義風潮已經佔據上風並漸成壓倒之勢的時代,讓更多的美國人認識到危機的根源,喚醒他們的道德和社會責任,它不僅在通過學術表達以揭示病源,更在於提出有針對性的行動路線,號召人們正視危機並及早行動起來。
對於美國人和中國人來說,過去四十年的歷史敘事似乎呈現出完全不同的基調:一個顯得疑慮重重,躑躅彷徨,一個顯得高歌猛進,自信滿滿。對於《我們的孩子》所診斷的“美國病”,我們毫無理由作壁上觀,甚至幸災樂禍。要知道,所謂的“美國病”絕非“美國的病”,它毋寧是典型的“現代病”,它正在困擾美國,帕特南開誠佈公,直面問題,尋找解救之道。他的學術勇氣、智性的真誠以及面對複雜的現實問題時的謙卑,難道不值得同樣作爲學者的我們自我檢省?不寧唯是,《我們的孩子》還爲我們提供了一面透鏡,通過它,我們或許能夠更加清楚地發現類似的疾病正在我們的社會肌體內生根蔓延。
《我們的孩子》屬於美國,更屬於我們。
(注:本文所有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均不代表鳳凰網國際智庫立場)
查看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