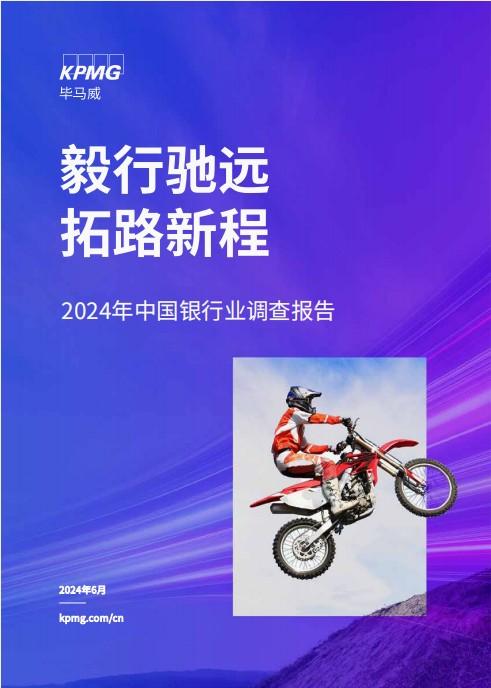米塞斯的世界不只是陰鬱的經濟學
摘要:\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大師身影后的獨立女性\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讀《米塞斯夫人回憶錄》時,我頗有些感到悲哀的是,瑪吉特只能以“米塞斯夫人”這一名號和形象留存於歷史中。\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因此,儘管瑪吉特不是米塞斯的學術伴侶,她自己也苦惱於要費很大的勁才能理解丈夫從事的經濟學研究,但夫妻二人絕非缺乏精神交流。
"\u003Cimg src=\"http:\u002F\u002Fp1.pstatp.com\u002Flarge\u002Fpgc-image\u002FRXdSuJeBg687mg\" img_width=\"1080\" img_height=\"1458\" alt=\"米塞斯的世界不只是陰鬱的經濟學\" inline=\"0\"\u003E\u003Cp\u003E(圖片由出版社提供)\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嚴鵬\u002F文\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作爲一名經濟思想史研究者,我對經濟學家的自傳興味盎然。學術史尤其文科學術史的演化,不是知識與理論的單線進步或機械積累,它充滿意外和偶然,與學者的人生際遇往往有着直接關聯。文科學者“知”與“行”的關係通常比理工科學者存在着更大的張力,要理解思想史或學術史,對兩者的考察不可偏廢。學者的自傳是其“行”的最原始記錄,有着高度的史料價值。較爲少見的是學者的伴侶留下自己的回憶錄,尤其那些非學術圈的伴侶。《米塞斯夫人回憶錄》就是這樣一本經濟學家米塞斯非學術伴侶留下的文字,若對米塞斯的生活感興趣,讀之定會興味盎然。\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零星的經濟思想史史料\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兩年前讀《米塞斯回憶錄》,我最大的感觸是,這個堅持自由至上主義學說的經濟學家,在爲人處世方面表現出了很大的靈活性與務實性。米塞斯寫道:“在學術上,妥協是對真理的背叛。但在政治上,妥協卻是必不可少的,許多時候只有通過互相沖突的觀點的折衷,才能取得一點進展。學術屬於個人的成就,從定義上看不屬於協作的產物;政治則永遠是人羣的合作,並且常常意味着妥協。”\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當《米塞斯夫人回憶錄》中譯本出版後,我懷着極大的興趣,第一時間去閱讀。不過,瑪吉特·馮·米塞斯,這位奧地利學派大師的妻子,提筆便向讀者發出警告:“這本書不會回答任何經濟學問題,也不會講學院智慧。它要回答的是我的丈夫路德維希·馮·米塞斯的許多個人問題。”讀完整本回憶錄後,會發現此言不虛。不過,由於文科學者的“知”與“行”高度纏結,從米塞斯的個人問題裏,也能發現不少零星的經濟思想史史料。\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由於《米塞斯回憶錄》只寫到米塞斯1940年逃離納粹抵達美國爲止,因此,《米塞斯夫人回憶錄》是從個人生活角度對《米塞斯回憶錄》有益的補充。瑪吉特尤其詳細記錄了他們夫妻抵達美國後的日子。瑪吉特是一名女演員,並非經濟學圈中人,她無法敘述太多丈夫工作的細節。不過,她記錄了米塞斯工作的狀態。其中最有史料價值的或許當屬第八章《的故事》。該章詳細敘述了米塞斯的代表作《人的行爲》是在怎樣的狀態下寫出來的,以及米塞斯與出版該書的耶魯大學出版社的糾紛。\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此外,儘管瑪吉特回憶錄中對人物的品評不能算是她丈夫態度的直接反映,但仍然可以藉此一窺米塞斯的人際交往與關係世界。例如,瑪吉特提到,米塞斯的一位學生告訴她,米塞斯在課堂上如此評論熊彼特:“有很多人……堅定不移地支持熊彼特教授的社會理論。他們似乎忘了,這位偉大的教授擔任財政部長時,沒能夠讓奧地利避開史上最具破壞性的通貨膨脹。當這位偉大的教授擔任一家銀行(彼得曼銀行)的總裁時,這家銀行倒閉了。”寥寥數語,直觀地反映了米塞斯對熊彼特的態度。這種態度源自學術觀點上的不同立場,有着超越於個人關係的思想史意義。\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立體而豐富的米塞斯形象\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米塞斯是瑪吉特的第二任丈夫。米塞斯44歲時遇到這位喪偶的女演員,45歲向她求婚,但因爲米塞斯對婚姻突然的恐懼和納粹上臺後的時代風雲變幻,直到58歲時,米塞斯才和他的心上人成婚。對有些人的愛情來說,時間並不那麼可怕。與熊彼特最終娶了一位優秀的學生不同,米塞斯無意於找學術伴侶。瑪吉特稱,米塞斯曾對她說:“你能想象我跟一個經濟學家結婚嗎?”或許,米塞斯認爲,學術屬於個人成就,所以他不需要學術伴侶來進行協作吧。\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米塞斯早年喪父,瑪吉特這樣描寫他的母親:“那些瞭解路的母親的人告訴我,她是一個聰慧的女人,但有着將軍般的態度和鋼鐵般的意志,極少對他人表露熱情和關愛。”值得注意的是,瑪吉特認爲“路在心裏肯定不想和母親住在一起”。這與頗爲戀母而性格溫和的熊彼特,大不相同。成長經歷與母親的個性,或許可以解釋米塞斯威嚴而易怒的性格。與母親的某種緊張的心理關係,則或許能解釋這個剛毅的男子爲何在44歲以後對心儀的女性表現出小男孩一般的低姿態。\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讀過《米塞斯夫人回憶錄》後,我極爲敬佩米塞斯的工作規劃能力。瑪吉特寫道,當米塞斯還在追求她時:“我不知道他是怎麼擠出時間來做手上的工作的。當時他是商會的全職法律顧問和金融專家,在維也納大學開設有課程,要負責研討班,要和來訪的當局一起開會和喫午餐,要出差,還要進行大量的閱讀和寫作,但他總有時間給我。他對我的工作很感興趣,他不僅讀我翻譯的每一部戲劇,還總勸我自己也寫些東西,並不斷給我提供思路。”瑪吉特記錄了一個小細節:“他時常說:‘剃鬚時我腦子裏會蹦出好點子來,所以這時候我也沒落下寫作。’”大師高產的奧祕或許就在於此吧。反過來說,當我們這些普通人抱怨不同性質的工作擠壓時間過甚或者苦惱於寫不出東西時,或許因爲我們確實缺乏大師的工作規劃能力與旺盛精力。\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大師身影后的獨立女性\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讀《米塞斯夫人回憶錄》時,我頗有些感到悲哀的是,瑪吉特只能以“米塞斯夫人”這一名號和形象留存於歷史中。當然,瑪吉特本人是不會介意這些的。不過,考慮到熊彼特的學術伴侶,一位卓越的經濟學者,也完全被熊彼特遮蔽了光芒,那麼,瑪吉特這樣的非學術伴侶,是不是更幸運一些呢?\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不過,瑪吉特可不是什麼花瓶。她是她那個時代的獨立女性。儘管人們讀《米塞斯夫人回憶錄》的目的,可能主要是希望瞭解米塞斯,而且瑪吉特也抱有爲丈夫立傳的意圖,但她本人的經歷也非常值得稱道。瑪吉特出生於漢堡,父親是當地最早的一批兒童牙科醫生之一。幼年時的瑪吉特接受了良好的教育:“我愛我的學校,愛讀書。我父親也愛讀書。每當晚上父母休息之後,我就去客廳把父親當天讀的書帶回臥室,伴着燭光閱讀,還把一條毯子放在房門底部遮光。我父母從未發覺這件事。”那時,德國還沒有專門給女孩開設的高中,瑪吉特的父親想讓女兒學醫,就讓她參加“教師研討會”,並私下裏學習拉丁語。\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良好的家庭氛圍塑造了瑪吉特的智性,但瑪吉特比她父母所設想的走得更遠。17歲時,她擔任一場業餘表演的主演後,迷上了舞臺。那個年代,德國的中產家庭是不會想讓女兒成爲女演員的,瑪吉特就乾脆離家出走,通過看報紙廣告找了一份家庭女教師的工作,迫使父親同意她從事自己渴望的職業。這種叛逆不會令一般的父母感到高興,但憑藉自由意志選擇自己的人生道路,不正是人格獨立的體現嗎?日後嫁給了自由主義大師的瑪吉特,早已用自己的行動在追求與踐行自由。\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因此,儘管瑪吉特不是米塞斯的學術伴侶,她自己也苦惱於要費很大的勁才能理解丈夫從事的經濟學研究,但夫妻二人絕非缺乏精神交流。在米塞斯、熊彼特與凱恩斯成長的那個年代,文科學術遠沒有今日的規範化與標準化,最傑出的經濟學家在經濟學研究之外,往往有着對歷史、文學、藝術的深入理解與不俗品味。這種教育和文化基礎,使米塞斯能與瑪吉特保持智性與精神的交流。瑪吉特寫道,在夫妻二人的假期裏:“他讓我去讀一本書,讓我學習如何去寫短故事。他說:‘實際上,要注意的只有一件事,你要圍繞一個令人喫驚的結局來建立整個故事。如果你能做到這一點,你就能寫出好的故事來。’那年夏天我寫了一個又一個的短故事,我的點子很多;但回到紐約之後,我因爲要忙着照顧路的生活而無法再聽從他的建議了。”\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再如,在一次又一次感嘆米塞斯時間規劃能力超羣的同時,瑪吉特也透露了夫妻二人的業餘生活:“儘管我不知道他是如何做到的,但他給每一件事和每一個人都安排好了時間。他的大腦和時間被分配得很好,而且每逢週六或週日,如果不用跟全國製造商協會開會的話,他早晨都會跟我去博物館或藝術畫廊,晚上則會一起去劇院。”小說、博物館、畫廊、劇院,米塞斯的世界不只是陰鬱的經濟學,而瑪吉特屬於那個優雅的藝術的世界。\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如果站在今日某種流行版本的女權主義的立場上看,米塞斯夫人的獨立性或許很不夠。實際上,她的再婚也包含着不無功利色彩的撫養小孩的經濟考量。但在瑪吉特成長的那個昨日世界,茨威格曾回憶,維也納中產階級子弟裏的文藝青年對女孩子不屑一顧,認爲她們在智性上要低一等。毫無疑問,瑪吉特是那個年代裏少有的獨立女性。而獨立也好,自由也罷,都是具有歷史性的。米塞斯或許不會同意這種歷史主義的觀點,但在歷史主義的視角下,他摯愛的瑪吉特才能從大師的身影后彰顯出一名獨立女性的魅力。\u003C\u002Fp\u003E"'.slice(6, -6), groupId: '67191409573143516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