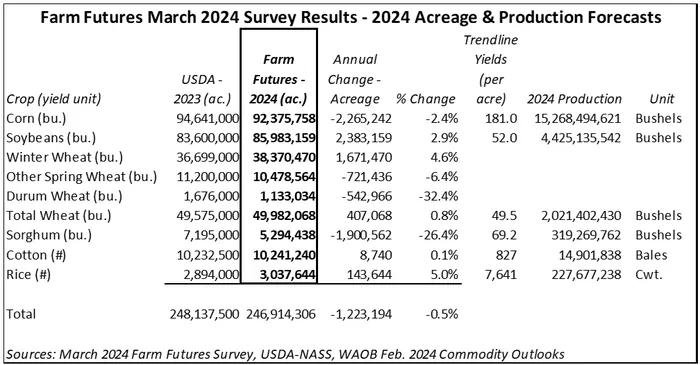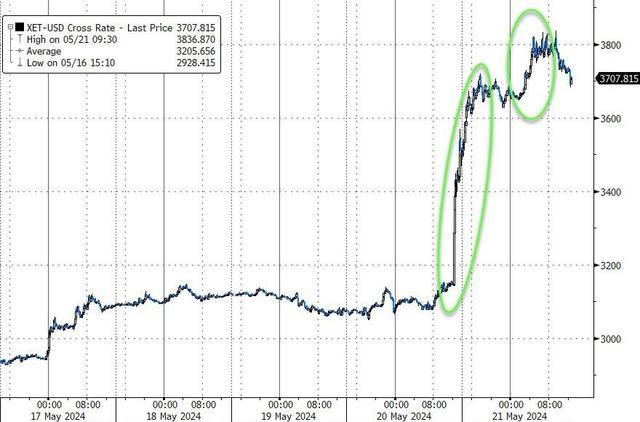点绿成金 路出太行
摘要:\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有模有样地剪苹果树,李保国是从马峪沟开始的。”\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向来“说一不二”的前南峪村党委第一书记郭成志,这次笑得很不好意思,“于老师说的对,我输了。
"\u003Cp\u003E5月18日,知道河北农大教授郭素萍来了,家中养病的郭成志执意要出来接。\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前南峪能有今天,你们是头功。”郭成志握住郭素萍的手,“村里要建三座纪念亭,感谢河北农大,纪念于宗周老师,纪念李保国老师。”\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983年,河北农大教授于宗周带领的小流域综合治理课题组进驻前南峪。课题组一对年轻的“夫妻档”就此扎下根来,他们正是李保国、郭素萍。\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人老了,山正青。\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老书记,还记得当年你和于老师打的赌不?”郭素萍笑着说,“你说马峪沟一年要能赚30万,钱就分于老师一半。”\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向来“说一不二”的前南峪村党委第一书记郭成志,这次笑得很不好意思,“于老师说的对,我输了。”\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对赌马峪沟 科技才是真财神\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科技的力量,前南峪人在于宗周来之前就领教过。\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到1976年,前南峪山上的栗树已有13000多棵,但结果的不过2300多棵。\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一棵树一年产栗才6斤多。”郭成志彻夜难眠,满山果木,啥时候能见着收益?\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听说昌黎果树研究所有个叫王金章的,板栗技术厉害。郭成志三赴昌黎,把他请到前南峪。\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王金章带着剪子来了,过他手的老栗树,一棵能剪下几百斤枝子。\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碗口粗的树枝齐根而下,我们在旁边看着都害怕。”村民郭双庆加入了王金章的栗树修剪专业队,但“轮到自己动手,心都颤”。\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老人们更受不了,在村里指着鼻子骂,“树枝子就像人的胳膊腿,给你都砍了,你还能活?败家子!”\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还有人半夜偷摸上山,砸碎了王金章磨剪子的磨刀石。\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但第二年秋天,被修剪的栗树产量增了3倍。\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村里年人均收入因此净增300元。对王金章的质疑这才算平息。\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但于宗周一来,就放了个比王金章大得多的“卫星”。\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到时候,马峪沟每年能给乡亲们带来30万元收入。”开群众大会,郭成志把于宗周推上台,这位大教授一张嘴,就把底下惊得连咳嗽声都没了。\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有村民喊了一嗓子:“这是哪来的疯子!”\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不怪人们不信。往年,马峪沟最多拿回5000块钱。”郭双庆说。\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不光村民不信,郭成志也不信。他指着马峪沟坡上的树跟于宗周叫板:“于老师,你要真能让马峪沟产出30万,村里分你一半。”\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穷山恶水,是山区贫穷落后的‘根’。”于宗周说。\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这位水土保持专家带来的队伍,不光是来剪树,还要挖出“穷根”。\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浩大工程就从马峪沟开始。\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爆破声中,课题组设计的“隔坡沟状梯田”模样初显:在保留原来坡面的基础上,开挖水平沟,把梯田修成外高里低的“噘嘴形”;横向按照来水一方稍高的“渐低形”盘旋。既能加厚活土层,又能把雨水蓄积起来。\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搞栽培管理的,搞肥水管理的,搞病虫害防治的,课题组里专家云集。”多专业多学科都在前南峪的一片片山坡上结合起来,郭素萍说,“治法就有9种。不同坡度、坡向、植被条件的,都采取了不同的治理方式。”\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梯田里埋下排水沟,沟底设下塘坝拦挡。经过改造后的马峪沟,小雨不出田,大雨不出川,暴雨不成灾。\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996年那场洪水中,前南峪考出满分的秘密,都藏在这些沟状梯田里。\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蓝天白云,青山绿岭。5月19日,记者跟着郭素萍重走马峪沟。30多年前修出的梯田整齐依旧,风化成土的片麻岩滋养果木茁壮成林。\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当初“种什么不长什么”的片麻岩山坡上,如今栽着乌克兰大樱桃、欧洲榛子、美国葡萄、澳洲油桃。\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这效果,和当初大伙儿想的一样。”郭素萍说。\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这收益,早就不知超了30万多少。”郭双庆说。\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这套开发模式和技术体系,日后成为太行山乃至国内其他山区综合开发的经典范式。前南峪,也因此成为“太行山道路”的先行地和引领者。\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高新技术示范园区、国内外优种果树引种示范园区、优种苗木繁育示范园区等相继建成;天津大学院落污水低能耗净化技术,农业部规划设计研究院连续式热解炭气清洁联产技术等接连落地。\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科技才是真财神。”早年要把王金章赶出山的前南峪人,如今对此笃信不疑。\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剪”来的教授 大山是一座课堂\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苹果咋还没套袋?”\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我抓紧。”\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疏果也不到位。一拃一个。再稀稀。”\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沾。”\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沾沾沾’,嘴上答应挺好,手上就是不动,再不麻利着点,这树就没样了!”\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5月19日,站在马峪沟沟底,郭素萍冲坡上忙活的农民喊话,像当家大姐在催自家弟兄。\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没有不熟的人,没有不熟的路,郭素萍说,“来这儿就像回娘家。”\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当年一进山,李保国和郭素萍就搬进了半山腰黑黢黢的石头房。看资料靠煤油灯,三餐多半是豆沫汤里加蔓菁条,床上跳蚤四处乱蹦,随手一捏,噼啪作响。\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条件这么苦,自己不跑就不赖了。可没多久,李老师还把儿子和丈母娘也接了来,一住就是4年多。”郭双庆说。\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吃苦受累没问题,要是一事无成,我才觉得有点不合适。”郭双庆说,这是李保国的原话。\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到了水文观测月,一下雨,农民都往屋里跑,郭素萍却往外冲。“好几个监测点都要跑到,水量、流速才能记得周全。”郭素萍齐膝高的雨靴,回来能倒一盆水。\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李保国更拼。爆破整地,他自己炒制土炸药。一次遇到哑炮,不等别人近前,李保国先跑过去查看,突如其来的爆炸把他崩了个大跟头,险些搭进性命。\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开始时看不出门道,时间长了,村里人都瞧明白了:郭素萍采集的数据、李保国开出的水平沟,环环相扣,精确地搭建着图纸上的梯田林地。\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他们改变着前南峪,前南峪也在改变着他们。\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少有人知的是,苹果专家李保国的科班专业是桑蚕,果树管理只是兼修副业。\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有模有样地剪苹果树,李保国是从马峪沟开始的。\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马峪沟的苹果树,品种老,产量低,却是乡亲们为数不多的收入来源之一,分外珍贵。\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最见不得农民穷”的李保国,决心向马峪沟的苹果树要效益。\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可村民们不敢把树交给从没管过苹果的李保国。\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有农民在保国剪过的苹果树上钉牌子,上边写着,‘李保国剪的树’。”郭素萍说,那意思就是,这树要剪坏了,不长果了,都怪你李保国。\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无奈之下,李保国和村民们立下字据:承包100棵苹果树,出了问题包赔损失。\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树怎么剪,枝怎么留,保国对每一个技术细节都抠得仔细。”郭素萍说,“光他手绘的苹果树修剪图,就攒下好大一本,画得细致逼真,讲得清楚明白。”\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按照“基部三主枝、疏散分层形”的树形,李保国剪去长枝弱枝,苹果树焕然一新。转到秋天,亩产增了一倍。\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为了提升品质,李保国又自己出钱买来80棵红富士树苗,开始了嫁接育苗的试验,此后闻名全国的浆水苹果,生发于此。\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山地爆破,苹果栽培,在桑蚕专业教科书里面找不到只言片语。但凭着论文《山地爆破整地造林技术研究》,李保国从讲师晋升副教授;论文《发展经济林促进了前南峪的经济振兴》则为他晋升正教授加了分。\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前南峪是个大课堂。\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你得会说,望一眼,就得说出这个园、这棵树主要有什么问题。你得会干,得教会人家问题怎么解决。”郭素萍说,李保国经常跟她分享在前南峪收获的新学问。\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2016年4月2日,李保国最后一次来到马峪沟,叮嘱大伙儿尽快给苹果树安装滴灌。\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8天后,他去世的噩耗传到前南峪。\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细小的塑胶管,泌出透亮的水滴,沁入松散的片麻岩风化土中,如今,李保国惦记着的滴灌设施滋润着马峪沟的苹果树。\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郭素萍检查着树下覆盖的地膜和有机肥,“这是前些天我们送来的,地膜减草,有机肥提升果品质量,配合滴灌再好不过。”\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走下坡来,郭素萍停下脚步。一片新辟出的平地上,安放着一块小小的墓碑。\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那里埋着于宗周的骨灰。\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就葬在这儿,和郭成志打赌的地方,他特意嘱咐的。”郭素萍说,“村里人,哪儿会随便让外人埋在自己地里呢。但于老师下葬,大伙儿都来了,跟送自家人一样。”\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就是在这里,郭成志提到的三座纪念亭,将耸立而起。(记者 桑献凯 张怀琛 郭伟)\u003C\u002Fp\u003E"'.slice(6, -6), groupId: '67196071081043563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