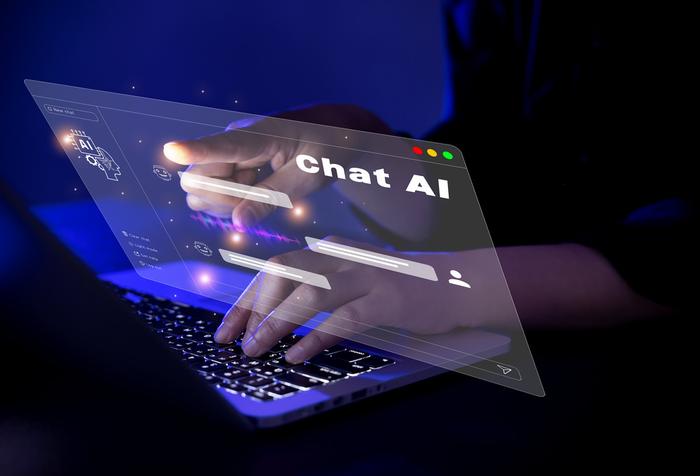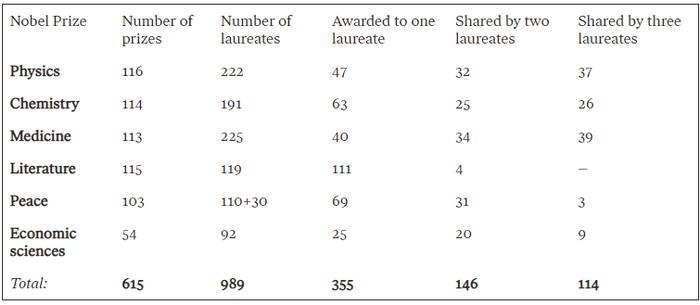譯者||陳衆議:楊絳,永遠的女先生
"\u003Cp\u003E本文來源:文藝報\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轉自:\u003C\u002Fp\u003E\u003Cimg src=\"http:\u002F\u002Fp3.pstatp.com\u002Flarge\u002Fpgc-image\u002FRXoREJHCHDtoYU\" img_width=\"300\" img_height=\"300\" alt=\"譯者||陳衆議:楊絳,永遠的女先生\" inline=\"0\"\u003E\u003Cp\u003E楊絳先生離開我們已有時日。讀者的嘆惋和哀悼仍在繼續,媒體的追詢和驚爆已漸趨平允,而我也從悲痛和忙亂中緩過神來。自先生病重住院到彌留之際再到起靈往八寶山浴火重生,我見證了幾乎每一個細節。這是我幼年送別祖母以來第一次全程參與,甚至可以說是受命主持的一樁後事。可它是怎樣的一樁後事啊!它是我國現代文壇最後一位女先生的後事。它意味着一個時代的結束,一代大師的遠去。\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有關先生的報道已經很多,我似乎再也說不出什麼“新鮮”的話來。但近20年因工作關係與先生接觸的點點滴滴卻不斷浮出腦海,揮之不去。從這個意義上說,她並沒有離開我們。\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我們知道,先生是在痛失愛女和丈夫之後的近 20 年間再度爲社會所廣泛\u003Ci class=\"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 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style-5\"\u003E關注\u003C\u002Fi\u003E的。在此期間,她排除所能排除的一切干擾,信守諾言。那是她作爲一位賢妻對丈夫的最後承諾:“你放心,有我呢!”須知錢鍾書先生是在愛女錢瑗去世後一年多撒手人寰的。他罹患重病期間一直惦念着久未露面的女兒,無如之下楊先生只好以各種藉口搪塞、隱瞞、安慰,並用那簡單而有力的諾言讓錢先生安心離去。\u003C\u002Fp\u003E\u003Cimg src=\"http:\u002F\u002Fp3.pstatp.com\u002Flarge\u002Fpgc-image\u002FRXoREJbDSZNzVB\" img_width=\"500\" img_height=\"362\" alt=\"譯者||陳衆議:楊絳,永遠的女先生\" inline=\"0\"\u003E\u003Cp\u003E錢鍾書、楊絳、錢瑗合影\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然後,作爲一位成名遠早於丈夫的才女,她還有自己的使命。她在無比悲傷和寂寥的一個個漫漫長夜和一個個茫茫日子裏,翻譯了柏拉圖關於靈魂的《斐多》,創作了《從丙午到流亡》《我們仨》《走到人生邊上——自問自答》和《洗澡之後》,主持編輯了《楊絳全集》,主持整理了《錢鍾書中文筆記》(凡20卷)、《錢鍾書外文筆記》(凡 48卷)。這些先後由北京三聯書店、北京商務印書館和人民文學出版社付梓出版。其中據不完全統計,《我們仨》在海內外累計印行 40餘次,發行數百萬冊(還不包括大量盜版),成爲當代傳記文學不可多得的範例。先生以一貫的平和、翔實、婉約和純真,再造了女兒,喚回了丈夫,展示了三口之家鮮爲人知的尋常的一面、快樂的一面、親切的一面、素心的一面。小錢瑗畫父親帶書如廁,可謂童趣橫生。它讓我想起了楊先生對坊間關於其丈夫“過目不忘”的回應。她說,“鍾書哪裏是過目不忘?他只不過筆頭較常人勤快、博覽強記罷了。”皇皇68卷中外文筆記印證了楊先生的說法。這些筆記見證了錢先生是怎樣大量閱讀、反覆閱讀各種經典的。許多中外名著出現在他的讀書筆記中,可謂經史子集無所不包;但稍加留意,我們就會發現一些奧妙或規律,即錢先生的閱讀習慣:一是讀名著,儘量不把有限的時間浪費在閒雜無聊的消遣書上;二是他每每從原典讀起,並且反覆閱讀,爾後再拿註疏、評述和傳略來看。\u003C\u002Fp\u003E\u003Cimg src=\"http:\u002F\u002Fp1.pstatp.com\u002Flarge\u002Fpgc-image\u002FRXoREJrANTzT4I\" img_width=\"500\" img_height=\"348\" alt=\"譯者||陳衆議:楊絳,永遠的女先生\" inline=\"0\"\u003E\u003Cp\u003E錢鍾書讀書\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錢楊二位先生藏書不多,他們的取法是借書讀。用楊先生的話說,個人藏書再多也不過滄海一粟。因此,他們是圖書館的常客,無論國內國外,所到之處概莫能外。過去,我所在的中國社科院外文所就曾留下了錢楊二位先生的大量手跡。當時,每一冊圖書的封底,或內或外皆有一隻小紙袋,裏面裝着一張借書卡。每次借閱,須在卡片上籤個姓名、寫上日期。書借走,卡片留下。我初到外文所時,許多圖書的卡片上都有二位先生的簽名。而且,從年長一些的前輩、同行口中得知,錢先生一直是圖書館的義務訂購員。他爲外文所和文學所圖書館訂購的圖書不計其數,蔭庇數代學人並將繼續惠及後人。在錢楊二位先生看來,所謂學問,無非是荒江野老屋中三兩素心之人商討培養之事。而圖書館便是這個荒江野老之屋,前人通過自己的耙梳、閱讀和著述傳承經典、滋養後學、培植德性。\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楊先生還時常提到錢先生和她自己的譯得。她關於翻譯的“一僕二主”說膾炙人口,謂“一個洋主子是原文作品,原文的一句句、一字字都要求依順,不容違拗,不得敷衍了事。另一個主子就是譯本的讀者。他們既要求看到原作的本來面貌,卻又得依順他們的語文習慣。我作爲譯者,對洋主子盡責,只是爲了對本國讀者盡忠”。錢先生稱這種“一僕二主”是化境,即既要忠實原著的異化,又要忠於讀者的歸化。這自然是很不容易的,有時甚至是矛與盾的關係,但楊先生在其《堂吉訶德》《小癩子》《吉爾·布拉斯》等譯作中努力做到了。\u003C\u002Fp\u003E\u003Cimg src=\"http:\u002F\u002Fp1.pstatp.com\u002Flarge\u002Fpgc-image\u002FRXoREK7FWRWxH0\" img_width=\"640\" img_height=\"315\" alt=\"譯者||陳衆議:楊絳,永遠的女先生\" inline=\"0\"\u003E\u003Cp\u003E楊絳先生部分譯作:《堂吉訶德》\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吉爾·布拉斯》《斐多》\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要說楊先生年屆六旬開始自學西班牙語,那是何等毅力、何等勇氣。適值“文革”如火如荼,先生卻躲開睽睽衆目,利用有限的間隙偷偷譯完了《堂吉訶德》。一如錢先生所譯德國大詩人海涅的感喟,楊先生認爲《堂吉訶德》實在是一部悲劇。是啊,在強大的世風面前,堂吉訶德那瘦削的身軀是多麼羸弱,生鏽的長矛是何等無力。還有那一往無前的理想主義,簡直是不合時宜!但楊先生就是那個不合時宜的高古之人。\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此外,她翻譯的《小癩子》雖是另一種文學形態,卻一樣傳遞了先生的問學之道。下筆前先竭澤而漁,瞭解相關信息。且說《小癩子》原名《托爾美斯河上的小拉撒路生平及其禍福》,實在冗長得很。楊先生之所以翻譯成《小癩子》,是因爲《路加福音》中有個叫拉撒路的癩皮化子,而且“因爲癩子是傳說中的人物”……在此,我們不妨稍事逗留,將楊先生的考證摘錄於斯,以饗讀者:“早在歐洲 13 世紀的趣劇裏就有個瞎眼化子的領路孩子;14世紀的歐洲文獻裏,那個領路孩子有了名字,叫小拉撒路……我們這本小說裏,小癩子偷喫了主人的香腸,英國傳說裏他偷喫了主人的鵝,德國傳說裏他偷喫了主人的雞,另一個西班牙故事裏他偷喫了一塊醃肉。倫敦不列顛博物館藏有一部 14 世紀早期的手抄稿《Descretales de Gregorio IX》,上有7幅速寫,畫的是瞎子和小癩子的故事。我最近有機緣到那裏去閱覽,看到了那部羊皮紙上用紅紫藍黃赭等顏色染寫的大本子,字句的第一個字母還塗金。書頁下部邊緣有速寫的彩色畫,每頁一幅,約一寸多高,九寸來寬。全本書下緣一組組的畫裏好像都是當時流行的故事,抄寫者畫來作爲裝飾的。\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從那7幅速寫裏,可以知道故事的梗概。第一幅瞎子坐在石凳上,旁邊有樹,瞎子一手拿杖,一手端碗。小癩子拿一根長麥稈兒伸入碗裏,大約是要吸碗裏的酒,眼睛偷看着主人。畫面不大,卻很傳神。第二幅在教堂前,瞎子一手柱杖,一手揪住孩子的後領,孩子好像在轉念頭,衣袋裏裝的不知是大香腸還是麪包,看不清。第三幅也在教堂前,一個女人拿着個圓麪包,大概打算施捨給瞎子。孩子站在中間,伸手去接面包,另一手做出道謝的姿勢。第四幅裏瞎子坐在教堂前,旁邊倚杖,杖旁邊有個酒壺,壺旁有一盤東西,好像是雞。瞎子正把東西往嘴裏送,孩子在旁一手拿着不知什麼東西,像剪子,一手伸向那盤雞,兩眼機靈,表情刁猾。第五幅是瞎子揪住孩子毒打,孩子苦着臉好像在忍痛,有兩人在旁看熱鬧,一個在拍手,一個攤開兩手好像在議論。第六幅大概是第五幅的繼續。孩子一手捉住瞎子的手,一手做出解釋的姿態。左邊一個女人雙手叉腰旁觀,右邊兩個男人都伸出手好像向瞎子求情或勸解。第七幅也在教堂前,瞎子拄杖,孩子在前領路,背後有人伸手做出召喚的樣兒,大約是找瞎子幹甚事。”同時,漢語裏的癩子也並不僅指皮膚上生有癩瘡的人,而是泛指一切混混。殘唐五代時的口語就有“癩子”這個名稱,指無賴;還有古典小說像《儒林外史》和《紅樓夢》裏的潑皮無賴,也常叫作“喇子”或“辣子”,跟“癩子”是一音之轉,和拉撒路這個名字也意義相同,所以楊絳便巧妙地將書名譯作了《小癩子》。\u003C\u002Fp\u003E\u003Cimg src=\"http:\u002F\u002Fp9.pstatp.com\u002Flarge\u002Fpgc-image\u002FRXoREKNChU43Pp\" img_width=\"355\" img_height=\"380\" alt=\"譯者||陳衆議:楊絳,永遠的女先生\" inline=\"0\"\u003E\u003Cp\u003E楊絳譯《小癩子》\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近10年,先生逐漸雙耳失聰,最後必得與人筆談,還須目不轉睛地看着對方的表情和口型。我頗爲着急,多次勸先生配一副好一點的助聽器。她原是有一副助聽器的,但質量不好,戴上它嗡嗡地似有發動機在耳邊轟鳴。即使如此,每每提起新助聽器,她就一再搖頭說算了,“不必浪費,我能看書、寫字就可以了”。後來,我偶然得知有位鄰居叫張建一的,是協和醫院的耳科專家;便再次勸先生配助聽器。她依然不肯。我和張大夫都以爲她心裏裝着“好讀書獎學金”,捨不得花錢。於是,張大夫經與協和醫院領導商量,準備替楊先生免費配一副最好的助聽器,結果還是被先生婉言謝絕了。我們這才明白,她是不想浪費資源,以便多一個“更年輕、更需要的人”去擁有它。而實際上先生又何嘗不需要呢?近年來,其實總有領導和各方人士前去探望,可她卻寧可自己將就。\u003C\u002Fp\u003E\u003Cimg src=\"http:\u002F\u002Fp1.pstatp.com\u002Flarge\u002Fpgc-image\u002FRXoREbk37ShDix\" img_width=\"600\" img_height=\"449\" alt=\"譯者||陳衆議:楊絳,永遠的女先生\" inline=\"0\"\u003E\u003Cp\u003E說到“將就”,那也是應了先生的性情。她固愛清靜,但更想着不麻煩別人。因此,她最近十來年也着實謝絕過許多熱心讀者、媒體,甚至領導的造訪。這又使我想起了錢先生的逗趣:喜歡喫雞蛋,又何必非要認識下蛋的雞呢。\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如今,先生駕鶴西去,“喪事從簡,不設靈堂,不受賻儀,不留骨灰”,但她的作品早已爲她鑄就了豐碑,而她的德行便是那不朽的銘文。“不說違心的話,不做違心的事,一生只靠寫作謀生。”這便是先生對自己的寫照,而錢先生對她的讚美卻是“最賢的妻、最才的女”。作爲一位著作等身的知識分子,她的同人、晚輩則將一如既往地尊稱她爲先生。\u003C\u002Fp\u003E"'.slice(6, -6),
groupId: '67198373528747381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