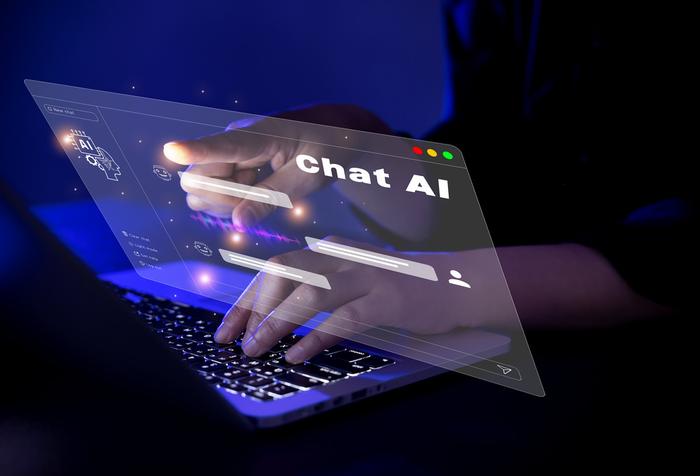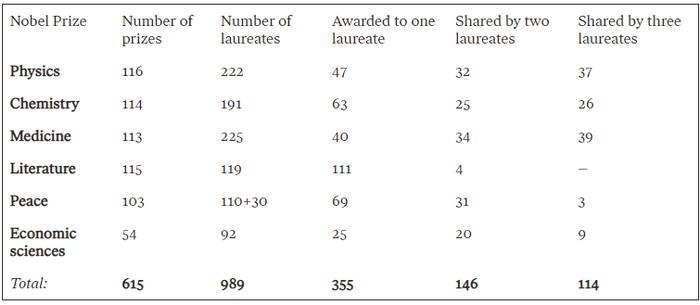“我们的脚陷进大地太深,拔不出来”
"\u003Cp\u003E“在北京和上海,你说‘我爱你’,人家会吓跑,谁都不会相信——‘你是开玩笑吧?’——但在边疆最淳朴的地区,可以直截了当说‘我爱你’,没有人怀疑。边疆地区的人还相信人类神话最重要的东西,所以他们写的东西非常简朴,直奔主题。”\u003C\u002Fp\u003E\u003Cimg src=\"http:\u002F\u002Fp1.pstatp.com\u002Flarge\u002Fpgc-image\u002FRXsQg0C8Lmlau8\" img_width=\"960\" img_height=\"640\" alt=\"“我们的脚陷进大地太深,拔不出来”\" inline=\"0\"\u003E\u003Cp\u003E2019年7月12日上午,在新开张的“十月文学馆·丽江古城”里,专家对几位青年作家的作品提出了意见。 (新华社记者 胡超\u002F图)\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2019年7月12日上午,在新开张的“十月文学馆·丽江古城”里,丽江青年诗人李凤、散文作者黄立康、诗人阿卓日古和小说家东巴夫坐在一起。他们对面是几位来自北京的客人,包括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过常宝、张柠,作家徐则臣和弋舟,以及十月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胡晓舟以及《十月》杂志副主编宗永平。\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这是一场青年创意写作营,或更直白地说——“改稿会”,专家对几位青年作家的作品提出了意见。东巴夫刚刚出版小说集《豹子的诱惑》,其余几位作家的作品散见于文学期刊。李凤说,她有些羞于让“老师”们看到自己的作品。\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h3\u003E“云南作家需要用飞扬的姿势,把书桌搬到天空中”\u003C\u002Fh3\u003E\u003Cp\u003E对于云南的文学创作,作家、《人民文学》副主编徐则臣的印象是:诗歌和小说都充满地气和野气。看到东巴夫的小说,他同样感到“元气淋漓”,但也期待东巴夫有所改变,避免审美疲劳。\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这种写作容易在某一个语境中衍生出来,有很多意象、细节,甚至故事情节在同一个语境中有点近亲繁殖的感觉。”徐则臣说。\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2011年,张柠发表论文《当代汉语文学中的“边疆神话”》,讨论中心城市的作家怎样从边疆作家那里获得营养。他写这篇论文的缘由是,大城市的市民心态、城市生活越来越复杂,叙事语言也越来越复杂,以至于阅读越来越专门化,许多读者连现实主义小说都很难读懂。他想追问:人类最纯洁、最质朴和最直接的生活方式还有没有?《诗经》那么直截了当的表达还有没有?\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读到边疆作家的小说和诗歌时,张柠突然发现,他们把大城市人不敢说的话直接说出来了。“在北京和上海,你说‘我爱你’,人家会吓跑,谁都不会相信——‘你是开玩笑吧?’——但在边疆最淳朴的地区,可以直截了当说‘我爱你’,没有人怀疑。边疆地区的人还相信人类神话最重要的东西,所以他们写的东西非常简朴,直奔主题。”张柠说。\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读到阿卓日古那种“喷发式”的地方意象堆叠的诗句,张柠不满足简单的山岗、竹叶吹响笛声等描述。在他看来,这些诗句尽管带有《诗经》式的古老诗意,但有特定条件:封闭的文明环境。诗人遗忘和现代生活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写出这样的诗句,但丰富多彩的现代生活嵌入诗人的经验,这样的诗意就不复存在。会深思现代生活复杂性的读者,目光不会局限于风景,他会反观自身。\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古典诗歌的诗意是没有疑问的,呈现在这个地方,直接把它唱出来就可以。现代诗的诗意是有疑问的,疑问当中诞生非常暧昧和复杂的东西,诗人非常重要的功能是捕捉和抓住一般人。”张柠说,“雷平阳、王单单的诗带有古老的传奇色彩、史诗色彩和英雄色彩,但文学怎么服务于今天的人、日常的生活、普通的人?这是今天文学非常重要的任务。”\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李凤的诗歌不再直接面对羊群、雪山和江水,面对的是肯定和否定之间的摇摆不定。在张柠看来,这就是一种现代感觉。\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就云南诗歌来说,雷平阳之后,王单单、刘年等人构成了一个谱系。但徐则臣认为,这些诗人越来越套路化,自我更新越来越少,成为类似民谣或旅游指南的写作。张柠打趣,旅游局会比较关注和喜欢这个种类型的写作。\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这次“改稿会”上,李凤和阿卓日古构成了两个极端,都具有样本价值。徐则臣认为阿卓日古的仪式感过强,元气有余,抽象不足;李凤则相反,更具思辨气质,但“巫气”不足。\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徐则臣提醒年轻作者们:李凤的问题是人的思想和感觉能力不会日新月异,很可能写几年就难以为继;阿卓日古的问题是不断重复,一本诗集像一首诗。“说难听一点,文学既要有上半身,也要有下半身,这样才完整,血肉和精神结合。”他评价道。\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审美疲劳之外,徐则臣也认为,另一个问题是与现代生活经验的距离比较远。\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在大地上漫游是好事,但还得走到人群里,成为现代人间的思考者,不然会觉得跟我们当代人的内心世界稍微有点远。”徐则臣发现,云南诗人和作家笔下极少出现“异化”这样更富现代感的词汇。\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面对中心城市的作家,批评家期待他们可以具有边疆作家的淳朴直接;而面对边疆作家,批评家则期待他们能够呈现更多现代生活经验。\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我们对他们复杂性的程度不满意,单这个东西我读了很舒服,日常我处理小说的时候把复杂性处理够了,闹心死了,平衡一下又有什么问题呢?”弋舟开玩笑道。\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李凤也意识到了自己的局限。“云南的文学传统拥有古老的诗意,接地气也通神灵,让云南许多诗人在全国拥有独一无二的精神气质和概念标签。遗憾的是,这又是我所缺乏的元素,”李凤告诉南方周末,她希望在今后的创作中可以加入更多“异质性”的诗意。\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h3\u003E“想象力我有,但是表达我没有”\u003C\u002Fh3\u003E\u003Cp\u003E对于东巴夫这些当地青年写作者,需要面临一个客观劣势:小说这种文学体裁在丽江乃至云南一直都很薄弱。\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弋舟认为,广西文学在中国文学的版图中就像拉美之于世界文学,广西有一批不失水准的小说家。然而,相比之下,云南很少有具备全国影响力的小说家。\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丽江这边比较出彩的还是诗歌。像彝族、纳西族,他们天生为歌谣、诗歌而生。”黄立康说。他向南方周末介绍,主要分布于云南省的普米族只有三万人,但拿过骏马奖的诗人已经有好几位。骏马奖是针对少数民族的国家级文学奖。\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而对母语并非汉语的黄立康来说,汉语表达也是问题。书写时,他需要经历转译过程。丽江大部分少数民族作者的共性与汉语表达有关,很多人的表达还处在模仿阶段,犹如写作文。\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我读莫言老师的作品,他的想象力非常磅礴,比喻句非常好。想象力我有,但是表达我没有,还是表达限制,我们第一步还是应该有好文字,大部分作者的困境可能还是这个。”黄立康说。\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黄立康提及他喜欢的北京作家周晓枫,后者把形容词称为自己的“密码”。\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而让东巴夫困惑的是:处理现实主义题材的时候,怎么可以让小说稍微“飞”起来一点?在他眼中,自己目前最大的创作困境是对素材的提炼能力和“思想力”的缺乏。\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黄立康也面对同样困境。弋舟以黄立康的短篇小说《每个人都有秘密》为例,内容涉及捡垃圾,包含窥私、情杀和悬疑等诸多元素,但小说结尾的处理降格成了花边新闻。他建议:如果最后不满足于把小说花边新闻化,那就是“思想力”,顺道滑下去就没有“思想力”。\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徐则臣发现,云南很多作家会面临一个问题:小说阐释的空间如果比较大,更多依赖于生活本身的复杂性,而不是作家抽象出来的复杂性,或者说缺乏对现实经验材料的抽象提炼,小说呈现给读者的并没有比生活更多。\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现实通过作家的整合抽象,从里面捞出了什么干货,那个东西更重要。”徐则臣说。\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学者过常宝主要从事古典文学研究,他举了一个关于“思考力”的例子:中国历史上纯粹的山水诗并不多,背后是文人的选择。尤其到晚唐时期,诗人写风景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即便稍早的李贺,写山水田园时已经有很深刻的个人观点,关于生存和死亡意义的思考,对个人情感价值和情感方式的思考已经完全不一样了。\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h3\u003E“大作都写于荒野小村,或幽暗的书房”\u003C\u002Fh3\u003E\u003Cp\u003E在北京邮电大学读硕士期间,李凤在一次笔会上和大家交流喜欢的诗人。她说喜欢云南诗人刘年,引起诗友们质疑。李凤才发现,自己的认知之外,其实还有截然不同的观点或诗歌流派。\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我们搞评论读长篇小说,对当代作家、长篇小说的美学判断来自哪里,标准不可以来自我个人,是来自于世界文学和中国文学的坐标。你不能把你的标准定在刘年和王单单。”张柠说。\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身处文学和地理意义上的双重边疆,云南等地区的写作者尽管不像大城市的年轻人,可以随时接触丰富的文化资源,但当地也有扶助青年写作者的措施。\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云南丽江当地的文学月刊《壹读》由市文联主编,全国发行,供职于文联的黄立康就是这本杂志的编辑。由于财力有限,而且主要为本地读者服务,刊物很少有外地作者。\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本地作者发外面的刊物很难,所以我们就要鼓励他们,每年给他们发一两次。作者比较多,但整体层次来说还是稍微有点低。”黄立康说。他比较认可期刊体系,而且云南省政府还出台了“一族一品”的政策,一个民族一部精品,作品足够优秀就可以申请,由政府资助出版。身在文联,他感受到政府对当地文学创作的支持力度正在加大。\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远离北京、上海和江苏等传统文学中心,在边疆写作意味着什么?东巴夫自称野生的边疆作家。他第一次见到全国闻名的作家是2016年,在《滇池》杂志的改稿会上见到马原。李凤则更晚。2018年5月,在“云南省首届人口较少民族文学创作培训班”,她见到了吉狄马加、徐则臣、石一枫和范稳等活跃在当代文坛的作家。\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十月文学馆·丽江古城”是北京出版集团旗下“十月”文学品牌在国内设立的首个文学展馆,,弋舟是首位入驻作家。未来,当地文学爱好者、作者可以有更多机会与一线作家交流。\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对于身处文学场域的中心和边缘,黄立康认为,如果写作单纯以发表为目的,相对来说就是边缘。东巴夫也没有因为远离文学中心而寂寞。“大作都写于荒野小村,或幽暗的书房。”东巴夫说。\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沈河西\u003C\u002Fp\u003E"'.slice(6, -6),
groupId: '67200906345075184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