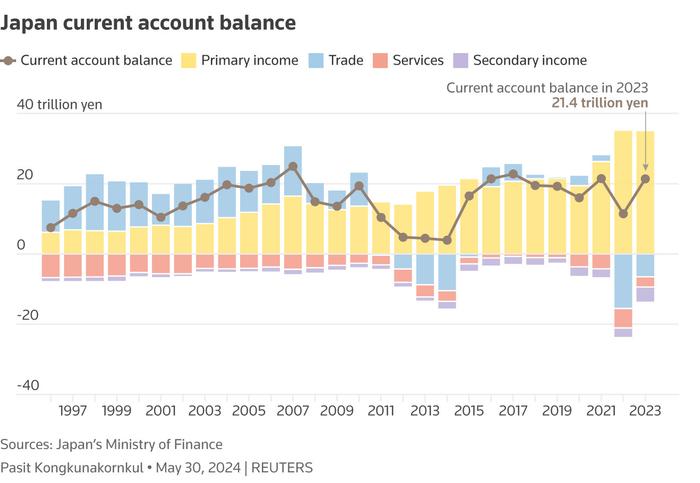隋唐制度史研究:史學綜合化趨勢下有了新突破!| 社會科學報
"\u003Cimg src=\"http:\u002F\u002Fp1.pstatp.com\u002Flarge\u002Fpgc-image\u002FRX8IV0OCTJ3hbd\" img_width=\"1080\" img_height=\"778\" alt=\"隋唐制度史研究:史學綜合化趨勢下有了新突破!| 社會科學報\" inline=\"0\"\u003E\u003Cimg src=\"http:\u002F\u002Fp1.pstatp.com\u002Flarge\u002Fpgc-image\u002FRXszSJsHn424zE\" img_width=\"410\" img_height=\"308\" alt=\"隋唐制度史研究:史學綜合化趨勢下有了新突破!| 社會科學報\" inline=\"0\"\u003E\u003Cp\u003E在中國史學界有關中國古代各個斷代的歷史研究中,隋唐史研究具有突出的重視制度史的特點。無論從新史學誕生以來的學術史看,還是從近期的學術進展看,重視制度史都是隋唐史研究與其他斷代史研究相比最爲顯著之處。在當今史學研究走向新的綜合化趨勢的背景下,\u003Cstrong\u003E隋唐制度史\u003C\u002Fstrong\u003E研究也呈現出新一輪的知識整合和議題更新。\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原文 :\u003C\u002Fstrong\u003E《史學綜合化趨勢下的隋唐制度史研究》\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作者 |\u003C\u002Fstrong\u003E中國人民大學教授 劉後濱\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圖片 |\u003C\u002Fstrong\u003E網絡\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制度史研究出現碎片化現象\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以岑仲勉和陳寅恪爲代表的新史學第一代唐史學者,對制度史就極其重視,儘管他們的學術關懷相當寬廣,研究領域涉及衆多面向,但構成其對隋唐史敘事框架的當屬制度史。岑仲勉撰有《府兵制度研究》,又在《郎官石柱題名新考訂》中收錄了除書名所揭主題外另外三種史料的考訂和校補,包括《翰林學士壁記注補》《補唐代翰林兩記》《登科記考訂補》,整理的都是有關唐代官制史研究的基本史料。在分爲上下兩冊的《隋唐史》一書中,職官制度、賦役制度、府兵制度等也是重點論述的內容。他在寫成於1950年代末的《通鑑隋唐紀比事質疑》一書中,針對司馬光敘事的錯誤加以訂正,在一條條簡短讀書札記中,揭示出許多有關唐代制度的問題關節點,體現了作者在制度史方面卓越的史識。陳寅恪除了《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專論隋唐制度特徵及其在南北朝之淵源,其《唐代政治史述論稿》的敘事展開也是建立在隋唐府兵制度、科舉制度、賦役制度、中樞體制以及其他中央地方相關制度認識基礎上的。\u003C\u002Fp\u003E\u003Cimg src=\"http:\u002F\u002Fp3.pstatp.com\u002Flarge\u002Fpgc-image\u002FRXszSK8AJm4nOD\" img_width=\"768\" img_height=\"901\" alt=\"隋唐制度史研究:史學綜合化趨勢下有了新突破!| 社會科學報\" inline=\"0\"\u003E\u003Cp\u003E其實,如侯旭東所揭示的,最早從19世紀中葉以來,在爲了尋求體制變革而帶來的史學研究中,“制度”的意義與價值凸顯,“制度”逐漸凌駕於人和事之上,獲得了更爲根本性的意義,進而從原先在史學門類中的附庸位置掙脫而出,自成門戶。到了20世紀二十年代,制度史作爲一門專史就已經大致成型(侯旭東:《“制度”如何成爲了“制度史”》,《中國社會科學評價》2019年第1期)。\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可以說,在新史學成立的初期,中國史學界最早是自覺通過制度史而建立起對中國歷史的整體敘事框架的。除了清末以來尋求體制變革的現實政治動因外,後來進入中國學術視界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也對制度史研究產生了重要影響,學者們在進行制度分析時,或隱或顯地結合了當時風行於世的馬克思主義社會史觀,將制度放置於更宏大的社會史視野之下,以剖析社會整體結構爲指歸。在這種思路的統攝下,制度製作的權力格局、政策環境與文化背景均作爲制度史的考察對象,使制度史完成了對傳統官制研究的揚棄,成爲現代史學的重要支柱。岑仲勉、陳寅恪等人即是在此背景下,通過制度史的結構性思路,建立起了對隋唐斷代史研究的整體認識。其他學者如王亞南、錢穆等人的研究,也都聚焦於制度的演進史。\u003C\u002Fp\u003E\u003Cimg src=\"http:\u002F\u002Fp3.pstatp.com\u002Flarge\u002Fpgc-image\u002FRXszSKT3b2uzwe\" img_width=\"765\" img_height=\"920\" alt=\"隋唐制度史研究:史學綜合化趨勢下有了新突破!| 社會科學報\" inline=\"0\"\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從專門化走向綜合化\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20世紀後半期以來,以汪籛遺著《汪籛隋唐史論稿》、唐長孺《魏晉南北朝隋唐史三論》、王永興《唐勾檢制研究》以及黃永年《六至九世紀中國政治史》等論著的出版爲標誌,岑仲勉和陳寅恪之後的第二代唐史學者進入學術盤點的階段,制度史依然是他們構建隋唐史整體敘事的基本框架。\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在這些學者指導和影響下,隋唐史研究的成果總量巨大,但相比於\u003Ci class=\"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 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style-3\"\u003E五六\u003C\u002Fi\u003E十年代的研究,總體來看,論題的開拓卻未有多少實質性的進展。如果要說隋唐研究中由量的積累帶來了質的突破,突出的成績在於政治制度史和敦煌學。這是中國學術界自我反思以及在國外(主要是日本)和我國港臺地區隋唐史研究成績衝擊下作出的回應,一時間政治制度史和敦煌學率先成爲隋唐史研究的熱點,且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九十年代初期(參見吳宗國《我看隋唐史研究》,《文史知識》2006年第4期)。隨着研究的深入,制度史研究出現了碎片化現象,大量的研究陷入同質性的重複,話題切分得越來越細緻,盡顯專門、深刻,而缺少整體觀照和議題更新。於是,一些中青年學者提出,要反思新史學成立以來那些核心議題提出時的理論語境,吸取大量個案研究中的有效積累,對接20世紀上半葉的學術背景,實現又一輪的知識整合,在史學綜合化的背景下更新研究議題。對於制度史的研究來說,如侯旭東所指出的,要克服後見之明,順時而觀,避免將制度架空在具體的人和事之上。\u003C\u002Fp\u003E\u003Cimg src=\"http:\u002F\u002Fp1.pstatp.com\u002Flarge\u002Fpgc-image\u002FRXszSKr3ckXmBZ\" img_width=\"665\" img_height=\"516\" alt=\"隋唐制度史研究:史學綜合化趨勢下有了新突破!| 社會科學報\" inline=\"0\"\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整合性研究得到拓展和延伸\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人類社會原本是以整體的面貌展開和推進的,碎片化的描述或是出於學科劃分的研究需要,或是限於史料留存的不完整,更多是由於帶着所處現實的有色眼鏡剪裁史料所導致的。回到歷史現場,是史學從專門化走向綜合化的一個重要路徑,對接的是年鑑學派倡導的整體史研究取向。自從20世紀二十年代法國年鑑學派倡導史學研究要注重多面向和長時段以來,整體史研究就日漸成爲西方史學追求的目標。整體史敘事要求的多面向,是一項隨着人類認識水平提高而無限擴展的要求,在不同時代有其特定的針對性。而長時段到底取多長,則取決於問題的設定和掌握材料的多少。\u003C\u002Fp\u003E\u003Cimg src=\"http:\u002F\u002Fp3.pstatp.com\u002Flarge\u002Fpgc-image\u002FRXszSddH3vmaLZ\" img_width=\"465\" img_height=\"542\" alt=\"隋唐制度史研究:史學綜合化趨勢下有了新突破!| 社會科學報\" inline=\"0\"\u003E\u003Cp\u003E其實,整體史敘事原本是歷史學的基本追求,中國古代史學很早以來就追求“通古今之變”。自從20世紀初中國學術界引進新史學的研究理路以來,打破王朝體系和君道政體歷史觀的“破”的一面建樹顯著,從社會史、經濟史和文化史等角度重建歷史敘事框架的“立”的努力也頗有成效,還出現過以五種社會形態來敘述中國歷史的宏大框架。但是迄今爲止,應該只有從制度尤其是政治制度切入的整體史敘事及其依託的一套話語或概念系統無可替代,並顯示出強大的學術生命力。並不是說依託制度史研究的整體史敘事就臻於完善了,只是就已有研究積累來說,這樣角度的歷史敘事更加切近中國歷史的實際,更加契合中國歷史的編撰傳統和史料特點,呈現出了極其廣闊和深厚的研究空間。\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其他衆多研究視角取得的成績,都爲一個特定時段的整體敘事貢獻着知識和觀念,各個角度對中國歷史研究的擴展和深入,都以其繁富的成果豐富着人們的認識。但具有宏觀視野和長時段關懷的歷史敘事,似乎都難以擺脫制度史研究搭建的框架和提出的概念。各種專門史和專題研究對歷史研究的細化與深化,對於走出模式化的歷史敘事有很大貢獻,但一旦回到整體史敘事,制度史研究的骨架作用仍然無可替代。\u003C\u002Fp\u003E\u003Cimg src=\"http:\u002F\u002Fp1.pstatp.com\u002Flarge\u002Fpgc-image\u002FRXszSdxCGZeMFl\" img_width=\"444\" img_height=\"293\" alt=\"隋唐制度史研究:史學綜合化趨勢下有了新突破!| 社會科學報\" inline=\"0\"\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議題的促生與多維解讀\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推動當今史學研究走向綜合化趨勢的主力,是區域社會史和財政經濟史,尤其是有關明清時期的相關研究。儘管明清時期的史料留存自有其特殊性,但由此推動的史學研究走向整體史敘事的趨勢,對於隋唐制度史研究來說無疑也具有重要的借鑑意義,促使隋唐制度史研究朝着整合既有知識和史料、打通唐五代和兩宋歷史脈絡的方向努力拓展,回到一些基本議題的多維立體解讀上。區域社會史所追求的歷史的鮮活與豐滿,克服殘缺的、碎片化的和僵死的歷史,也是隋唐制度史研究追求的重要目標。\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在這個目標下促生的重要議題,就是政務運行機制與國家權力結構,以及在此框架下的衆多具體問題。中古國家政務的重心涵蓋在尚書六部職掌之內,尤以官員選任、賦役徵派和司法審斷最爲關鍵。要理解隋唐時期國家的政務運行機制,勢必要深入分析從中央到地方和基層鄉里各個層級的政務運行,要以事任爲中心,而不是以職官和機構爲中心。\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可以說,區域社會史和財政經濟史推動的新一輪整體史敘事趨勢,對隋唐制度史研究議題的牽動相當明顯。例如,以“政務運行”爲中心的隋唐制度史研究思路,就是力圖將傳統的以職官爲中心的政治制度史研究轉向以事類(政務)爲中心的綜合性制度史研究,或者說努力使制度史成爲一種視角,用以分析國家與社會各個層面的具體運行及其變化。這種視角的研究,在回到歷史現場和整體史敘事兩方面都有積極的意義。\u003C\u002Fp\u003E\u003Cimg src=\"http:\u002F\u002Fp1.pstatp.com\u002Flarge\u002Fpgc-image\u002FRXszSeG7iYFEvM\" img_width=\"748\" img_height=\"1080\" alt=\"隋唐制度史研究:史學綜合化趨勢下有了新突破!| 社會科學報\" inline=\"0\"\u003E\u003Cp\u003E明清區域社會史和財政經濟史的研究進展,啓發我們認識到,隋唐時期國家行政體系在制度形式上有着整齊劃一的設計,真實的國家構造和實際運作中的體制機制,應該是大量吸收了產生於複雜社會運行中的各種要素。儘管隋唐制度史研究無法像明清史那樣擁有豐富具體的傳世史料和田野材料,相類似問題的研究還只能停留在主體通過編撰史料加以拼合和分析的層面,但受其啓發而整合的議題無疑得到了拓展和延伸。例如,近年來有關隋唐五代時期包括州縣官府在內的基層政務運行機制研究、官員選任遷轉制度及俸祿體系研究、官人身份及其擴大化問題研究、藩鎮體制與唐宋間官僚身份體系變化研究等,都取得了重要進展。在此基礎上,更進一步的整合性研究開始被嘗試,有關隋唐國家構造的特質、路徑及其與宋代國家的區別這樣全局性的問題,逐漸成爲隋唐制度史研究的邏輯起點。曾經一度受到以\u003Ci class=\"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 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style-1\"\u003E關注\u003C\u002Fi\u003E地方和社會基礎爲核心任務的“新社會史”的衝擊而略顯沉寂的“國家”議題,在中國中古史研究中重新受到重視。\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綜括言之,統合過去一個世紀的個案研究成果,隋唐制度史不但能呈現新的解釋系統,擺脫新知識與舊框架間方枘圓鑿的怪現象,更重要的是,通過重述制度史,可以將各類專門史綜合成爲整體史,而這也是20世紀下半期史學方法革新過程中 “新政治史”、“新文化史”和區域社會史的旨趣所在。\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文章原載於社會科學報第\u003Ci class=\"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 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style-6\"\u003E166\u003C\u002Fi\u003E7期第5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u003E社會科學報\u003C\u002Fp\u003E\u003Cp class=\"\"\u003E做優質的思想產品\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i class=\"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 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style-2\"\u003Ewww\u003C\u002Fi\u003E.shekebao\u003Ci class=\"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 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style-6\"\u003E.com\u003C\u002Fi\u003E.cn\u003C\u002Fp\u003E"'.slice(6, -6),
groupId: '672012624102372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