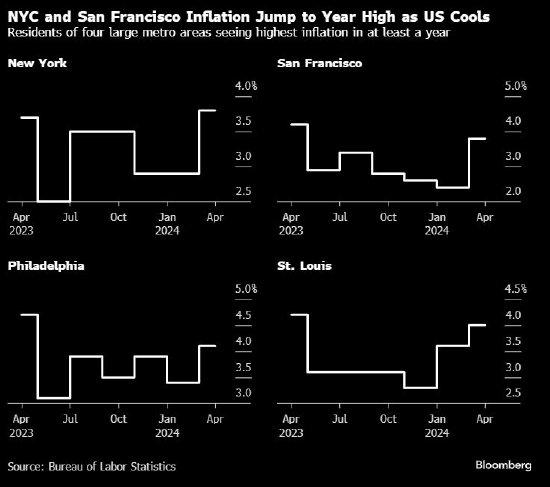詹姆斯·鮑德溫:20 世紀美國文壇無可取代的良心|單讀
"\u003Cimg src=\"http:\u002F\u002Fp1.pstatp.com\u002Flarge\u002Fpgc-image\u002FR6NJAB8BlPKmwJ\" img_width=\"605\" img_height=\"241\" alt=\"詹姆斯·鮑德溫:20 世紀美國文壇無可取代的良心|單讀\" inline=\"0\"\u003E\u003Cp\u003E今天下午,單向空間·大悅城店將舉辦《下一次將是烈火》中文版新書發佈會,單讀主編、本書譯者吳琦會與翻譯家王家湘教授、九久讀書人高級編輯索馬里一起聊一聊黑人作家詹姆斯·鮑德溫。\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作爲馬丁·路德·金最重要的夥伴和同行者之一,美國作家詹姆斯·鮑德溫是 20 世紀美國文壇無可取代的良心,他想要通過直面生命的困境,激起時代情緒,吟唱回應痛切現實的布魯斯。其作品《下一次將是烈火》出版 56 年後,依然是批判美國種族主義影響最大的文本之一。\u003C\u002Fp\u003E\u003Cimg src=\"http:\u002F\u002Fp9.pstatp.com\u002Flarge\u002Fpgc-image\u002FRY36J7nIu7Nc2T\" img_width=\"474\" img_height=\"316\" alt=\"詹姆斯·鮑德溫:20 世紀美國文壇無可取代的良心|單讀\" inline=\"0\"\u003E\u003Cp\u003E詹姆斯·鮑德溫(James Baldwin,1924 - \u003Ci class=\"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 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style-4\"\u003E198\u003C\u002Fi\u003E7),美國黑人作家、散文家、戲劇家和社會評論家。\u003C\u002Fp\u003E\u003Cimg src=\"http:\u002F\u002Fp3.pstatp.com\u002Flarge\u002Fpgc-image\u002FRY36J884TaMWqV\" img_width=\"1080\" img_height=\"1739\" alt=\"詹姆斯·鮑德溫:20 世紀美國文壇無可取代的良心|單讀\" inline=\"0\"\u003E\u003Cp\u003E《下一次將是烈火》\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美]詹姆斯·鮑德溫 著\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吳琦 譯\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人民文學出版社 出版\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點擊上圖即可購買譯者簽名書)\u003C\u002Fp\u003E\u003Cimg src=\"http:\u002F\u002Fp1.pstatp.com\u002Flarge\u002Fpgc-image\u002FR8kCdDy40U5YA\" img_width=\"605\" img_height=\"52\" alt=\"詹姆斯·鮑德溫:20 世紀美國文壇無可取代的良心|單讀\" inline=\"0\"\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吉米的布魯斯 \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撰文:Clifford Thompson\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翻譯:索馬里\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960 年代前半葉,在他的第一本書出版十多年後,快要步入 40 歲的小說家、散文家、劇作家詹姆斯·鮑德溫——去世於 30 年前,終年 63 歲——開始自比一個布魯斯歌手。他藉此表明自己的藝術前輩並非詹姆斯·喬伊斯那樣的作家——喬伊斯毋庸置疑地影響了他的風格——而是諸如貝西·史密斯(Bessie Smith) 這類歌手。當然,我們不能按照字面意思理解他的這句話,鮑德溫在現實中並沒有成爲布魯斯歌手。在《十字架之下》這篇中,他表明自己“沒有音樂天賦”,在另一篇《布魯斯的用途》中他也說自己“對音樂一無所知”。他之所以如此表態,是想表明,寫作和成爲布魯斯歌手,對他而言是服務於同一種目的。\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人們對於布魯斯音樂有一種普遍的看法,即這種悲傷的音樂是屬於潦倒不堪的底層人,這也加深了那種無意識的看法,即那些布魯斯歌手,不管是在現實層面還是在隱喻層面,都屬於那種社會等級——衣食無虞幸運如我們,永遠都不會想加入的那種階級。但事實是,布魯斯音樂是對每個人無處可逃的生活境況的一種證詞,我們生活的本質就包含了痛苦。布魯斯音樂並不是那些因過於愚鈍或倒黴而陷入不必要爭鬥的人的哭喊,而是對我們或早或晚都要面對的人類真相的一種回應。更進一步說,布魯斯事實上根本不是“痛哭”。“痛哭”這個詞已經包含了一種暗示,即一個人完全被情緒裹挾以致失控,而藝術的首要需求也許就是藝術能夠完全掌控特定的媒介——無論那工具是畫筆、小號、嗓音或者文字。那麼,作爲一種藝術形式的布魯斯,是對人類境況的剋制、冷靜和深刻的回應,一種通過直面困境來超越困境的過程。它是文化評論家 Albert Murray 所說的“誕生於困厄中的屬於黃金時代的音樂” 。\u003C\u002Fp\u003E\u003Cimg src=\"http:\u002F\u002Fp3.pstatp.com\u002Flarge\u002Fpgc-image\u002FRY36J8P3EY1tvs\" img_width=\"1080\" img_height=\"576\" alt=\"詹姆斯·鮑德溫:20 世紀美國文壇無可取代的良心|單讀\" inline=\"0\"\u003E\u003Cp\u003E當一個作家說自己是布魯斯歌手時到底代表什麼?鮑德溫這麼表達似乎至少包含了兩層意思。第一,不僅是爲人們的生活作見證,更是爲美國黑人所面臨的極端特殊、無法忍受的境況作見證, 而美國黑人的這種可怖境況,同樣的 ,給予再多的\u003Ci class=\"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 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style-2\"\u003E關注\u003C\u002Fi\u003E都無法將他們從中解放出來——簡單來說,就是種族主義。但在某種程度上,這一任務與直面生活真相的任務密不可分。鮑德溫的觀點是,很多美國白人在努力追求一種崇高的狀態,爲的是能夠戰勝,或者至少讓自己逃避面對我們所有人都要直面的現實——最終的死亡。這就讓尊崇某人變得必要。這是一種自我永存的循環:白人越覺得需要逃避現實,他們就要付出越多的努力讓黑人安守本分,而他們的這種手段越是殘暴,白人們的罪惡感就愈發深重;他們的罪感越是強烈,他們逃避現實的需求就更加強烈,而這一切正是邪惡的根源。藉着將自己定義成一個布魯斯歌手,鮑德溫想傳達的意思是,和所有的布魯斯歌手一樣,他追求直面事實,並且希望他的同胞,無論其膚色爲何,都能如此。 \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但鮑德溫的這句話還有別的意思,也就是開始嘗試將布魯斯音樂——涵蓋了整體意義上的美國黑人音樂,包含爵士樂——的感受力、韻律和強節奏(beat),帶入書寫語言中。他曾經寫過,長期以來自己用現存的英語語言去模仿那些偉大的白人作家的風格,但是現在希望能爲自己的目的重新創造這種語言,不爲了模仿任何事物,而是通過布魯斯的音符去分享自身的經歷。此處反諷的一點在於,鮑德溫像一個布魯斯歌手一般寫作是否成功這一點,我們只能說有待商榷,而他另外的目的則是他長久以來已經實現的某種成就:面對自身和他的同胞們的現實和苦痛,在這一點上他是成功的。\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鮑德溫自身的痛苦和憂鬱,有很多現實根源。他於 1954 年 8 月 2 日出生於哈萊姆某個社區的一家醫院,那個街區將會決定他的一生。他是一個私生子,他的母親,愛瑪 ·貝爾迪·瓊斯生他的時候還不到 20 歲,這個未來最偉大的美國黑人作家的男孩只有在很短的一段時間裏擁有“詹姆斯·瓊斯”這個名字。1927 年,愛瑪·瓊斯嫁給了大衛·鮑德溫,一個從南方移居到紐約、已經上了年紀的男人,他可能出生於 \u003Ci class=\"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 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style-3\"\u003E186\u003C\u002Fi\u003E3 年內戰爆發之前。他的繼子詹姆斯·瓊斯就變成了詹姆斯·亞瑟·鮑德溫。要等到詹姆斯十幾歲時,他母親才告訴他大衛並不是他的親身父親,但她從未告訴他他的生父是誰。這個事實令他沮喪不已。\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在他快 50 歲時,鮑德溫曾告訴一個記者自己“從未擁有童年”,這句話的一層意思就是,他要忙於照顧家裏的其他孩子,自己無法當一個孩子。鮑德溫一家最後一共有 9 個孩子。大衛·鮑德溫在一家工廠工作,薪資微薄,一家人生活幾近赤貧,連飯都喫不飽。幾乎都無法讓一家人勉強餬口,亦無力反抗當時的種族主義和種族隔離政策,更無法掌控自己的生活,大衛·鮑德溫因此成了一個滿腹怨恨的人,憎恨白人,對家人也冷漠避之。(他的妻子稱他爲“鮑德溫先生”)。他經常毆打自己的孩子,而當他偶爾想要親近家人的嘗試也悲劇告終:正如鮑德溫在《土生子札記》(\u003Cem\u003ENotes of a Native Son\u003C\u002Fem\u003E)一書中所寫的,當他父親將他的某個孩子抱上膝頭與其嬉鬧時,孩子往往會被嚇怕、放聲大哭;當他試着輔導我們的功課時,他周身釋放出的那種極度強烈的\u003Ci class=\"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 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style-2\"\u003E緊張\u003C\u002Fi\u003E感讓我們的頭腦和舌頭開始發憷,而他自己根本不明白原因爲何,便會惱怒不已,而某個不明就裏的孩子就會遭到懲罰……我不記得那些年裏他的哪個孩子看到他回家時是興高采烈的。\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諷刺的是,這樣一個陰鬱的男人的生活目標卻是成爲一名牧師,照亮他人,雖然並不成功,他“從一些大一點的教堂換到那些更小的,更加怪異的教堂”,並且發現自己“逐漸不被人需要”——用詹姆斯的話形容。\u003C\u002Fp\u003E\u003Cimg src=\"http:\u002F\u002Fp1.pstatp.com\u002Flarge\u002Fpgc-image\u002FRY36J8eF0Xcn7O\" img_width=\"1080\" img_height=\"576\" alt=\"詹姆斯·鮑德溫:20 世紀美國文壇無可取代的良心|單讀\" inline=\"0\"\u003E\u003Cp\u003E當詹姆斯·鮑德溫將自己的認知從他不幸的家庭轉向他所在的街區時,他看到等待自己和同齡人的會是什麼。“比如,犯罪變得真實——第一次,它不再只是一種可能,而幾乎成爲真真切切的可能性,”他在《十字架之下》(《下一次將是烈火》的第一篇)中寫道,“一個人絕不可能通過工作和儲蓄來戰勝所處的環境;一個人也絕不可能通過工作獲得足夠的財富;此外,在社會待遇上,即便是最成功的黑人,如果要獲得自由,僅有一個銀行賬戶也是不足夠的。”鮑德溫補充道,每個到了他那個份兒上的男孩子都能迅速、徹底地意識到,因爲他要活下去,因此他就讓自己陷入了巨大的危險,他必須很快找到“某樣東西”,某種祕密把戲,讓自己振作起來。是什麼祕密把戲其實無關緊要。最後這一點讓我深感恐懼——因爲它展示出太多門外的危險——將我拋向教堂。\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4 歲時,鮑德溫成了一名少年牧師。因爲他對佈道的天賦,又因爲他的年輕是一種吸引力,結果他比他父親更受教堂會衆歡迎,這是鮑德溫擊敗的第一個父親的形象,但並非最後一個。\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詹姆斯·鮑德溫的諸多天賦之一,就是直面和應對現實的能力。在他擔任少年牧師的那三年裏,他逐漸意識到,作爲一種機構的教會的基礎不是愛,而是恐懼、自衛和排斥,這麼做是爲了一個必定比此生要好的來世做準備,這麼做的時候對個人小\u003Ci class=\"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 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style-1\"\u003E圈子\u003C\u002Fi\u003E之外的任何人的命運都漠不關心。鮑德溫在這個時候顯示出自己是一個極度陽光的男孩,他也被顯赫的德懷特·克林頓公立高中錄取,他的很多同學都是猶太人,而他也覺得去相信他的朋友們因爲自己的出生就要遭受永恆的詛咒這一點很虛假,而且很邪惡。他同樣看到,自己所處的那個教堂總體上對白人,不管是基督徒還是其他人都毫無愛心,也毫無用處。鮑德溫本可以在教堂裏享受某種特權的舒適地位,他也喜歡教堂的音樂,而《聖經》的文本也激發了他的寫作熱情和韻律,但他知道,爲了對自己、對自己的信仰保持誠實,他必須離開教堂。他預感到自己會成爲一個作家,而不是一個傳道者, 或者用他經常說的那句,“他離開佈道壇是爲了傳播福音。”\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在面對其他事物時——包括他自己的性向,以及在一個充斥着種族仇恨的社會里等待他的未來會是什麼樣子——鮑德溫亦帶有同樣的坦誠。他在青年時代也和女人約會過,但後來亦建立了和同性的關係,他似乎從來沒有試圖掩蓋這一點——“我愛過一些男人,我愛些一些女人”,是他對此的表態。但事實上更難適應的一點,是他發現他幾乎在一點上是對的,即鮑德溫在《土生子札記》一書中所謂的“白人的分量”。二戰期間,快 20 歲的鮑德溫離家,在新澤西的國防工廠找到一份工作,他也寫到,當他在只接待白人顧客的餐館和其他場所受到諸般羞辱時,他一開始是難以置信的。他生動地描述了那些經歷在他心中喚起的痛苦和憤怒,尤其是某個晚上,當他第 N 次被一個餐館拒絕——“我們不接待黑人”時,他情緒失控的情形。那讓他身處險境,差點喪命。之後鮑德溫意識到,用他的話說,他的生活,他真正的生活,處於危險之中,“不是由於別人會做什麼,而是由於我自己心中懷有的仇恨”。而正是這種認識,讓他在不會法語、身無分文的情況下,遠遁巴黎。\u003C\u002Fp\u003E\u003Cimg src=\"http:\u002F\u002Fp3.pstatp.com\u002Flarge\u002Fpgc-image\u002FRY36J8s74jAJ11\" img_width=\"1080\" img_height=\"576\" alt=\"詹姆斯·鮑德溫:20 世紀美國文壇無可取代的良心|單讀\" inline=\"0\"\u003E\u003Cp\u003E1948 年 11 月,當他離開美國時,鮑德溫已經開始爲一些文學雜誌,比如《評論》撰稿,這些文章讓他在小說處女作出版前就已經享有一定的聲譽,但這些短小的文章並沒有改善他的經濟狀況。在巴黎,他發現自己面臨的經濟困窘和他在美國經歷過的捉襟見肘不相上下,但隨着他的前兩部小說出版,他個人的經濟狀況立刻大爲改善後,他發現了一種更難擺脫的東西:儘管歐洲在某種程度上是讓他能夠遠離美國諸多邪惡的庇護所,但在本質上,他還是一個美國人。那些和身在海外的他錯過的美國民權運動的新聞,讓他深刻意識到了這一點。在他的故土,他無法真正自由地生活,但在歐洲,他很難擺脫這樣的感覺,即自己只是躲起來,而沒有出現在他應該出現的地方。\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我們因此可以看到鮑德溫憂鬱的原因:做一個沒有祖國的人;在一個同性戀不僅被普遍詆譭,更會被法律懲罰的年代,做一個同性戀者;在他的祖國作爲一個被蔑視的局外人,少數派當中的少數派。這些就是他在短篇小說、散文和小說中吟唱的布魯斯,而與我們之前對布魯斯的定義相吻合,他的寫作是剋制、超然而智慧的,這讓他能洞悉自身問題的真正面目,並且試圖超越它們。他也試圖爲他的祖國付出同樣的努力。\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布魯斯音樂的一個核心事實,儘管它是美國黑人的創作,但它同樣也是多種文化雜交的產物;它糅合了歐洲的曲風和黑人的聲樂風格、情感、韻律,以及賦予這種音樂獨特聲韻的五級音或七級音降音的壓音音符(或“布魯斯音符”)的存在。從他寫作生涯伊始,鮑德溫就是一個文學意義上的布魯斯歌手——他的作品將他自小就浸淫其中的歐洲文學大師們在形式上的掌控力,和黑人教堂布道的韻律、復奏和激昂糅合在一起。讓我們來看一看鮑德溫處女作小說《向蒼天呼籲》(\u003Cem\u003EGo Tell It on the Mountain\u003C\u002Fem\u003E)中的第一段——這本小說出版於1953年,當時他在法國——小說描述了哈萊姆區格蘭姆斯一家人的遭遇,這家人的境況和鮑德溫一家有很多相似之處,小說第一頁就描述了這個家庭在週日的生活場景:\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em\u003E他們那天會一起起牀,他父親當天不用去工作,就會帶領大家完成早餐前的飯禱;他母親那天一般會精心打扮一下,看起來幾乎是非常年輕了,頭髮被拉直了,頭上戴着幾乎是那些神聖的婦女固定裝束的合身的白帽子;他的弟弟羅伊那天從早到晚都會沉默寡言,因爲他父親待在家裏。\u003C\u002Fem\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這一段落是一個完整的句子,有三個分號和八個逗號, 行文之流暢應該會讓鮑德溫崇敬的亨利·詹姆斯也會引以爲豪,這也是鮑德溫標誌的風格。同時,我們注意到“那天”這個詞的重複,從信息提供的角度,這個詞的重複不是完全必要的,但會讓人聯想起教堂唱詩的節奏;一個人甚至可以想象剛剛這段話是出自一位牧師之口,每一個“那天”都賦予詞語某種難以言說的含義,每一次重複,都會讓聽衆去思考這個詞語的另外的含義。\u003C\u002Fp\u003E\u003Cimg src=\"http:\u002F\u002Fp1.pstatp.com\u002Flarge\u002Fpgc-image\u002FRY36JXA4jOXfzK\" img_width=\"1080\" img_height=\"584\" alt=\"詹姆斯·鮑德溫:20 世紀美國文壇無可取代的良心|單讀\" inline=\"0\"\u003E\u003Cp\u003E如前文所述,鮑德溫鼓勵每個人去直面自己的生活,吟唱屬於自己的布魯斯,這種音樂不是和他人的衝突,而是和自己的對峙。他的小說和散文中諸多最重要的段落都在記錄這種對峙,或者對峙可悲的缺席。《向蒼天呼籲》中的主人公約翰·格蘭姆斯,他的經歷很大程度上來自鮑德溫一家的真實生活,在教堂皈依上帝時遭遇了劇烈的自我衝突,彼時上帝和撒旦在爭奪他的靈魂,而其他的會衆大聲高呼“拯救他”時,他感覺自己虛弱無力。小說結尾處的一段話同時抓住了這種“衝突”的內核,以及鮑德溫標誌性的“布魯斯”般的文學雜交風格。這段有三個句子:第三個句子一共有 9 個短句(這一段則一共有 11 個句子),而且爲實現某種效果進行詞語的重複,\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em\u003E有什麼東西進入了約翰的身體,那身體已經不是他的。他已經被侵入,被踐踏,被迷了心竅。這個力量擊中了約翰的大腦,或者他的心靈;在一瞬間,讓他被此生未曾想象的某種痛苦所填滿,這種痛苦當然也是他不可忍受的,即便在此刻他也無法相信,這種痛苦剖開了他的身體,就像斧子劈開木材,石頭從中間裂開。它在一瞬間撕扯他,將他擊倒在地,以至於他感受不到自己的傷口,只有那種痛楚,他感受不到自己的跌倒,只有那種恐懼,就這樣,躺在這裏,在黑暗的最底層,無望地尖叫。\u003C\u002Fem\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儘管《向蒼天呼籲》中的約翰·格蘭姆斯爲了守住自己的靈魂經歷了一番自我對抗,而鮑德溫的第二本小說《喬萬尼的房間》中的主人公大衛則努力逃避這種和自我的對抗,結果卻是他自身靈魂的死滅,以及他的同性情人(書名角色)的喪命。在一個出版商們因爲害怕招致官司謹小慎微不敢出版涉及同性戀主題的小說的年代,確有一些作家是同性戀,但只有極少的作家以同性戀爲自己的題材。鮑德溫卻在 1956 年出版的《喬萬尼的房間》中大膽刻畫同性之愛,當時他身在海外(他身上更激進的一點是,他並沒有延續讓他收穫成功的處女作的套路,繼續寫一本以黑人爲主人公的小說,恰恰相反,在他的第二本小說裏,沒有一個角色是黑人)。大衛是一個已經訂婚、即將完婚的白人,去到了巴黎,愛上了喬萬尼。當大衛的未婚妻也來到巴黎時,大衛立刻疏遠了喬萬尼;萬念俱灰的喬萬尼淪落成男妓,並捲入了一場謀殺,他也因此被判了絞刑。同時,大衛只能在私下裏釋放自己密不告人的對同性的情慾,表面上在冠冕堂皇地維持着主流生活。但這本小說的最後一段,卻暗示了逃脫自我的不可能性。喬萬尼收到一封房間,信上告知他喬萬尼已經被行刑,鮑德溫寫道:\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em\u003E我拿到雅各寄給我的那隻藍色的信封,慢慢將它撕得粉碎,任它們四散風中,不知所蹤。我轉身朝等我的人走去,那陣風將一些碎片又吹回我身邊。\u003C\u002Fem\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大衛沒能唱出自己的布魯斯,其下場也是悲劇性的。\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在他的兩本小說之間,1955 年,鮑德溫出版了第一本散文集《土生子札記》,同名文章是關於鮑德溫父子關係的一首極度坦誠、毫不傷感的布魯斯。他是在思考美國的種族問題時才意識到自己和父親的關係的,而他父親的一生也讓鮑德溫明白了一個道理——用鮑德溫的話說——“逃避是不可能的”。這也是《喬萬尼的房間》結局背後的真相,而這一具有生命力的觀點,盤亙在鮑德溫最傑出的作品當中。我們無法逃避任何事物,但我們可以超越他們,只要我們願意挑戰自己,讓自己直面現實。鮑德溫知道這必定是一項艱鉅的任務——他的作品中也許沒有一個詞會像“可怕的”(terrifying)這個詞一樣高頻率地出現——但是他深知這是一項必然的任務。對鮑德溫來說,這項任務的第二部分,即在自己的寫作中貫徹這一真理。他在爲第二本散文集《沒有人知道我的名字》(\u003Cem\u003ENobody Knows My Name\u003C\u002Fem\u003E,1961)一書所寫的導讀中寫道,“自我欺騙,不管是服務於多麼渺小或者多麼崇高的目標,都是沒有一個作家能承擔得起的巨大代價。(作家的)主題就是他自己,就是世界,這需要他調動每一寸氣力去努力地真實地打量自己、打量世界。”\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本文系節選 \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首發於洛杉磯書評(Los Angeles Review of Books)\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https:\u002F\u002Flareviewofbooks.org\u002Farticle\u002Fjimmys-blues\u002F\u003C\u002Fp\u003E\u003Cimg src=\"http:\u002F\u002Fp9.pstatp.com\u002Flarge\u002Fpgc-image\u002FRY36JXUGAcMEcy\" img_width=\"1080\" img_height=\"1920\" alt=\"詹姆斯·鮑德溫:20 世紀美國文壇無可取代的良心|單讀\" inline=\"0\"\u003E\u003Cp\u003E地點:單向空間 · 大悅城店\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地址:北京市朝陽區朝陽北路 101 號朝陽大悅城 5F)\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主辦方:單向空間、上海九久讀書人、\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人民文學出版社\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歡迎已經報名的讀者前來參與活動!\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img src=\"http:\u002F\u002Fp1.pstatp.com\u002Flarge\u002Fpgc-image\u002FR6QCrAC1ks0E05\" img_width=\"605\" img_height=\"160\" alt=\"詹姆斯·鮑德溫:20 世紀美國文壇無可取代的良心|單讀\" inline=\"0\"\u003E\u003Cp\u003E編輯丨十三\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圖片來自紀錄片《我不是你的黑鬼》\u003C\u002Fp\u003E\u003Cimg src=\"http:\u002F\u002Fp1.pstatp.com\u002Flarge\u002Fpgc-image\u002FR6kShw0ANP6eQx\" img_width=\"500\" img_height=\"369\" alt=\"詹姆斯·鮑德溫:20 世紀美國文壇無可取代的良心|單讀\" inline=\"0\"\u003E\u003Cp\u003E\u003C\u002Fp\u003E"'.slice(6, -6),
groupId: '67207678909847966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