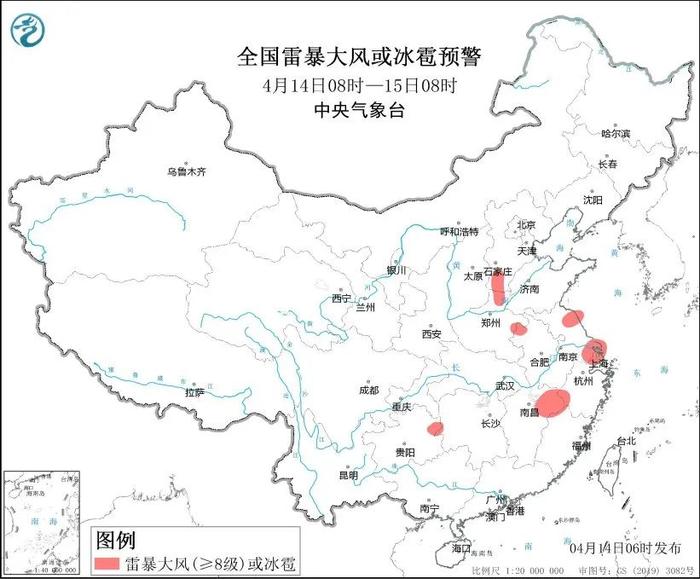《地久天長》“這不是電影,這是生活。”
“這不是電影,這是生活。”
《地久天長》正值公映,在接受多家媒體採訪時,王小帥反覆強調這一句話。
他本應無需強調這一點,畢竟,王小帥是中國第六代導演的代表人物之一。作爲中國導演代際體系中的一環,賈樟柯、婁燁、王小帥等第六代導演,從90年代起,就開始以底層人物的生存狀態和紀實性的手法,被觀衆所熟知。
他們的影片理所應當有一些無法磨滅的痕跡。第六代導演試圖呈現中國人當下的生活狀態,在影片中投射他們自身的生命體驗,以碎片的形式來展示一座城市,不是城市流光溢彩的那一面,而是服務者、無業者、落魄者看到的另一面。
《小武》
從90年代至今,三十年的時間逝去了。第六代導演展示的人羣發生了變化,城市發生了變化,連第六代導演自己也早已甩脫“邊緣”的身份,在從邊緣至主流,從反抗第五代到獨樹一幟。在被新銳導演們學習,成爲突破對象的過程中,第六代導演自己也在發生着變化。
“城市”是第六代導演創作的源泉。在第五代的鄉土民族寓言,已經成爲過去和中國電影史的經典後,第六代在90年代,選擇城市作爲自己的創作根源,本着“我的攝影機不撒謊”的創作理念,對當下的中國故事予以記錄。
因此,蘇州河成爲了一個電影在現實生活中的地標,《日照重慶》記錄了一代人記憶中的重慶。在賈樟柯的鏡頭裏,觀衆得以發覺90年代的山西汾陽,究竟是什麼樣子。
《蘇州河》
但時代在變化,第六代導演的拍攝對象,在30年間,已經變得面目全非。王小帥在拍攝《地久天長》時就遇到了困難:拍攝需要的廢磚房,已經很難找了。
如果有時光機,90年代的第六代導演或許很難接受這種現實:內蒙古自治區成立70週年,原本的老房子被刷上了粉色的新漆,《地久天長》裏試圖呈現的“現實”,在真正的現實中已經不存在了。
現代的城市如今發展的面貌,已經和第六代導演們習慣展示的樣子相差太遠。城市的樣子在改變,鏡頭裏的城市質感也在改變,能直接呈現在鏡頭裏的“真實”,距離導演們心中的真實也很遠。第六代導演眼中所看到的城市,已經不再是“當下”,而是“過去”,是還原和追溯。
如今,城市也不再由一羣人書寫。所有的城市大都日新月異,新銳導演們或者選擇再次迴歸鄉村,比如畢贛在《路邊野餐》中選擇的凱里,比如周子陽在《老獸》裏選擇的鄂爾多斯。或者選擇在影片裏抹去城市的痕跡。
《路邊野餐》
反正所有的現代都市,大多像是從同一個模子里扣出來的。故事發生在哪裏已經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哪裏都有可能發生這樣的故事。
婁燁在《蘇州河》的首映式上曾說“長的段落,纔可能有真實,纔能有所觸動。”長鏡頭也成爲第六代導演慣用的拍攝手法。
這一點特徵,還停留在第六代導演的作品中,也被更多的年輕導演所繼承。無論是《地久天長》中王景春和詠梅聊天的長鏡頭,亦或是《江湖兒女》中趙濤和廖凡的聊天,都還能看出導演對於長鏡頭的偏愛。
《江湖兒女》
與此相反的是導演在畫面色彩上的選擇。大片的灰色調蔓延在第六代的早期影片裏。主題是晦澀的,畫面是晦暗模糊,剪輯時常以碎片的形式出現。畫面構成與影片主題聯繫緊密,孤獨、空虛、無奈、迷茫,灰色讓情緒更直接。
但在《江湖兒女》中看不到這一點,穿着紅上衣綠裙子的趙濤,和影片裏紅綠分明的色調,或許可以視作賈樟柯用來解釋,何所謂現代江湖氣的關鍵物件。
《地久天長》裏,在成爲失獨家庭,與丈夫遠走他鄉之後,詠梅扮演的王麗雲在切菜的時候帶着一隻乾淨的、粉紅色的袖套。從鏡頭中可以看見,淺綠色的牆壁,藍色的窗簾,素淨而不再晦暗。
而婁燁則是最積極地嘗試以高清機來拍攝的導演之一。《推拿》中有盲人的視角和大量的雨水,但仍然比《春風沉醉的夜晚》和《浮城謎事》都更明亮。
當現實已經被時光更改,第六代導演們也在選擇出路。
如何與帶着傷痕的過去和解?婁燁的影片裏還沒出現明確的解答。
婁燁這幾年創作欲並不旺盛,上一部由他執導的影片《推拿》於2014年公映。從這部影片中,並沒有明顯的關於“和解”和“治癒”的成分。
他的影片仍然在關注着邊緣人羣,在黑暗裏服務別人的盲人羣體,和在按摩房裏“上鍾”的性工作者。整個故事的發生地“沙宗琪”按摩中心,在最後被地產公司收購,所有盲人按摩師各自分散,主角之一小馬和自己的女友,以失蹤來開始新生活。
《推拿》
有些角色在消失,有些角色在出走,有些角色則在迴歸。在《站臺》之後,賈樟柯的人物起初也在出走。《世界》的小桃成爲了北漂,《三峽好人》中的男女從山西小城趕到奉節,尋找已經逝去的生活。
但在《江湖兒女》中,巧巧和斌斌在出走後,再次選擇回到故地,觀衆既可以認定他們無處可去,也可以說是落葉歸根。
巧的是,王小帥的人物也在迴歸,《闖入者》的老鄧在北京居住多年後,回到貴陽面對往事,而《地久天長》的劉耀軍夫婦,因爲失獨而背井離鄉,又因爲一個電話而重回故鄉。
《闖入者》
時間對人物的改變一直存在,第六代導演們一直以自己的方式記錄。在過去,他們的人物是統一的。青年們長期處於空虛之中,被小的家庭和大的社會所拋棄。內心和未來都空虛無着。
如今,青年們大多長大了,成爲了沉默的成年人。他們有了更多的責任要揹負,也被命運和時代的洪流所推搡。《地久天長》《江湖兒女》《三峽好人》幾部影片,都被評斷爲“幾十年社會變遷史”。第六代導演的人物,已經不再是某個城市裏的某個個體。
三十年過去,他們的人物也隨着導演和觀衆一起發生了變化。苦悶空虛的荷爾蒙氣息消散,中年的焦慮麻木迷茫,終於在這些影片裏留下了痕跡。而那些有光鮮亮麗的職業和素養,號稱文藝先鋒的青年和搖滾一起,在這些影片裏,徹徹底底消失了。
無人可以爲此進行道德評價,這是導演們自己的選擇,也只有導演們自己可以論斷。
在多年前,王小帥曾在導演手記裏提過:“人們在意識形態、倫理道德、價值取向以及世界觀上處在一種不斷變化和尋找的過程中。但儘管如此,我所希望的、在我的影片中所具有愛和寬容的主題,依然會是影片的主要關注點。”
恰好,觀衆如今在《地久天長》中,也可以發覺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