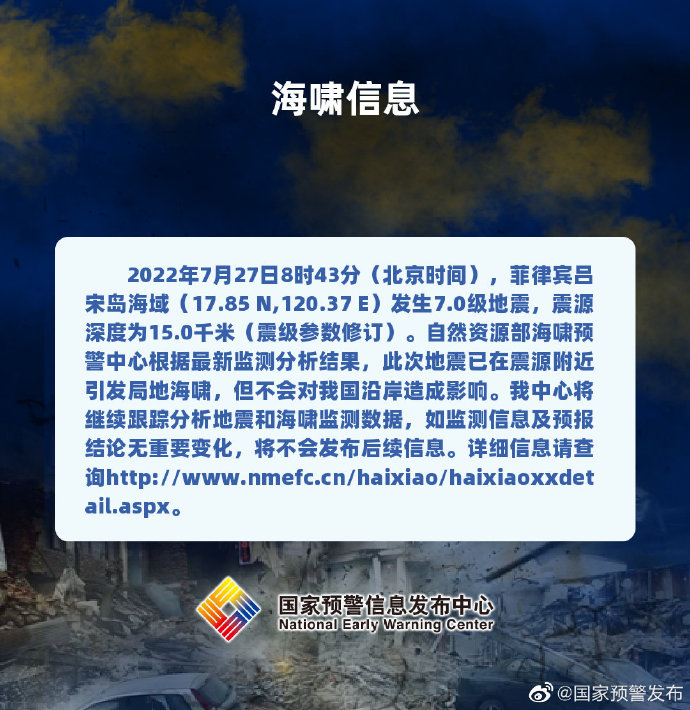第二章 飘在铁轨上的人
在我和外公二十年的交情里,外公一直是个古板的老头,常年把新闻联播当做精神食粮一期不落,别在胸前的全国劳动模范奖章,一天要擦上三遍,这样的老古董基本都是忠实的唯物主义者,所以,当一个近乎怪力乱神的词语正儿八经从外公嘴里冒出来,我个人是表示非常震惊的。
“什么?爸您知道这个?”老妈一脸厌恶地瞥着碗里:“真是用死人头泡酒哇……我们要不要报警?”
“啊?阿弥陀佛……”外婆原本并没有在意我们之前的谈话,听到老妈说人头泡酒,吓得直念佛号:“那怎么能往家里拿,快些丢出去!”
我们一家都是奉公守法的普通老百姓,像眼前这样惊悚的事物是从来没有见过的,一时间非常惊惧,都指望唯一认识这东西的外公能够说出个子丑寅卯。
外公看所有人都迫切地注视着他,倒颇有几分得意起来,带着一种吃盐比米多的优越感道:“这酒名字叫鬼头烧,里面不是人头,看起来很像,但实际上是一种树上结的果子,很久以前广西一带有人专门酿这种酒,酒劲相当大。”
这样说来,那颗落在碗里的“骷髅头”确实太小又太长了,对应眼窝的黑窟窿把整体分成上下两个几乎等大的部分,看起来更像是一只充血的大猪腰子。但即便如此,上面七窍俱全,血丝密布,乍看下就跟活剥了皮的人头无异,着实难以分辨,若不是有人刻意为之,这种离奇的相似程度足以令任何人发出惊叹。
“这也太像了,果子能长成这样?”老爹摇晃着手里的碗,那个大腰子就这么滋溜滋溜的滑来滑去,让人很不舒服。
“您刚才说什么鬼什么酒的,就是因为里面这团东西?”方伯脸色泛红,忍不住问道。
全家的注意力再次转移到外公身上。
外公这时却拿起撂在桌上的筷子,跟着夹了一片牛肉放进嘴里,饶有兴趣地咀嚼起来,就像刚刚发现这是可以吃的食物一样,先前稳稳挂在他皱纹间的得意神情忽然消失了,转而变成了一脸的不自在。
外公从来不是个藏得住事的人,这种类似于小孩犯错被大人发现,又拖延时间找借口的表情,肯定是瞒不过自家人的。
“你们莫听他乱讲,他哪里晓得什么广西的事情,志强你带着这酒请教你家老爷子,他学问大肯定知道。”外婆这一手激将路数稍显生硬,但是对外公万试万灵,从未有失。
方伯一听这是突然给他喂招啊,多少有点措手不及:“哦,那……这个……我先封上这口子……”
“哪个讲我不晓得?坛子一启开我就晓得了,就是想一下后面怎么跟你们讲。”没等方伯答话,外公先松了口,完了还不忘回呛外婆:“你别总搞那些花西西,激我没用,不吃这套。”
可事实再次证明,他就吃这套。
外公往后挪了挪身子,在椅背上靠定,双手十指交叉。这架势通常就表明他要开始讲故事了。
小时候总听外公讲他退休前在铁路工作的事迹,长大后就越来越少了,原因是外公的故事总结起来都一个意思——咱们工人有力量!不管什么主题,总能圆到这上边来,年复一年也就听乏了。
“六几年我还在广铁机务段,不像现在的高铁,那时候火车烧柴油,靠内燃机头带着跑,经常出问题,每趟车必须有机械师跟车检修。”说着外公抬起两个大拇哥指着自己:“当时我是段上手艺最好的……”
“诶,外公打住!您这开场白我都听了不下100遍了,熟得很,要不直接跳过讲有酒那段吧?”我有点心急,催促外公快进。
“有那么多遍吗?不还有自强没听过么,再催我懒得说了。”外公就势要反水。
“别啊,我意思是,您的光荣事迹晚点我们再做专题学习,先挑那些没说过的暖暖场呗,”我指了指灌进瓶子里的酒,陪笑道:“要不先给您来一杯助助兴?”
外公看着那酒出神,良久摇了摇头:“不能喝喽,”说着拣了一颗油炸花生米扔进嘴里,脸色渐沉,“年轻那会喝过一口,实在没想到……”
算起来应该有三四十年了,印象中那趟列车由南宁始发,经衡阳开往武汉。当时还是“小唐师傅”的外公晚饭后在湖南某个站上车换班。火车进站前,外公凭经验来到列车尾巴可能停靠的区域,准备从后端上车。然而等那笨重的绿皮车“啾”一声刹住,停在眼前的却是接连几节货运集装箱。
这在之前是极少见的,一般客运专列除了必须的动力机车外,由卧铺、座位厢、行李厢以及餐车厢组成,混编挂上货厢的情况非常特殊,会受到多方面条件的限制,除非有迫不得已的理由,否则绝不会这么干。而且,外公向后望了望,可以数到的集装箱就有四节,隐匿在夜色中的部分估计还有更多,明显已经是超负荷牵引了。
“胡搞乱搞,半道上撂挑子,你们下来拉车?”
外公心里嘀咕,转身朝列车前段一溜小跑,经过临着集装箱的第一段客车厢时,发现这节车厢竟是封闭的,不但没有列车员来开门,连窗户都是一片漆黑,就像从里面拉了层幕布一般,只得又继续向前跑了一阵,好不容易窜上了车。
早先就在车上的其他机修师正聚在一起打扑克,前一言后一语地跟外公聊了几句,有知道的说“在始发站之前就挂上了几节货箱子”,至于那节封闭的客厢,谁都没注意。外公心里不痛快,又看了一阵见没位置接手,就跟哥几个打了声招呼,独自挤到休息室睡觉去了。
那时火车时速普遍不足百公里,一趟省际列车走走停停,动辄要在路上耗上好几天。车厢里的环境也是相当糟糕,车窗一律锁死,夏天是“闷罐”,冬天又成了“冰箱”,不论死的活的、生的熟的,各种各样的行李都能随身扛上车,经常是人畜同座,混乱不堪。总而言之,选择铁路长途出行,一定要事先做好丢掉半条命的思想准备。
不过,再怎么拥挤的客车里,也有两处是相对舒适的,一是车头的驾驶室,再就是留给工作人员的独立隔间。隔间位置在靠近车厢的连接处,大小刚好够两个人面对面坐下。像外公这样跟车的机修师,遇到列车故障要负责抢修,其余闲时是可以进入这些隔间休息的。
时至午夜,外公迷迷糊糊睁开眼,起身舒展筋骨。这一觉他睡得并不踏实,一来隔间里空间有限,人只能坐着;二来总惦记着屁股后头的一溜货厢,万一半路上火车抛锚,又够大伙一阵忙。
按理说,货厢的结构强度是比不上客厢的,以客运速度跑起来,指不定哪个弯道就要出事情,那问题就不是抢修而是要抢险了。再者,外公一直留心车速的变化,即便是纯粹的客运,现在的速度也太快了,究竟运送什么东西需要这样极力赶路呢?
“至少也该发个通知,好让我们有准备啊,太不像话了!”外公越琢磨越觉得悬,也是闲得无聊,推开门便往车尾挤去——拉什么货不让人知道,机修师例行检查客厢总行吧?
借着微弱的车灯,外公摸索着穿过狭长的卧铺过道,窗外月光在山势的掩映下忽明忽暗,不时照亮一张张憔悴的脸,兀的有几分瘆人。好在他休息的车厢离最后那节客厢并不远,几分钟后便来到了封闭客厢的连接处。
这个所在没有稳定的照明,比车厢里更加昏暗,只能勉强看到一些金属器件的反光。正当外公要伸手去拧门把手,这时忽然响起了一阵汽笛,他知道那是火车进隧道之前的示警。果然紧接着眼前就是一黑,吭哧吭哧的传动声也瞬间抬高了音量,从四面八方呼啸袭来,乍听之下犹如千百人一齐哀嚎一般。
火车上的各种设施外公再熟悉不过了,他只稍顿了顿,也不等眼睛适应黑暗,便继续向门把探去。
没想到还未触碰到门把,竟冷不丁在半道摸到一只冰凉的人手。
瞬间一阵寒意从他脚底直凉到后脑勺,整个人触电般猛地一惊,立刻便往回缩手。
在漆黑的环境里突然摸到意料之外的东西,这种体验相当不愉快,退缩完全是出于条件反射。然而几乎同时,那只冰凉的手竟在黑暗中反客为主,准确无误地攥住了外公的腕子。
这一下,外公三魂惊掉了两魂,连蹦带跳疯也似的挣扎,只想要抽回手来。
有过类似经历的应该知道,人在那种情况下的反应是异常激烈的,可没想到,外公当时二十多岁的小伙,铆足力气猛甩几下竟没能挣脱,手腕还是被牢牢把住,当下卸了劲,脚后跟一软就站立不稳。
“同记,耍流氓哇?”
外公惊魂未定,脑子里一片空白,这会儿忽而听到门边角落里有人说话,一时间虽没听明白对方说什么,但总算知道原来是有人蹲在这,随即长舒一口气,叹了声社会主义好。
此时火车终于驶离隧道,恢复了些许亮光。对方撒开手,顺势站起身来,胸口以上正好进入月光范围之内,隐约就瞧见两撇小胡子和头顶一束盘起的发髻。
“我的个天爷,你谁啊?”外公把住壁上的扶手道:“车厢那么空,怎的躲这装鬼呢?”
那人嘿嘿一笑道:“我也是有要系在身啦,奉命守着惊门,免得吓到老百姓啰。”
外公皱眉道:“听不懂你说些什么,我是车上搞维修的,你去前面车厢找空地待着吧,别在这妨碍我做事情。”
“哦,这铁皮车子不跑得好好的嘛,没系啦,”那人边说边从胸前衣襟里掏出一包烟卷,拈出一支递给外公:“同记,来抽一根先,介后面你们领导关照过的,有我手镯就行,不信你去问下辣味姓赵的领导啦。”
外公受了刚才的惊吓,其实也没心思再在这纠缠,既然有老赵的言语,出事是他担着,随即接过递来的烟道:“我还懒得管,有情况去前面找我,你们别瞎搞就是。”
那人满脸堆笑,一副毕恭毕敬的样子,连声说好。
这边外公嘴里叼着烟,晃晃荡荡走进隔壁的休息室,随手就要关门。没想到一转身就看见门外一张蜡黄干瘦的人脸贴在面前,正和自己四目相对。
“我你……操!”外公一个趔趄跌坐在木板凳上,烟都不知掉哪去了,语无伦次地叫骂道:“娘的诚心是要吓死老子啊!”
再一看,还是刚才躲在暗处那个小胡子,不声不响跟到了休息室,此刻正嬉皮笑脸地望着瘫在角落的外公。
“同记,系我啦,”那小胡子说着便来扶起外公,然后端坐在对面的木板凳上,对他道:“同记,不系我有意吓你叻,特殊情况,消消气啰!”
外公有气无力地颤声问那人:“你到底是干什么的啊,没事你好好待着行不行?”
“系介样,我叻系装门负责在介一路上手镯那过车厢的,其习那扇门从里面落啦锁,有我西服活西胸在,哩从外面系推不开跌。”小胡子用一口南腔北调混搭的口音向外公解释着,那时候还没有推广普通话,两个人鸡同鸭讲一多半要靠猜,也不知道有没有错漏。
为了方便记录,后续就过滤掉两人的方言口音。
“是才时逢子丑际会,车厢所对方位移向惊门,近者皆受其扰,”小胡子笑道:“同志你是否觉得心惊肉跳,直冒冷汗?”
外公抚着胸口,没好气的对小胡子道:“我这一惊一乍还不是被你整的?再来准要吓出毛病。”
可他转念一想,好像那种心惊胆战的感觉,确实是在被抓住腕子之前就有了,也就是往最后一节客厢走那阵,越靠近心里越慌。再者从小到大摸黑干活的情况也不少,像这样被吓得六神无主还真是头一遭。
看外公脸上变颜变色,那小胡子接着道:“说来这事也怪我,本来同志你走近惊门就已经三魂不稳,我还突然抓了你一把,一般人肯定是吓坏了,不过让你碰到车门后果更严重,功过相抵,这事就算我俩扯平了吧!”说完小胡子又嘿嘿赔笑。
外公向来信奉马列主义,心中唯一神圣形象是光芒万丈的伟大领袖,对小胡子说的什么惊门魂魄之类并不为所动,只是觉得眼前这人虽然神神叨叨,但几句言语都说中他心中所惑,况且组织上不会无故叫这怪人守着车厢,也许其中真有什么非常事物也未可知。
想到这,再仔细看那人打扮,只见他长发拢起,在头顶盘成发髻,用一段布条扎住,两鬓带霜,清瘦模样,面色苍白,在车灯的照映下略微泛黄,但容貌却不过而立,比外公大不了几岁,身上套件素色褂子,摆长过膝,打着绑腿,穿一双薄底粗布鞋,端的是个道士装束,只欠一柄拂尘。
小胡子就像看穿了外公的心思一般,顺手抄起搁在角落里的鸡毛掸子,唱大戏似的摆弄几下,就势搭在肘窝里,跟着捏出个兰花指一样的手印,向外公欠身颂道:“无量寿福!”
这下倒把没有宗教信仰的外公难住了,怎么回呢?念声佛号吧,像是和尚道士要斗法,小时候听过那洋神父念的什么阿里路亚,好像也不合适。思来想去,最后“嗯”一声冲道士竖起大拇哥,硬答道:
“顶呱呱!”
两个奇怪的手势就这么僵持住了,我都能脑补出当时道士满头的黑线。
过了好一会,还是外公先打破了尴尬的局面:“你刚才说要是碰到那门就如何?什么更严重?”
“嘿嘿,其实也没什么,同志你现在不没事吗,就别问啦。”小胡子道士打起了马虎眼。
外公不依不饶,追问道:“你刚才可不是这么说的啊,要没事你跟着我干什么?这是工作人员的地方。”
“我是看同志你心绪不宁,过来闲聊几句,况且贫道现在也算是这车上的临时工啊。”道士说着又从胸前的衣襟里摸出一只扁平的小铁壶。
外公显然不信小胡子的话,可也不好发难,毕竟他真正感兴趣的是那节车厢里的东西,其余最多只算是趣闻而已。正犹豫是不是该让谈话直奔主题,就听那小胡子道士“噌”一声把封住铁壶的木塞启开了。
本就狭小的隔间里顿时酒香四溢,连从不饮酒的外公也不禁垂涎,心中百般惊异,早把那车厢里的事物忘到了九霄云外。
“你这壶里装的是什么好东西?”外公使劲吸着鼻子,似是想把整间休息室里的酒香吸尽一般,“是酒吗?”
“这却可以和你说道说道,”小胡子道士似是突然来了兴致:“此酒唤作鬼头烧,因储藏时须用异果入坛,其状酷似人首而得名,是广西山民的古法酿制,过程十分繁琐,我道门中人饮之可除三尸,于尔凡夫俗子最能凝神静气。同志,来一口否?”
外公别的没听明白,后面这意思是要让他喝酒压惊啊,登时喜出望外,忙说:“我是从来不爱喝酒的,这会也不知怎么,只觉得你这壶里的酒香,特别想要尝尝!”
那小胡子点头,用木塞原样封住壶口,吩咐外公去取半杯热水。
这可把外公高兴坏了,去不多时推门回来,端着一只搪瓷的水杯,直往外冒热气。
小胡子接过水杯,从酒壶里倒出不足半口小酒,摇晃一阵后递回给外公。
外公见状道:“你这也太小气了吧,好歹让我喝上一口,这兑水算是怎么回事啊?”
小胡子解释道:“你有所不知,若是嗜酒成性之徒,经年累月在体内养有酒虫,光闻到这酒香就能醉倒,硬拼上性命豪饮,是会醉死过去的,现在只为安神,趁热喝了这兑出的半杯足矣,多饮无益。”
外公听了将信将疑,但杯中酒香实在诱人,抬起手来就要喝下。
“慢!”小胡子忽又拦下外公,笑道:“喝了这杯,同志你只管静心睡下,师傅算过此行无虞,但后半夜有一阵行程朝向正合死门,你切莫向窗外张望。”
外公一心只想尝尝美酒的滋味,也没太过在意小胡子道士说了什么,含糊答应下来便举杯一饮而尽。
用外公的话来说,那是一种如饮甘露,飘飘欲仙的感觉,但究竟是怎样的口味,他却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原因是他灌下那杯酒后,立刻就不省人事,陷入了半昏迷的状态。
在某一瞬间,我脑海里闪过一个江湖骗子用蒙汗药谋财害命的画面,好在那个年代人人都是穷光蛋,也没什么值得提防。
外公确实是醉倒了,他不知道小胡子道士什么时候离开的,也不知道自己是怎样在昏迷中始终保持了一个盘腿打坐的姿势,当他被下肢阵阵酸麻的感觉激醒时,火车正在夜色中缓缓驶离某个破旧的小站。
交错的铁轨在窗沿下扭动,分离,靠拢,合并,再分离。
月台上褪了色的红灯笼逐渐缩小,远去。
月台上的人却不紧不慢的跟在窗外,面无表情,苍白缥缈。
迷迷糊糊的外公觉得奇怪,为什么铁轨上的人能赶上逐渐加速的火车,他们既不跑,也不跳,就那么忽近忽远地飘在铁轨上……外公这么想着,很快又昏昏睡去。
突然间,他猛地惊醒,四肢僵直,恐惧地盯着窗外,在黎明的晨曦中瞪大眼睛,竭力搜寻目所能及的每个角落。
那些飘在铁轨上的,是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