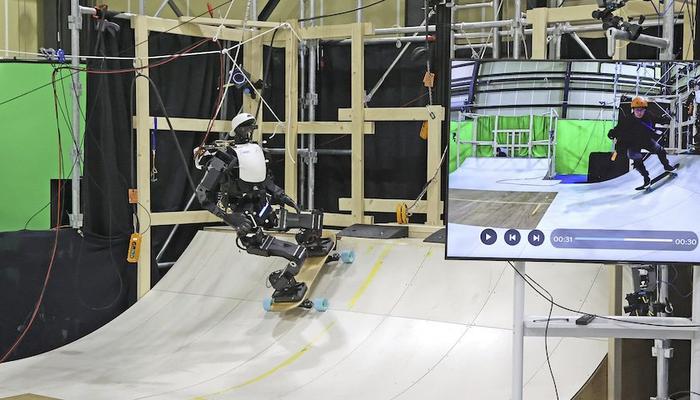棗莊:“十間樓”大變樣,你知道變成什麼樣了嗎?
山家林到官橋的公路叫山官路,省道標記爲s347線,我一直以爲當山官路穿過京臺高速就是滕州的地界了,這次去小石樓村,才知道不是這樣的,小石樓村應該說是滕州和薛城交界處的一個小村子,屬於柴胡店鎮管理,這個村子與衆多的鄉村一樣普通,也與其他鄉村不一樣的是,它的村子中心位置有一處地主宅院,保留了三棟二層樓建築,這處明清時期的建築羣,如今被稱爲“十間樓”也是用這個稱呼成爲省級文物保護單位名錄上的一員。
小石樓村普通的讓人有種很偏闢的感覺,要不是有“十間樓”的存在,可能我們也不會慕名開着車專程來到這個村子,但是就是這樣的一個村子的老建築,不僅沒有任其破敗下去,而且得到了非常妥善的保護維修,這纔是讓我感概的地方。
據《柴胡店鎮志》中記載和老人們的敘述得知,村中原來因有石姓人家居住,並有石樓一座,村名原爲“石家樓”;國學音韻大師張畊,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來此建造了佔地100多畝的張家大院,並有專門藏書的“十間樓”,因此村名一度被稱作“十間樓”;後又與後莊的“大石樓”延順,逐漸演變爲現在的村名——小石樓。
2016年1月10日下午,《棗莊晚報》記者孔浩老師、棗莊市中作協譚玉峯老師及小編驅車來到柴胡點小石樓村,專程來看看“十間樓”那時的“十間樓”如暮年老人,處處給人一種垂垂老矣的感覺,曾經做過國家糧庫的這些小樓得以保存下來,那時的牆面刷上了黃色的塗料,上面還有標語的字跡,從這些標語判斷是拍攝電視劇場景需要而書寫的,當地村民也說有不下二十部電視劇曾經在這裏取過景。
當時我們還感慨爲什麼不進行修復即使成不了經典,也可以作爲影視劇的拍攝地,說不準就被哪部熱播劇給帶成熱門景點了。
當時建造這些建築的張家主上是一位叫張畊的,乾隆至道光時代的人,他悉心致力於古文字研究,尤精訓詁、經學及音韻學。“治經以漢唐爲宗,一字之解,本‘六書’,貫百家,悉諸至當。”對東漢經學家、文字學家許慎所著的《說文解字》研究頗深。晚年所著《古韻發明》、《切字肆考》,以《說文解字》爲根源,以清代思想家、文字學家顧炎武,經學家、韻學家江永,哲學家、音韻訓詁學家戴震三家之說爲基礎,推廣擴充他們研究未盡的意蘊,並對其著作認真剖析,使古文字學理論更加精密。
因爲對經學及音韻的研究,使得他鐘情於書的收集與珍藏,他在24歲時專門爲了他的書建造了“十間樓”,據說經過數十年收集的藏書約十萬冊,這些書來源甚廣,河南、河北、江蘇一帶到處都是張氏族人不遺餘力收羅孤本珍籍、精校名抄的市場,僅於天津鮑氏知不足齋就不惜重金購得古籍達5萬卷,成爲魯南地區著名的私人藏書樓。張畊從早到晚讀書不倦。遂絕意仕途,超然塵外,蒐羅古籍,博覽羣典,著書立說。
張畊本人活到80歲,也就是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他撒手人寰,他的那些書安穩的藏在這些樓房裏,繼續滋養着張家的後人們,這個詩書繼世長的家族,因爲忠厚傳家遠,書籍的浸潤之下,張家後人們都有所作爲,其中更能讓他們這些族人驕傲和敬仰的兩個人:一位是在國難當頭時,毅然投身革命,並變賣家產爲抗日隊伍買槍買糧,開明民主人士、滕縣人民副縣長張瑞五;另一位是爲了革命理想,在日本鬼子的酷刑面前視死如歸、始終沒有泄露黨的機密,慘遭敵人殺害的革命烈士張兆謙。
2013年,“十間樓”被山東省評爲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到了2018年終於得以修繕,張畊當時投巨資營建“石家樓別墅”時,規模達到了東西5個分院、30餘處四合院、220餘間廳室組成,總佔地120餘畝。現在整個小石樓村剩下的這幾棟230年建造的張家建築僅是當初開始營造的很小的一部分,但是它在張家大院5個分院的建築中,它備受儒家文化的薰陶和浸潤,屬典型的北方套院式建築,分爲一、二、三進院,最後是堂樓。當時聘用了外地的工匠作指導,集當地的建築精英高手的智慧爲一體,吸收明清兩朝建築的優點。房屋整體佈局嚴謹規整,房屋結構外形莊重大方,堅固耐用.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與建築藝術價值。所以得以修繕是對傳統文化的保護與傳承。
3月16日,小編又一次與孔浩老師來到這裏,是因爲聽說,張家大院正在修復施工中,我們想看一下,新的張家大院變成什麼樣子了,據現場一位施工師傅說,這一次的修繕由山東省古建築保護專家實地測量制定了嚴格細緻的修繕方案,由湖北大冶古建承擔修復工作,修復圖紙細緻到對於每一塊磚的修復都有明確的標示,必須嚴格執行,所以,現在看到的這些建築與當時剛建好的時候最爲相似。
與我們一起來的小崔,年齡不大但是熱心於收藏古籍,也算是與張畊同好,他更關心的是當年那些書籍都去了哪裏,根據石正祥老師的文章來看,有一部分被當成了墊腳石:據傳說當年(1926年)直奉大戰在柴胡店地區的一次血戰前,直魯聯軍曽光顧張家,當時正值夏季連陰雨,道路泥濘坑窪,車馬炮無法行走,兵勇們就動用了張家10間樓的書籍,鋪了整整幾十裏泥路上,才順利過去。
滄桑變幻,解放後,張家大院收歸國有,西大院建起了小學,中大院爲國家糧庫。張家大院先後毀於解放戰爭、“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時期。所以建築尚得不到妥善保護,更何況其中的那些古書籍,一定是在歷史的某一天於愛書人最不願看到的方式結局。
棗莊地區目前留下的地主宅院並不多,甚至沒有一處是完整的,除了薛城西倉村的孫家大院得到了維修,保留下來的建築得到重新修繕,使得我們還能看到當初它的主人匠心獨運的木雕、石雕、磚雕藝術傑作,最爲遺憾的是,就在進入二十一世紀後,棗莊某地的地主宅院,號稱“十八間樓”的幾棟老建築卻被整體拆除。在當今社會提倡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把傳統建築視爲展現傳統文化的重要標誌,繼承傳統文化的物質載體的時代,不僅破壞了一處老建築羣落,也爲世人留下了沒有文化,不懂歷史的笑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