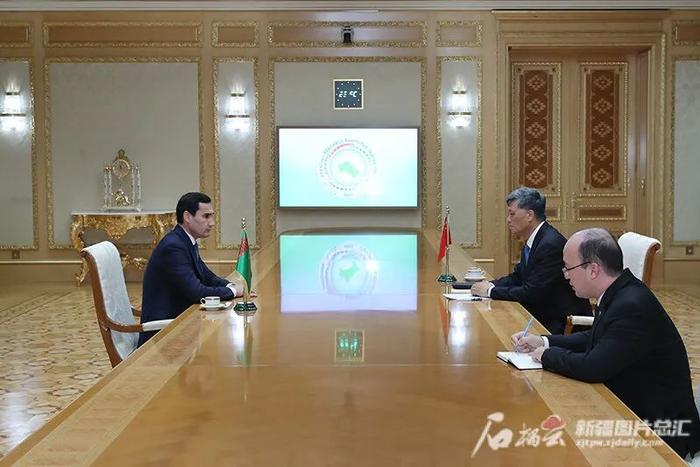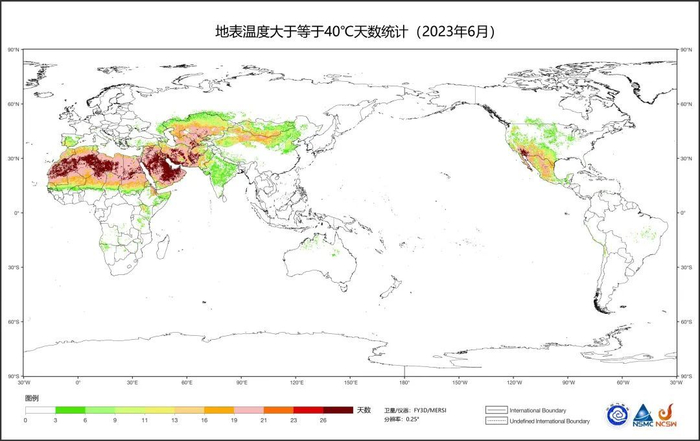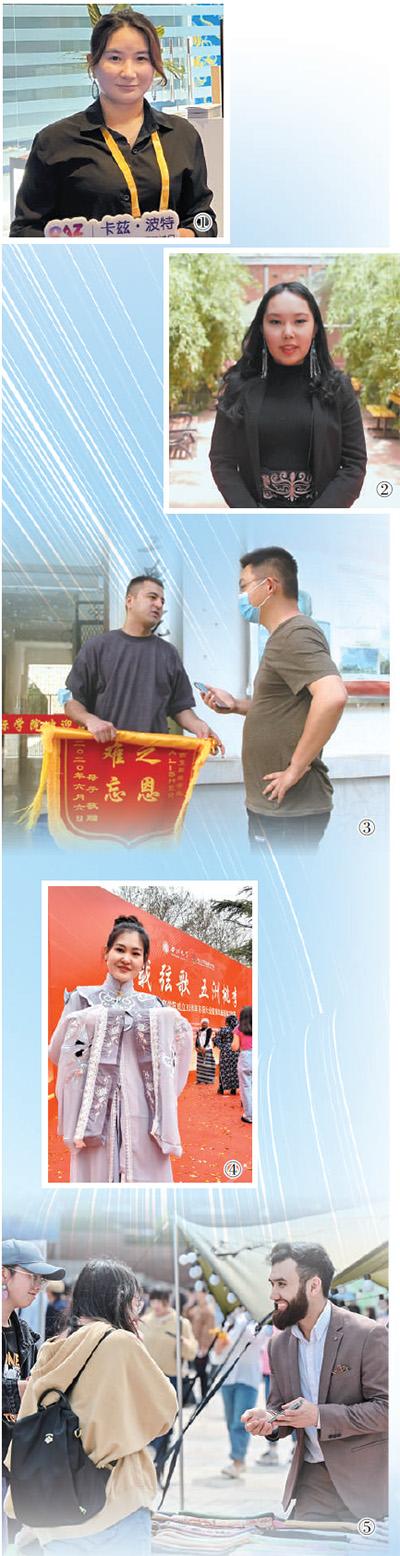印度新德里到底藏了多少敦煌藝術品?
位於新德里的印度國家博物館成立於1949年,是該國規模最大、館藏最豐的博物館之一。其館藏時段涵蓋史前至當代藝術,數量超過20萬件。
新德里國立博物館中亞部古物陳列廳內景
印度國家博物館設有史前、考古、中亞等多個部門,展廳則包括以1世紀到3世紀的犍陀羅和馬圖拉爲主的貴霜廳、以4世紀到6世紀的馬圖拉和薩爾納特爲主的笈多廳、涵蓋7世紀到13世紀的中世紀藝術廳、中亞廳及佛教藝術廳。其中,中亞廳的藏品基礎是斯坦因在絲綢之路上3次主要考察(1900—1901、1906—1908、1913—1916),歷經百餘座古代城市所蒐羅而來的壁畫、絹畫、木雕、石雕、陶塑、瓷器、金銀器、宗教及世俗文書。佛教藝術廳則囊括了大量來自印度本土、巴基斯坦、尼泊爾、中亞、中國西藏地區、緬甸、柬埔寨等地的古代金銅石木及彩繪造像。
S.492 夜半逾城(NM2003-17-312,Ch×lvi. 007)
貴霜廳、笈多廳、中亞廳、佛教藝術廳、中世紀藝術廳,上述5個廳的展品及庫房內相應主題分類下的館藏不僅在數量上極爲可觀,而且在涵蓋年代、出土物地域、造像題材、教派種類、風格樣式等諸多方面,有着極廣大而深厚的覆蓋面。其中大多數藏品在學術層面上具有不可替代性。
S.364 達摩真像(NM 2003-17-310;Ch00378)
早期印度本土佛教造像藏品
在新德里國立博物館中,印度本土製作與出土的佛教造像主要陳列於以下6個展廳:孔雀王朝/巽伽王朝/薩塔瓦哈納王朝藝術廳、貴霜王朝(含犍陀羅及馬圖拉風格)與伊克什瓦庫王朝藝術廳、笈多朝藝術廳、笈多朝紅砂石與早期中世紀藝術廳、晚期中世紀藝術廳、佛教藝術廳。其中,公元1-6世紀造像集中於前3個展廳。
作爲公元前的早期佛教造像藝術,孔雀朝的造像很有古風:造型樸拙、情節簡易。這種直覺觀感或許是一種錯覺,似乎孔雀朝缺少壯觀的營建。阿育王不僅派遣使者宣教四方,據說還曾派遣18名藝術家、工匠、畫師隨其子摩欣陀前往錫蘭,並在錫蘭故都繪製壁畫、營建廟宇。事實上,對於始終浸淫於中國本土佛教造像傳統的研究者,從孔雀朝、巽伽朝到薩塔瓦哈納王朝,乃至貴霜王朝,最大的視覺與觀念雙重衝擊,源於印度本土的象徵主義傳統。
斯坦因所掠中亞及敦煌佛教美術品概況
印度新德里國立博物館藏敦煌吐魯番藝術品及文書,主要來自斯坦因第2、3次中亞考察。1906年至1908年斯坦因開展的第2次中亞考察,沿絲綢南路北上,先後重訪了其第1次中亞考察到過的和田、尼雅,繼而發掘樓蘭、米蘭等古代遺址。在敦煌,斯坦因發掘了漢代長城烽燧遺址,拍攝了莫高窟洞窟壁畫,買走了藏經洞24箱文書、5箱絹畫及其他絲織品。在吐魯番,斯坦因初步考察了部分古代遺址,爲第三次中亞考察做準備。之後,經焉耆、庫車、喀拉墩,返回和田,併發掘了老達瑪溝及麻札塔格等古代遺址。
S.345 旗幡山花(NM 2002-17-187;Ch00138)
1913年至1915年斯坦因第3次中亞考察,仍沿絲綢南路北上,先後發掘了和田的麻札塔格、巴拉瓦斯特、瓦石峽等古代遺址,以及尼雅、樓蘭等古代遺址,再到敦煌獲得了藏經洞570件寫本,發掘了敦煌至酒泉間的漢代長城烽燧遺址。之後,至居延發掘了西夏黑水城(即喀喇浩特)遺址,至吐魯番阿斯塔那,切分了10個墓區,發掘墓葬34座。在吐峪溝、伯孜克里克等石窟揭取壁畫。返程時,調查、發掘了焉耆的七格星古代遺址和庫車的一些古代遺址。
S.450 于闐瑞像 (N M99-17-98;Ch××ii. 0023)
根據榮新江的研究,“斯坦因第二、三次中亞考察的一部分經費來自印度政府,所以根據英、印雙方的古物分配方案,一大批以文物爲主體的斯坦因中亞收集品於1918年運往印度新德里。1929年建立的中亞古物博物館,主要就是收藏這些斯坦因的收集品。1949年,印度國立博物館建成。到1958年,中亞古物博物館被合併爲國立博物館的一部分,藏品歸新館中亞古物部保存。收藏在新德里的斯坦因中亞收集品,主要是壁畫、絹幡畫、木雕、陶製小雕像、錢幣、陶瓷器、皮製品、玻璃器、金銀製品等文物材料,有不少佉盧文木簡也保存在這裏,漢文文獻很少,藏品總數在1100件以上。這些材料有的見於斯坦因本人的《西域考古記》和《亞洲腹地考古記》,但其時尚未區分哪些後來屬於印度所有。”
S.450.1 摩伽陁國放光瑞像
斯坦因獲得的繪畫品共計536件,其中282件收藏在英國倫敦大英博物館,254件收藏在今印度新德里國立博物館。536件繪畫品中,絹本畫約有335幅,麻布畫94幅,紙本畫107幅。在中亞部古物廳內,長期陳列的敦煌藝術品主要是佛教絹麻幡畫,還有吐魯番地區各類藝術品。如阿斯塔那墓葬出土陶俑、花園美人絹畫、伏羲女媧絹畫、吐峪溝石窟壁畫、伯孜克里克石窟壁畫等。在敦煌絹畫中,觀音題材最多。其他尊像畫及經變題材爲數不少。另有供養人供奉觀音與佛像絹畫1鋪,北方毗沙門天王紙本畫稿1件。在吐魯番藝術品中,泥灰質騎士俑1件,出自阿斯塔那3號墓區2號墓;泥灰質女俑1件,出自阿斯塔那10號墓區1號墓;泥灰質女俑頭1件,出自阿斯塔那1號墓區8號墓。花園美人像約有2幅出自阿斯塔那3號墓區4號墓。伏羲女媧像約有3幅出自阿斯塔那9號墓區2號墓。另外,還展出焉耆七格星遺址泥灰質菩薩雕塑、米蘭遺址佛與6僧侶及供養人壁畫殘片、和田巴拉瓦斯特遺址出土盧舍那佛壁畫一鋪等。
S.450.2 祇園說法
儘管2012年出版的《新德里國立博物館藏敦煌佛畫》披露了143件館藏佛畫,但存在四個問題:一、作者雖熟稔印度本土佛教美術,但對敦煌爲代表的中國中古佛教美術本土特點了解較淺,圖像讀解難免差池;二、圖錄披露畫作缺少細節,這是圖錄與實物的根本差別;三、罕有中國佛教美術史學者能夠親睹該批藏品;四、披露不完全,仍有超過100件作品從未示人。
S.450.3 坐佛
編號與分類
Ch.表示的是斯坦因的原始編號,即爲英文千佛洞的縮寫;Stein表示Stein painting(SP),SP表示的是大英博物館館藏號;NM表示National Museum代表印度新德里國立博物館館藏號,以SL.1(NM 2003-17-312)爲例:2003代表年,17代表藏經洞(莫高窟17窟),312代表印度新德里國立博物館對繪畫品的編號。該批絹畫從主尊神格劃分,可大致分爲16類,包括:佛陀、阿彌陀、藥師佛、彌勒菩薩、觀音、十一面觀音、千手觀音、日月觀音、武僧、文殊、地藏、五方佛、供養菩薩、四大天王、金剛手護法菩薩、七寶。
S.450.4 迦毗羅坐佛瑞像
上述16類題材,其佛教圖像學價值、史料價值、美學價值,遠非單一的題材劃分可以概括顯現。絹畫看似幅面有限、題材單一,無法在體量規模與細節豐富方面與佛教石窟寺相媲美。然而,絹畫作爲中古中國社會與宗教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組成,與石窟寺共同形塑了彼時民衆信仰、觀念與圖像共生的生活形態與面貌。
S.450.8 坐佛
此外,這批絹畫收藏於印度迄今已近百年。討論相關問題時,間或需參照作爲收藏地的印度本土學者研究。儘管印度佛教史學者中強調原發地的觀點,不可避免地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中古時代中國本土佛教圖像的自律性與本土化,但這也提醒我們中國學者,如何把握這些絹畫與印度乃至中亞等題材原生地之間的關係。
S.450.10 靈鷲山說法
縱觀古代亞洲世界內佛教的傳播與衍生,其內在層次之豐富,遠非早前學術研究中“A地首創題材a型,傳播至B地,摹仿爲a1型”這類單一線性的因果關係所能涵括。就佛教美術而言,圖像與經典的關係,亦非單純的一一對照。恰如宮治昭在其堪稱典範的涅槃圖研究中,揭示了同一題材在同一區域前後文化期的演進,以及周邊區域的接受與衍生。在本地演進與向外擴散中,題材分解爲多種層次,如文本、信仰、觀念、圖像、畫風等。這些層次,被受衆與信衆按照各自相異的需求所遴選,最終創作出各區域看似同源,實則各有千秋的佛教藝術。
S.450.11 劉薩訶瑞像
佛陀與比丘可謂佛教美術中最常見的基礎題材。在這批絹畫中,既可見到“夜半逾城”這類經典且面貌穩固的題材,也可見到伴隨着中國本土高僧信仰而起的新圖像。旗幡作爲一種特殊的禮儀畫形制,時見於佛事活動。旗幡所繪手印,或許微妙地反映出當時的信仰取向與偏好。瑞像在中古時代頗受歡迎,由此衍異的圖像與文本的變體,造成讀解此類圖像的困難,卻也使探索過程變得生動有趣。更重要的是,瑞像所反映的不僅是宗教觀念,亦是西域各國往來交流的旁證。
查看原文 >>